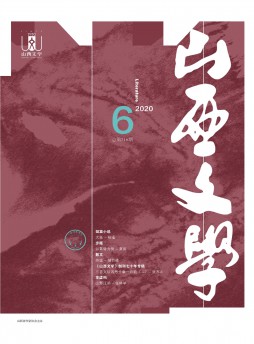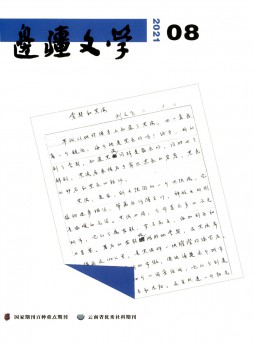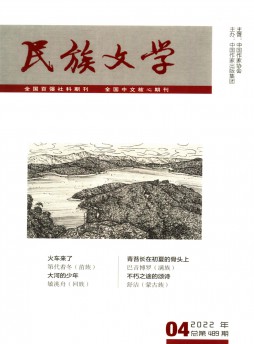文学批评理论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文学批评理论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 网络文学 文学批评 传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学批评一直以来都是文学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漫长的文学史中,文学批评从来没有缺席,它伴随着整个文学史的发展,直至今日。但当前互联网的发展完全颠覆了文学发展的土壤,网络文学在兴起的初期就受到了众多的质疑,特别是传统的文学批评似乎在网络文学环境中并不具备话语权,也导致了文学批评当前的发展极为艰难。当然,我们不能够一味地为了批评而批评,批评的目的是进步,而不是吹毛求疵。当前网络文学发展如此蓬勃,一定有其深刻的原因,所以我们就要剖析网络文学与文学批评理论的关系,图探索出二者的平衡点,使二者能够相互促进,为中国文学事业乃至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重要的力量。
1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的概念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字面上我们很容易理解,指的就是通过批评的方式对文学的发展方向、内容和思想等要素进行正确的引导,使文学的发展不致偏离方向。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的发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的,首先,对于作家来说,文学批评能够有效地规范作家的写作行为,能够引导文学创作的正确方向;其次,对于读者来说,通过批评的角度能够让读者更为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也有助于提升读者的文学审美水平;最后,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文学批评代表的是主流的价值观,之所以会出现公认的批评,是因为其不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想法和观念,这对于弘扬社会正能量,促进社会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网络文学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在互联网上创作、发表、供读者阅读的文学作品。网络文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作品的水平也参差不齐,这恰恰是因为网络的开放性激励着“草根”一族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舞台,文学不再是作家独享的瑰宝,而成为了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并实践的平民化的产物。
2网络文学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挑战
当前文学批评家担忧的并不是在网络文学环境中没有文学批评,恰恰相反,网络世界绝对不缺少“批评者”,网络的开放性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对网络文学进行评价,而很多观点非常浅显,仅仅是自身的直观感受,并不具有代表性,也不具有客观性。这才是文学批评家们最害怕见到的事情---不怕没有批评,但是怕没有逻辑的批评。在网络文学蓬勃发展的当前,文学批评越来越大众化,却又越来越低俗化。当然,这也是一个文学批评发展的“阵痛”,传统文学批评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现在话语权回归大众,势必要经过一定时期的混乱和无序,最终终究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文学批评领域的“精英”和“平民”之争,是文学批评在当前时代必然要经过的过程。
3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如何应对网络文学的挑战
在当前网络文学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应当适时地进行调整,以应对网络文学的挑战,如此才能够不负文学批评之名,充分发挥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发展的作用。
首先,文学批评理论应当走进大众。数千年来的文学批评理论话语权都掌握在极少数人口中,这种自诩为“雅”,却无法容忍“俗”的文学批评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状态,精英化并不是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的正确道路。文学和文学批评是服务大众的,大众都不认同,文学批评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了。
其次,应当坚守文学批评理论的原则、精神和价值。文学批评是要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促进和引导作用的,无脑地批判并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文学批评对于当前文学环境的适应还是应当坚守一些原则、精神和核心价值的。例如人文主义精神、歌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这都是文学批评恒久不变的精神和价值,无论文学批评理论如何发展都不应当有所改变。
最后,要转变批评的方式。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太过于艰涩,让大多数读者都无法理解,那么文学批评难道就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吗?当前的时代中,人们在各个领域的选择都更多了,人们更愿意去选择自己能够理解和适应的事物,文学批评理论亦是如此。通俗化是文学批评理论应有的发展方向,沉重的说教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了,注定要被淘汰掉。
4结语
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确给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网络文学之所以能够在这数十年内极为蓬勃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的发展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社会意识随着社会物质的变化已经发展根本性的变革。很多文学批评家都在感叹和惋惜,因为文学批评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却在只有数十年历史的网络文学面前捉襟见肘。笔者认为,文学批评是伴随着文学的发展而诞生的,只要有其价值,就不会消亡,只是面临着当前文学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传统的文学批评应当进行合理的改变,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是文学批评真正应当遵循的原则,才是能够继续发挥其引导作用的唯一出路。
参考文献
[1] 赵李梅,傅宗洪.传统文学批评如何应对网络文学的挑战[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29(7).
第2篇
论文关键词:印象主义的批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批评的独立性;自我;妙悟
很久以来,人们对李健吾先生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说、散文、翻译作品和法国文学研究理论上.即使谈他的文学批评,大多也只是会谈到他于1935年——1936年年问因书评而引起的和巴金、卞之琳的两场笔墨“官司”。但是毫无疑问,李健吾还是一个成就卓著的文学批评家。由于他与法国印象主义的渊源,一直以来,李健吾的批评都被称作是印象主义的批评,或者是印象鉴赏的批评,他自己也乐于承认这样的概括。但是近年来,有许多评论者注意到了他的批评中不仅有法国的印象主义,也有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成分,因而他的批评又被称为中国式的印象主义批评。但是,在我看来.纵观李健吾的文学批评理论.法国的印象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并不只是份量轻重的问题,而是表里的关系,即法国的印象主义为表.而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为里,虽然完全中国传统式的文学批评所占的地位与份量不大.却是他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所在.是我们理解他创作与批评的一把钥匙。
一、表面上看来,他深得法国印象主义的精髓
从源流上说,印象主义其实是唯美主义的余波。而唯美主义强调艺术的独立,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因而印象主义提出“为批评而批评”。此外.印象主义者很看重批评家的主观介入和创造性的发挥.他们非常赞同王尔德提出的唯美主义观点,认为批评也是一种创作,甚至认为“最高之批评.比创作之艺术品更富有创造性”。因而印象主义者主张应以个人创作的态度从事批评。而在文学批评的本质上,李健吾所持的“自我发现论”,就是把批评当作是“自我发现”的一种手段。“犹如书评家、批评家的对象也是书。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价值的决定。发现自我就得周密,决定价值就得综合。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去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批评)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可以说,李健吾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肯定了批评本身是一种艺术。这样,批评者就有了他自己的存在,而不必以作者的是非为是非。更不必如伺候东家一样伺候作家,看作家的脸色,因为“作者的自白(以及类似自白的文件),重述创作的经过,是一种经验;批评者的探讨,根据作者经验的结果(书),另成一种经验”。批评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批评者有阐释的自由。因此,当《爱情三部曲》的作者巴金表示批评者的“拳头会打到空处”的时候.李健吾并不是脸红心跳、诚惶诚恐地收回自己的意见,而是坦然道:“我无从用我的理解钳封巴金先生的自由.巴金先生的自白同样不能强我影从。”他捍卫了批评的尊严,因为批评“是一种独立的,自为完成的.犹如其他文学的部门.尊严的存在”。在他看来.批评的位置并不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尴尬,批评家不需要同作家“攀亲戚”.批评和作品是两种互为需要的艺术。批评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批评者有阐释的自由。维护批评的尊严当然不以贬低创作的地位为代价,批评者和创作者是平等的,但更是谦逊的、取对话的态度。批评者的谦逊并非意味着批评主体的丧失,而是恰恰相反,批评主体的确立不表现为教训、裁断,甚至判决的冰冷的铁面.而是以“泯灭自我”为条件.并且在与创作主体的交流融汇中得到丰富和加强。因此,对于批评者来说,作品并非认识的对象,而是经验的对象;批评主体在经验中建立和强化.并由此确立批评的独立性。
倘若批评是一种独立的艺术.那么批评也就是一种“表现”,表现“它自己的宇宙,它自己深厚的人性”。于是而有“所谓的风格,或者文笔”。风格即是“人自己”,表现自我,同时就“区别这自我”.“证明我之所以为我”。其难在于一个“诚”字。近年来,批评界不时冒出一两声对文采的呼唤.李健吾的议论可以使我们豁然开朗:批评要有文采,但这文采决不是外加的甚至外人的“润色”,它“是内心压力之下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由此出发,李健吾把“自我”作为批评的“根据”。文学创作中“张扬自我”虽然不是新鲜事,但在批评中。“自我”却一直被忽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健吾建立起了一种批评的自我意识,他认为强调“自我的发现”的结果就是必然宣告“批评的独立”,批评也就由充当文学的附庸而转为一种独立的创造“艺术”。
印象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认为宇宙万物永远都处于变动的状态,不可能真正把握客观真实,一切所谓“真实”都无非是一种感觉,是相对的、主观的。这样,印象主义者就特别强调以个人的感觉与印象去取代外在的既定的批评标准。或者说,干脆否定任何批评标准。
由此出发。李健吾也否定批评中存在任何客观的固定的标准。对于许多批评家都特别关注作品的所谓“客观意图”。他认为是不存在的,因为即使是作者本人也不一定就能说得清楚,那么批评家就更加无从解释了。更何况人与人的差异极大。同样的事物也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任何解释也都无所谓是否合乎标准。所以,李健吾的批评重在对于作品的整体的审美把握。首先是作品,首先是阅读,首先是体味。“批评的对象也是书”,“凡落在书以外的条件。他尽可置诸不问”。首先“自行缴械,把辞句、文法、艺术、文学等武装解除,然后赤手空拳.照准他们的态度迎了上去”。要用“全份的力量来看一个人潜在的活动,和聚在这深处的蚌珠”,要“像一匙白松糖浆,喝下去,爽辣辣的一直沁到他(作者)的肺腑”。否则,“缺乏应有的同情”,就“容易限于执误”。他强调直觉,强调感受,“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价值的决定”。据说如今有的批评家很少读作品,或是浅尝辄止,他们的批评隔靴搔痒,戳不到痛处,也就难怪了。
二、实质上。他是在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现代化
正如温儒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所说:“中国传统批评思维方法不无精微之处,在和世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批评理论的比较中。中国古典形态的批评确能独具特色。一般而言,我国传统批评多采用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松散自由的形式,偏重直觉与经验,习惯于作印象式或妙悟式的鉴赏。以诗意简洁的文字,点悟与传达作品的精神或阅读体验;另有一种传统批评的路数则截然不同,那就是作纯粹实证式的考据、注疏和索隐。但是不管哪一种,都不太注意语言抽象分析和逻辑思辨,缺少理论系统性。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所依赖的不是固定的理论和标准,而是文人大致相同的阅读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欣赏力和判断力,这些都是沟通批评家与作者、读者感受体验的桥梁。”
如果我们抛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主义与术语.仔细看一看李健吾所作的许多评论,用心体会一下的话,就会发现李健吾虽然被冠以印象主义,但他对许多作家作品的精微的议论却更令人想起中国古典的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人间词话》等等。他之所以推崇印象主义,是因为它从本质上与中国的古典文学批评是相通的,李健吾是想用印象主义的理论来收束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使之更富有操作性。更容易符合现代化的要求。
至于具体的方法.就是“把他独有的印象形成条例”。“印象”不是所有人的印象,而是他独有的。基于他全部个人的修养、经验、知识和人格的印象,“条例”即规则,即综合。要通过理性分析来完成。不妨说。李健吾的批评是一种以个人的体验为基础,以普遍的人性为指归。以渊博的学识为范围的潇洒自由的批评。用他自己一再引用并欣赏的印象主义批评家法郎士的话说:“好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
第3篇
论文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特征;文本性;政治性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舶来品,它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20世纪80年代,在渡过了西方“历史主义危机”之后,人们又重新追问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以反抗形式主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征。
一、历史与文学
(一)历史是什么。从历史理论来说,新历史主义的“新”是相对于传统历史观而言的,这最主要表现在它对历史的性质的再认识上。而对“历史是什么”的回答,构成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传统的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独立于他的研究手段(“发现”)和工具(“语言”)的实际存在。如果历史研究者在把握历史的过程中能够克服和排除主观因素,透明地运用其语言工具,他就能够再现般发掘出埋藏在时间风尘下的“史实”,并由此获得关于历史的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发现。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上述的历史观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它本身就是非历史的。历史研究者的主体(“人”)和他的工具(“语言”)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具体的人在借助语言而把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他的视点和视野都已经被限制在某一现刻历史、语言的历史沉淀以及它们错综的复合影响之中。
展现在他眼前的不过是他所看见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因此,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现时的人对过去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以话语的形式存在,它是被写出来的。至于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们则不管,他们认为历史主要由一些文本和一种阅读、阐释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
对此美国文艺理论家海登·怀特说:“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在这里,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并非纯粹的客观再现,而是语言对事件的再度构成,其中必然渗透着语言运用者对事件的解释。
因此,历史被看作一个文本。海登·怀特还进一步论证道:“不论历史事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们都是实际上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被认为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这样的事件,为了构成反映的客体,它们必须被描述出来,并且以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描述出来。后来对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释,不论是自然逻辑推理的还是叙事主义的,永远都是对先前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释。描述是语言的凝聚、置换、象征和对这些作两度修改并宣告文本产生的一些过程的产物。单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历史是一个文本。”
历史是一种话语,或一种文本。这种历史观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社会的色彩,是后结构主义者历史观的延续。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把历史称为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正是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用福柯的话说就是,原先的一个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被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取代了,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历史。福柯的这种历史观正应和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信念,即人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思想和感知,而文本之外的世界对于人的思想来说是不存在的,没有意义的。
作为话语或文本而存在的历史,带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虚构因此而成为历史文本无法摆脱的特质。海登·怀特曾说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便是基于对历史文本的想象与虚构特质的理解而作的评论。这也就是说,历史从来就不能脱离想象而存在,历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语言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与此相关,所谓历史真实并不等于事实,它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绝对的真实,一种离开具体观念和阐释语境的真实。历史话语中的真实总是存在于一定的观念构造之中。
(二)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当海登·怀特把历史的深层结构解释为“诗性”的时候,他已经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建立起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联系。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相似。在传统历史学家那里,历史的特质是“真实”,它记录的是真实的事件,而这种“真实”与文学的特质“虚构”恰成对比,两者是格格不入、不容混淆的。但新历史主义者打破了历史的“真实”假象,他们认为,历史文本的运作方式是“编织情节”,即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的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种编织情节的方式与文学话语的虚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
因此,在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中,文学文本被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认为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映。那么,旧历史主义批评家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任务就是一种“还原”历史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通过把文学作品放到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中,来试图再现出作者的原来的意义,从而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义。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因为它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或者说历史是背景,文学作品是前景。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由特定文本构成。在他们看来,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在新历史主义者眼里,文学与历史并无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复杂的相互纠缠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他们所关注的,并非通常人们理解的那种虚构的、想象的、狭义的文学,而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换句话说,新历史主义批评从事的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在具体批评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用文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也能看到“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文学”。
二、文学与政治
当新历史主义用“文本性”和“互文性”填平了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间的鸿沟,拉近了历史客体与当代主体间的距离时,并不意味着要把历史文本理解成凭空捏造,新历史主义的目的是揭开作为教科书或史书的“历史”的神秘的面纱,让人看到其形成轨迹,发现文本的“历史性”。在这方面,它对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多有借鉴。福柯用“话语”连接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社会机制、惯例、习俗等,这就使文本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指向社会历史。话语实践植根于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总是体现着权力的关系。由此,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指出,不论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
同时,福柯挑战现存历史定论的勇气也给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以莫大的鼓舞。福柯说,在任何一个看似处于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都充满了被压抑的它异因素,历史学家必须在他的谱系研究中对它异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研究断裂就是研究特定的话语、社会形态的形成条件,并由此对它进行批判,而不是认可;昭彰它异不仅否定了统一意识形态的神话,而且通过历史定论对它异因素的压制过程和方式可以透视出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的机制运作情况。
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批判也就必然包含着对现今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不在于马上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而在于对此制度所依存的原则进行质疑。新历史主义批评所关心的不只是主导意识形态所维持的表象,而更重要的是这表象下被压抑的它异和破坏性因素。
扩展阅读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