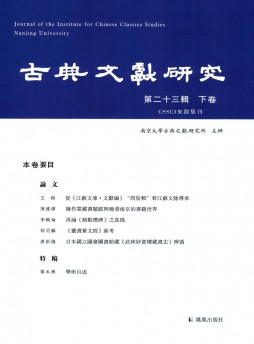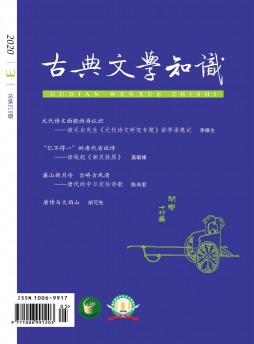古典词学趣范畴承传考察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古典词学趣范畴承传考察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趣”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审美范畴,它与“味”、“韵”、“格”等一起被人们用来概括文学的审美本质特征,标示文学的不同审美质性。“趣”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是一个相对出现和成熟得较晚的审美范畴。它衍化于唐前,成型于宋代,承传于金元,盛兴于明代,深化于清代,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范畴之一。本文对我国古典词学“趣”范畴的承传予以考察。
一、“趣”在古典词学批评中的承传运用
“趣”作为我国古典词学的审美范畴,它最早是在北宋前期进入到词学批评中的。有宋一代,人们多以“味”、“韵”、“格”等审美概念概括词作的不同审美本质及其特征,与此同时,少数词论家在词评中也引入了“趣”这一审美概念,较早将“趣”作为古代文论的审美范畴拓展了开来。宋代,运用过“趣”对词作进行论评的篇什主要有:米友仁《白雪·洞天昼永自序》,詹效之《燕喜词跋》,王质《苏幕遮·水风轻,吹不皱自序》,范成大《步虚词跋》,周密《乳燕飞·波影摇涟甃自序》,尹觉《题坦庵词》,柴望《凉州鼓吹自序》,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等等。如:范成大《步虚词跋》云:“自玉阶及红云法驾之后以至六小楼,意趣超绝,形容高妙,必梦游帝所者彷砩得之,非世间俗史意匠可到。”(朱祖谋《石湖词跋》引)范成大在词跋中较早引入“意趣”二字评词。他评断《步虚词》创作呈现出高妙的意趣,与一般词作着意从现实的层面感发拉出了一段距离。尹觉《题坦庵词》云:“人见其模写风景、体状物态,俱极精巧,初不知得之之易,以至得趣忘忧,乐天知命,兹又情性之自然也。”尹觉在评其师赵师侠词时,针对一般人评断赵词写景状物极其精巧,认为赵词最初是以情性为寄的,以抒发意趣为其词作之旨,它是在不经意然又暗合艺术规律中体现出精巧之态的。铜阳居士《复雅歌词序》云:“《文选》所载乐府诗,《晋志》所载《砀石》等篇,古乐府所载其名三百,秦汉以下之歌词也。其源出于郑、卫,盖一时文人有所感发,随世俗容态而有所作也。其意趣格力,犹以近古而高健。”鲖阳居士在文体质性上持诗词同源说,他评断古乐府、《文选》诗等作品上接了“有感而发”的上古诗歌传统,在意趣格力上呈现出高古劲健的特征。其又云:“吾宋之兴,宗工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犹祖其遗风,荡而不知所止。……其韫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鲖阳居士又从文学历史的角度评断宋词发展特征。他认为,宋人词作中能承古代风雅统绪,表现出骚人之意趣的词作还不多,为此,他希望通过编选富于雅正之作来做标树与提倡。南宋末年,张炎在《词源》中专列“意趣”一节,以“意趣”作为其评词的核心。其论道:“词以意为主,不要蹈袭前人语意。如东坡中秋《水调歌》云……王荆公金陵《桂枝香》云……姜白石《暗香》赋梅云……此数词皆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张炎在作词力主清空的同时,努力从意趣上标树词之创作。他推尚苏轼、王安石、姜夔等人词作,认为他们的一些优秀之作在对词意的凸显中,都能“意”中寓“趣”,“意”与“趣”相融相生,这使词作审美进入到快乐自由的层面。张炎将北宋以来苏轼、俞文豹等人对“意趣”的标树引入到了词论中,这在词论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我国古典词学批评偏重于对“情”的张扬,相对而言,“趣”在明人词学批评视野中不为惹眼。此时,承传运用过“趣”来对词作进行论评的著作和篇什较少。陈霆《渚山堂词话》在比较李世英、欧阳修《蝶恋花》中句子“朦胧淡月云来去”和“珠帘夜夜朦胧月”时,认为:“状夜景则李为高妙;道幽怨则欧为酝借。盖各适其趣,各擅其极,殆未易优劣也。”陈霆从李、欧二人词作各自艺术特征的呈现上标示出他们不同的词中意趣,界定二人词作意趣各别。他道出了词趣无优劣的原则。陈子龙《幽兰草词序》云:“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裱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陈子龙归结五代南唐至北宋末年词作的风格特征,他认为,此期词作都能立足在由情意而言辞,由言辞而词境的审美生发的基础上,通过天成的词境表现出创作者的“哀艳之情”或“盼倩之趣”。陈子龙较早见出了词趣审美表现是落足在词境的基础上的。
清代,词学兴盛,“趣”成为了人们评说词作的最重要审美标准之一。这一时期,承传运用过“趣”来对词作进行论评的著作和篇什较多,主要有: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倚声初集序》,先著《词洁辑评》,顾贞观《十名家词集序》,厉鹗《张今涪红螺词序》,查礼《铜鼓书堂词话》,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戈载《梦窗词跋》,刘熙载《艺概·词概》,张文虎《绿棵花龛词序》,张德瀛《词征》,陈廷焯《词则·大雅集》、《白雨斋词话》,杜文澜《憩园词话》,朱祖谋《梦窗词跋》,林大椿《欧阳文忠近体乐府跋》,等等。清人词学批评涉及到的“趣”的称名主要有:倩盼之逸趣、天趣、晕碧渲红之趣、意趣、佳趣、穷高极深之趣、淡远之趣、生动之趣、兴趣等。如:邹祗谟《远志斋词衷》云:“词虽小道,读之亦觉风气日上。序《衍波词》者,唐祖命云:极哀艳之深情,穷倩盼之逸趣。其旎高则璟、煜、清照之遗也。”邹祗谟对词作的地位与作用极为标树,他借为别人词作序之机,道出了五代、宋以来以“词家三李”为代表的正统词作路径实追求体现于顾盼之间的一种逸趣。厉鹗《张今涪红螺词序》云:“今涪词淡沲平远,有重湖小树之思焉;芊眠绮靡,有晕碧渲红之趣焉;屈曲连璪,有鱼湾蟹堁之观焉。”厉鹗评词崇雅尚清,他这里评断友人张亦枢词作有思致,有雅趣,词风鲜丽而词意悠远。查礼《铜鼓书堂词话》认为:“(郑燮)才识放浪,磊落不羁,能诗古文,长短句别有意趣。……(《沁园春》)风神豪迈,气势空灵,直逼古人。”查礼对郑板桥词“别有意趣”甚为心仪,他评词不限一端,对郑板桥《沁园春》一词以风神偏胜,以气势空灵见长极为标树。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评道:“苏、辛并称,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而苦不经意,完璧甚少;稼轩则沉著痛快,有辙可循。南宋诸公,无不传其衣钵,固未可同年而语也。”周济在对苏、辛二人词作的比照中,以“天趣独到”、“苦不经意”概括苏词,以“沉著痛快”、“有辙可循”归结辛词,他从词作意趣和创作路径上将苏、辛二人区分开来。刘熙载《艺概·词概》则评道:“叔原贵异,方回赡逸,耆卿细贴,少游清远,四家词趣各别,惟尚婉则同耳。”刘熙载细致地从词作意趣上辨析晏几道、贺铸、柳永、秦观四人词作异同,他在批评实践中切实地将“意趣”视为了词作审美的质性所在。陈廷焯《词则》又评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云:“情景兼到,骨韵俱高,无起伏之痕,有生动之趣。古今杰构耆卿集中仅见之作。”陈廷焯从词作审美质性的高度来加以论评,他概括柳永词作《八声甘州》在审美表现上情景交融,有骨力,有高韵,有生趣,是其词作中的“仅见之作”。这里,陈廷焯将“生趣”移用来了评词,体现出对词作审美特征新的认识。
二、“趣”在古典词学中的承传阐说
“趣”作为审美范畴被引入到词学批评中之后,从明代开始,词论家开始对其予以了理论阐说,这主要体现在钱充治和陈子龙两人的论说中。钱充治《国朝诗余序》云:“词者,诗之余也。词兴而诗亡,诗非亡也,事理填塞,情景两伤者也。曲者,词之余也。曲盛而词泯,词非泯也,雕琢太过,旨趣反蚀者也。”钱充治从不同文学之体艺术表现的旨趣上,来论析词与诗、与曲相互间的递变与差异。他指出,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用语及声律等方面过于讲究雕饰,这使词作为文学之体的旨趣被消弥了,最终被富有生趣的曲所替代。钱充治之论富于对文学历时发展的辩证认识。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云:“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沈永之趣,则用意难也。”陈子龙道出了词作意趣表现中存在的一个难题,这便是如何以浅近之笔写出沉挚之思,在审美表现上既产生如在目前的效果,然同时又含蕴隽永之意趣。其《三子诗余序》又云:“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纤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娈之趣合,志溺于燕婧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陈子龙肯定不同的时代有各异的词作,但他认为温厚中和的词作是无论如何都不足以宣志达情的。他一方面强调人对外物的感触中趋于极端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反对人情过分柔靡,认为此与“婉娈之趣”相触相生,必使词作呈现出异常唯美、柔弱的面貌。
清代,承传明人对词趣的阐说取向,词论家对词趣的审美内涵、特征、形态、生成与创造等展开了较为细致的论析。他们将“趣”升格为最重要的词论审美范畴之一。这一时期,对“趣”予以理论阐说的词学著作和篇什主要有:李渔《窥词管见》,陈椒峰《苍梧词序》,吴衡照《莲子居词话》,焦循《雕菰楼词话》,李佳《左庵词话》,蔡宗茂《拜石山房词钞序》,孙麟趾《词径》,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沈祥龙《论词随笔》,等等。如:陈椒峰《苍梧词序》云:“宋之能词者六十余家,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数子,始可称以新意合古谱者。杨诚斋论词六要:一日按谱,一日出新意是也。苟不按谱,则歌韵不协,歌韵不协,则凌犯他宫,非复非调;不出新意,则必蹈袭前人,即或炼字换句,而趣旨雷同,其神味亦索然易尽。”陈椒峰在论词上强调“新意”与“按谱”并重。他认为,如果词作缺乏新意,那么,即使在字句运用上大做文章,也会使词作意趣、主旨相同,缺乏“神味”。陈椒峰此论道出了新意在词趣表现中的重要性。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云:“咏物如画家写意,要得生动有趣,方为逸品。”吴衡照之论虽针对词作咏物而言,然其在清代词趣论中也有独到的意义,它实际上提出了寓“生趣”于词作的要求。焦循《雕菰楼词话》提出:“诗词是以移其情而豁其趣,则有益于经学者正不浅。”作为经学家的焦循对诗词之道甚具识见。他强调,诗词审美表现要以引人兴趣、移人性情为旨归,而这正是文学可补经学的关节处。李佳《左庵词话》云:“词以意趣为主,意趣不高不雅,虽字句工颖,无足尚也。意能迥不犹人最佳。东坡词最有新意,白石词最有雅意。”李佳高倡作词以崇尚意趣为旨,强调由“意”而“趣”,他标示出“趣”为词之本,字句为词之表,概括意趣的审美本质特征要高雅。李佳在词论史上又一次对词趣审美特征明确提出了要求。蔡宗茂《拜石山房词钞序》云:“冷趣相洽,清词载搜,洗其淫哇,濯以藻丽,既昭藐而荡气,亦芬芳而悦魂。”蔡宗茂在为顾翰所编《词钞》作序中论及到词趣创造。他认为,在清词丽句中突然浇以“冷趣”,是能起到比一般稳步性地抒情言意更好的艺术效果的,它荡人心气,愉悦人的精神。孙麟趾《词径》云:“陈言满纸,人云亦云,有何趣味。若目中未曾见者,忽焉睹之,则不觉拍案起舞矣,故贵新。”孙麟趾也对词作提出了要有“趣味”的审美要求,为此,他主张作词用语要新,要道人所未曾道,从而产生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孙麟趾在陈椒峰论词要有新意的基础上,将对词“新”的探讨往前挪了一步。之后,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词宜雅矣,而尤贵得趣。雅而不趣,是古乐府。趣而不雅,是南北曲。李唐、五代多雅趣并擅之作。雅如美人之貌,趣是美人之态。有貌无态,如皋不笑,终觉寡情。有态无貌,东施效颦,亦将却步。”谢章铤抓住词雅与词趣的辩证关系详细展开阐述。他认为,“雅”是词作在格调上所追求的,“趣”则是词作在主旨、意蕴的表现上所必然伴随的。谢章铤从两者的偏胜上来界定古乐府、南北曲与唐五代词的差别,认为古乐府格调雅正但意趣不显,南北朝歌谣俚曲趣味盎然但却格调欠雅,惟唐五代词雅、趣兼擅互融。他并比譬词雅如“美人之貌”,即目可见;词趣则如“美人之态”,惟通过感知体察可知。此论形象而切中地道出了词趣的特征。其又云:“然而文则必求称体:诗不可似词,词不可似曲,词似曲则靡而易俚,似诗则矜而寡趣,均非当行之技。”谢章铤还从词与诗、与曲的区别,词应求本色当行上论及词趣。他指出,如果词像曲一样,则必然流于浮靡而俚俗;像诗一样,则会显得矜持而少情趣,在艺术表现上缺乏伸展扩张和引人兴趣的特征。谢章铤对词体与诗趣相互关系的论述,将清人对词趣的考察推向了一个甚具理论意味的层面,他将“趣”标示为词作审美的最质性的特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美成词,有前后若不相蒙者,正是顿挫之妙。如《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沉郁顿挫中别饶蕴借。后人为词,好作尽头语,令人一览无余,有何趣味?”陈廷焯和孙麟趾一样,也对词作提出了要有“趣味”的审美要求,他借论评周邦彦词作,道出了词作须具备两方面审美的系统特征,一是在词律上应具“顿挫”之妙,二是在情感寄托上应“沉郁”,如此,才可使词作委婉蕴藉,含蓄深致。陈廷焯将词作趣味的生成定位在了“沉郁顿挫”的艺术原则之上。沈祥龙是清代论词趣最为集中的词论家。其《论词随笔》云:“宋人选词,多以雅名,俗俚固非雅,即过于秾艳,亦与雅远。
[摘要]中国古典词学“趣”范畴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批评层面对“趣”的承传运用;二是理论层面对“趣”的承传阐说。在第一个维面,“趣”在北宋前期进入到词学批评中,发展到清代,成为人们品评词人词作的主要审美范畴;在第二个维面,古典词学对“趣”的阐说集中在清代,其内容主要体现为对词趣审美内涵、特征、形态、生成与创造等方面的论析。上述两个维面,将“趣”作为古典词学审美范畴的内涵展现出来。
[关键词]古典词学;“趣”范畴;承传
扩展阅读
- 1古典文化
- 2古典诗吟唱
- 3古典文学
- 4古典诗歌语言特征
- 5古典时代雅典婚配模式
- 6古典词学趣范畴承传考察
- 7古典园林建筑在古典园林中的作用
- 8古典艺术风格
- 9古典经济学
- 10古典诗吟唱经验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