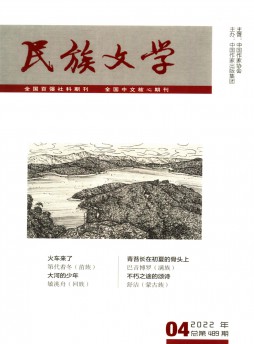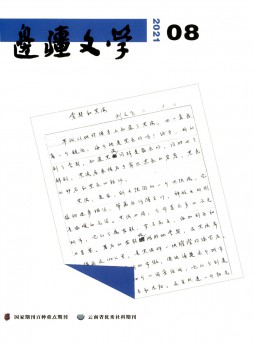文学翻译论文范文
前言:写作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探索。我们为你提供了8篇不同风格的文学翻译论文参考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给你带来宝贵的参考价值,敬请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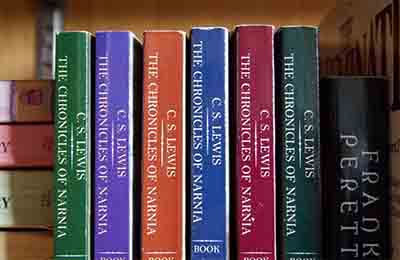
儿童翻译损失的文学翻译论文
一、儿童文学的定义与儿童文学翻译的特点
儿童文学(literatureforchildren),是一个历史概念,至今尚无统一的概念,它是指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王泉根教授认为,“儿童文学是为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服务的、具有适合儿童审美意识与心理发展的艺术特征、有益于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学。”[3]它既有一般文学的共性,又有其特性,表现为结构单纯、情节紧凑、故事性强等特点,既简单又具备幻想的成分,同时又能够刺激想象力,受到儿童的欢迎。虽然称为儿童文学,但它却并不是由儿童生产的,而是一种整体上由成人写给小孩看的文学。它寄寓着成人社会对未来一代的文化期待。基于教育儿童的需要,产生了儿童文学,因此,儿童文学难免烙下了教育性的痕迹,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是文学性与教育性的和谐统一体,它为儿童提供滋养的同时,也为成人提供着审美愉悦。总之,儿童文学的受众对象特殊,语言和故事情节貌似简单,但对已经很社会化的成人译者而言,进行翻译和改写,却并不是预想得那样简单。虽然儿童文学属于文学的一种,却有着很明显的特殊性,翻译时在遵循文学翻译的一般规律的同时,更要兼顾这种特殊性的需求,即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务必兼顾译文的读者对象和源语文本。对儿童译作而言,看译文的人所得的感受、所起的反应,应该与读源文的人是一样的,这样就基本达到了儿童视野期待的翻译要求。然而译者却都是成人,换句话说,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是成人翻译给儿童的作品,这就要求“译者要站在儿童立场上,用儿童观点去透视原文,怀着一颗童心去鉴赏,选用浅显易懂的语言”[4]。翻译儿童文学,作为成人的译者需要俯身低就,“蹲下来和孩子对话”,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思考、理解和表达以获得更好的接受,这样,译作才能引领儿童走向对世界文学作品的认知,达到儿童文学翻译应有的目的。因此,儿童文学翻译浅显易懂的要求并不意味着这一语言转换过程是简单的,相反地,对于思想已经复杂化的成人译者而言,这更是一种挑战,对译者的翻译素养要求更高。
二、儿童文学翻译损失枚举
翻译损失是翻译过程中信息、意义、语用功能、文化因素、审美形式及其功能的丧失,具有不可避免性。[5]儿童文学的翻译虽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但翻译损失的存在也不例外,甚至于损失更甚。为了能够更直观地感受超欠额带来的翻译损失,下面将摘取一些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中的实例予以分析解读,并提出对应补偿策略。
(一)超额翻译损失现象在儿童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为了让读者能够理解上下文中的联系,唯恐解释不到位、指称不明确,对词语加以修饰限定,将原本就已理解错误的东西搞成了错上加错。例Popwasalwaysonthelook-out,andalmostbeforeittouchedthegroundhe’dhaveitinhissackanddowntothevestrywithit.这是选自美国现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罗伯特•劳森(RobertLawson)的《本和我》第二章中的一句话。这部作品在国内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的三个译本,是一本很受国内儿童读者喜爱的作品。在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中,译者将这句话翻译成:“我的弟弟波普总是在一旁注视着,有栗子掉下来时,还没落地,他就赶紧把它装进口袋里,然后钻进小礼拜室里。”译文中的“我的弟弟”,是译者有意添加的同位语,想进一步给小读者交代清楚“Pop”是谁。作为一篇动物故事题材的小说,小老鼠Amos在故事一开头就交代了父母给它们兄弟姐妹们起名字的情况,分别是按照二十六个字母的顺序起的名字。身为长子,我叫埃莫斯(Amos),以此类推,后面的依次取名叫芭丝谢芭(Bathsheba)、克劳德(Claude)、丹尼尔(Danniel)……一直到色诺芬(Xenophon)、约瑟拜尔(Ysobel)和泽纳斯(Zenas)。在第二章中,文中的“我”埃莫斯因为家境贫寒,被逼出道,照此推算,Pop应该年纪尚小,回忆起家中往日取暖的情形,让小弟Pop出去找东西来供全家人取暖,不合逻辑。所以,译者在这里对Pop的理解肯定有问题。但译者并没有一笔带过,而是企图自圆其说或是想让小读者明白此处出现的新人物到底是谁,便堂而皇之地加上了“我的弟弟”来附加说明。简单粗暴地超额处理是无助于读者理解的,反而却进一步暴露出译者的不安和搪塞。这里的Pop应该如何理解呢?在词典中,可以查到[p?p],作为普通名词解释为“流行音乐,砰然声”等,专有名词做“波普”解,此外便是动词、形容词、副词等词性。而实际上,这里的Pop应该读作[pɑp],即中文中的“爸爸”。只有爸爸才会为一家人奔波忙碌,在冬季里寻找热源设法取暖,这在逻辑上也能讲得通。处理得亲切或者调皮一点,可以翻译成“老爹”。动画片《成龙历险记》中的“老爹”也是儿童非常熟悉的人物,对应起来,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一位睿智的长者形象。译者的这种过犹不及的超额翻译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倒暴露了自己企图瞒天过海不负责任的态度。超额翻译损失的现象在《绿山墙的安妮》这本儿童文学译著中同样有所发生。该儿童小说以加拿大为背景,反映加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心,被认为是“无以伦比的加拿大小说”。例MarinafoundAnnefacedownwardonherbed,cryingbitterly,quiteobliviousofmuddybootsonacleancounterpane.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译本中,译者的翻译是:“玛丽拉发现安妮脸朝下伏在床上伤心地哭着,一条十分干净的床单印上了几个泥靴印,相当醒目。”首先,这里的facedownward被译成了“脸朝下伏在”,“伏”字是个过于正式的表达,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儿童读者受众的语言水平。其次,“十分干净”中的“十分”二字是译者加进去的,或许是为了和干净一起凑够四字格来增强韵律感,但却过分放大了语境,违背了源文的意思。再次,该句翻译变换了描述对象,却依然采用一个单句,对小读者的简单思维能力照顾不到位。伏就是趴的意思,也可以组成趴伏这样的词组,其他两个译本翻译成趴在床上,可能是受了彼此译文的影响。其实这里讲的是安妮把脸埋在床上,脸既然埋在床上,肯定就是朝下的,这样翻译,就可以打破原有一些译文亦步亦趋的做法。这句话可以依照源文句式依次往下翻译,将句子断得更短一些,方便读者理解。可以译为:“马瑞拉发现安妮把脸埋在床上,痛哭流涕,一双沾满泥巴的靴子弄脏了干净的床单,却浑然不觉。”当然,笔者觉得任珊珊在其译本里将cryingbitterly译为“呜呜地哭”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这种翻译加强了语音效果,营造了悲伤的氛围,也符合儿童对拟声词偏好的期待。
(二)欠额翻译损失现象无论是超额翻译还是欠额翻译均会造成翻译损失,如果说超额翻译是译者唯恐表述不够清楚,解释唯恐读者不够理解,而在源语基础上不断衍生,那么欠额则是为了译语的流畅和简洁而故意略去本该译出的意义。欠额翻译,往往是译者无视译文的理解性与可读性,或过高地估计了译语读者的知识,以至于译文读者在译语中得不到理解源文意思所必需的信息,因为源语信息被译者忽视或被打了不应有的折扣。[8]下文同样以《绿山墙的安妮》为例来分析译者是如何遗漏源文信息,造成欠额翻译现象的。例PrissyAndrewstoldmethatshesatuphalfthenighteverynightofherEntranceweekandcrammedfordearlife……在《绿山墙的安妮》华文出版社的版本中[9]227,任珊珊对上面这句话的处理,可以说是个败笔。译为:“皮瑞莎安德鲁斯说她考试之前差不多总是半夜醒来,仓促地恶补。”Entranceweek在这里被译成了考试之前,显得太过宽泛,因为考前一天或者一月都算是考前,信息传达得不够精确。everynight在这句话中被省去未译,而satup被译作“半夜醒来”。半夜醒来是指睡了一觉受到打扰或是心神不宁而起床,总之是先睡了一觉,但situp的实际意思是“熬夜,迟睡,端坐”,根本没有先睡一觉的意思。译者在这句话翻译的过程中,对信息作了太多的精简处理,有违源文意思,也无法准确传递给读者需要了解到的具体信息,欠额翻译造成的损失很是明显。这句话可以完整地译为:“普瑞西•安德鲁斯跟我说,在入学考试那一周,她每晚都要熬半夜,拼命地死记硬背。”超额翻译与欠额翻译并非总是一个单纯的文本,有时可能还会以混合型文本的类型出现。在一句话中,为了让读者读起来更像在读本族语,而略去了需要译出的词语,却把单个词语就能表达清楚的意义重复修饰,采用译入语习惯放大了一些源语中没有的信息。例Istumbledhome,embarrassedandconfused,myheartcompletelycrackedopen.这句话选自文德琳•范•德拉安南的儿童小说Flipped,在中国华侨出版社的译本中,陈常歌将其翻译成:“我跌跌撞撞地跑回家,满心尴尬与困惑。我的心已经碎成了片。”这是对女主人公朱莉受到打击以后的描述。短短的一句话,译者采用了“跌跌撞撞和满心尴尬”两个极其归化的四字格进行了翻译,虽然四字格具有言简意赅、整齐匀称、形象生动的特点,也是汉语中特有的词语组合现象,颇受有些作者和译者的青睐和喜爱,但是滥用四字格也不见得就能赢得读者的认同。在摘录的这句话中,跌跌跌撞撞地跑回家,“跑”字是译者添加的,这是杜撰,stumble是“绊倒,蹒跚和牵绊”的意思,到底是跑回家的还是走回家的,或者是连滚带爬地回去的,源语采用的是模糊表达,也符合逻辑,一个备受打击的人浑浑噩噩到了家,却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去的,如果采用“跑”回去,就把这种无意识状态给抹杀了。但在处理后半句时,译者没有翻译出“completely”,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所以,短短的一句话,译者的取舍混合运用了超欠额,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以言害意的作法,造成了翻译的损失。这句话可以译成:“我跌跌绊绊地回到家中,觉得既尴尬又迷茫,心儿像是给完全撕裂开来。”这样翻译,一种撕心裂肺的难受和眩晕不知如何到家的情景会更为明朗一些。
三、儿童文学翻译损失探析与补偿
儿童文学翻译损失的发生首先是由语言本身的差异造成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英汉两种语言分属印欧语系和藏汉语系,由于受历史文化积淀和所处语言环境的差异,在语音、词汇、句法、表现方法等方面大相径庭,而翻译不只是语言形式的转换,除了语言形式本身所承载的语义信息,还有语言形式生成的美感及整合在形式之外的艺术意象。许多论文从语音、意义和文化意蕴等方面来探讨补偿方法,就是因为英汉两种语言有着固有的差异,很难实现“移瓶注酒”审美功能再现。儿童文学翻译损失与期待视野差异息息相关。儿童文学翻译毕竟是由成人译给儿童看的,翻译的主体是成人,阅读的主体却是儿童,一项活动涉及到了两个不同的主体,期待视野必然有差异。德国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尧斯对期待视野作出以下定义,即接受者在以往鉴赏中获得并积淀下来的对艺术作品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的认识理解。作为成人的译者很难在期待视野上与儿童读者达成一致与融合,这难免造成翻译的损失,而损失的现象就是译者对读者期待要么过高,造成欠额翻译,译文处理过于精简,信息传递单薄,不利于读者理解和认知;要么对阅读对象的认知水平和层次把握不准,看得太低,企图通过大量修饰和补充让读者理解,使得译文累赘繁杂,造成超额翻译,也不利于儿童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基于以上的探讨和分析,可以看出,要实现儿童文学翻译损失的补偿,需要对两种语言差异有深刻的认识,并在成人和儿童两者之间进行期待视野的矛盾调和。文中提到的超欠额翻译实例,涉及到了词汇和句法翻译的过量和不足,给儿童读者造成了意象上的差异。针对超额翻译第一例添加同位语的现象,删减了同位语,通过逻辑推断,改正了对于源语的误译,并将较为死板的词语换成了轻松调皮的称谓,更能迎合小读者的心理期待;而对于第二例超额翻译,剔除了过度修饰,让译文回归平实,符合当时源语描述的场景。在欠额翻译第一例中,补回了遗漏掉的“每晚”这样一个副词短语,使得译文表达更符合原作的意图,一个早不忙,夜慌张的形象跃然纸上。第二例欠额翻译副词“完全”的补充,更为恰当地描述了受到打击后的感受,让读者能够感同身受。受单句分析的局限,文中所列实例补偿都是在句中进行了直接补偿。对翻译超额和欠额的现象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词汇和句法的层面,仅仅追求字词对等是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必要添加的时候予以灵活处理,可以增加童趣,满足文本和语境需要。如:Down,down,down.Wouldthefallnevercometoanend!这是选自《爱丽斯漫游奇境记》中的一句话,赵元任先生将其译为:“掉啊,掉啊,掉啊!这一跤怎么一辈子摔不完了吗!”加入孩子喜闻乐见的语气词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这里对于“啊”这个语气词的添加就算不得超额翻译,而是按需添加,本来往下掉是令人心生恐惧的感觉,这样翻译,读来一下子让人轻松了许多,有助于读者去体验主人公当时的心理,给儿童读者带来玩耍娱乐的愉悦感。
外国文学翻译论文
一、民国期刊翻译概况
民国时期刊物众多,具体来看,登载外国文学译文的刊物主要有三类:首先是一般性的杂志,虽然不是专门的文学期刊或翻译刊物,但出于文化启蒙以及促进社会变革等目的,也刊载了一定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类刊物的代表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现代》等;其次是文艺期刊,尤其是文学社团的机关刊物,如文学研究社的《文学旬刊》,创造社的《创造》季刊,新月社的《新月》,未名社的《莽原》,学衡派的《学衡》等,都将外国文学的翻译作为刊物的重要内容;最后在30年代还出现了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杂志如《译文》《西洋文学》等,为该时期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以上各类刊物由于译介外国文学的目的不同,以及文学倾向的差异等,在译介的方式、内容和侧重点方面也多有不同。《新青年》在民国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中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据统计,1915~1921年的6年时间里,该杂志共发表了约128篇翻译作品。其中日本文学作品数量最多,共有35篇,占全部翻译作品的27%。其次是俄苏文学作品,共有18篇,占总数的14%,重点译介的作家有易卜生、王尔德、莫泊桑、屠格涅夫、泰戈尔等,译者则包括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名家。在它之前,期刊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主要受利益驱动,以满足读者需求为目的,并不太看重文学性,不以艺术价值为评判标准,而相对注重文学的可读性和娱乐性,对国外通俗文学译介较多。但自《新青年》开始,文学翻译更加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性,将外来文学翻译作为引进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办刊之初,陈独秀就提出“,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新青年》曾先后翻译了屠格涅夫、王尔德、易卜生等国外名家作品,很多都是国内的首次翻译。对易卜生作品的一系列翻译,更突出体现了该杂志的翻译特点。胡适对此有准确的评述,《新青年》译介易卜生,“在于借(易卜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他们“注意的易卜生并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
茅盾也指出了这一点,认为在《新青年》的翻译中,易卜生并不是作为戏剧家和作家,而是“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新运动的象征”。除一般性杂志之外,在民国期刊中,对外国文学翻译起到更大作用的是文艺期刊。如有学者所说,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每期都有几篇翻译文学的作品发表”,而一些文学社团的机关刊物,如《小说月报》《创造》季刊、《新月》《学衡》等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1921年茅盾担任主编后,改变了原有的编辑方针,特别提出“移译西欧名著使读者得见某派面目之一斑,不起空中楼阁之憾,尤为重要”。由此,《小说月报》成为民国时期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阵地,仅1921~1931年的10年间,该杂志就译介了外国文学作品800余篇,涉及的作家来自几十个国家。同时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其翻译也反映出了该社团的文学倾向,即重视俄国、法国、北欧等国家尤其是“被损害民族国家”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作为创造社的刊物《,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等更多表现出重浪漫主义的倾向,其译介重点包括了卢梭、歌德、海涅、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等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由于创造社成员如郁达夫、成仿吾等都曾留学日本,杂志对日本文学的译介也占了很大比重。《新月》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主要集中在英美文学方面,这与新月社成员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的英美留学背景有关,由于深受英美文学的浸染和影响,他们在对外来文学的翻译中侧重选择英美近现代作家作品,表现出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同的倾向。其译介重点有英国作家济慈、哈代、曼斯菲尔德等,对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如艾略特、伍尔夫、劳伦斯、奥尼尔等人的作品也多有翻译,填补了国内此前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翻译中的空白。除此之外,还有未名社创办的《未名》半月刊、《莽原》周刊等,对苏联、日本以及法国文学等多有译介。三四十年代,一方面原有的文学期刊因各种原因终刊,如《未名》1930年停刊,《新月》1933年停刊《,学衡》也出至1933年第79期停刊;另一方面抗日战争爆发,社会局势混乱,文学翻译一度出现沉寂。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多个专门刊载译文的期刊,如《译文》《西洋文学》等,使外国文学翻译在艰难的时期仍然得以持续。《译文》创刊于1934年,是我国最早的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刊物,而创刊目的则如茅盾所说,“是供少数真正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在翻译题材选择方面,该刊没有特定的限制,但从其发表的文章来看,杂志在广泛涉及各国文学的同时,仍然侧重苏联文学以及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这也反映了刊物最早的发起者、主编鲁迅的文学倾向和主张。《西洋文学》存在时间较短,自1940年9月创刊,仅出版了10期,但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译文选择方面,《西洋文学》更看重诗歌,曾刊发多位英国诗人作品,如拜伦、雪莱、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叶芝、乔伊斯等,尤其是对于乔伊斯的译介(该刊译为“乔易士”),在乔伊斯去世的两个月后制作完成,包括了作家小传、诗歌、小说、评论等,内容全面,反映出了当时国内期刊对于国外当代文学事件的迅速反应,同时也体现了编者的独特眼光。
二、民国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编辑策略
民国时期各类期刊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一方面继承了晚清以来文学翻译的余波,另一方面也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文化需求有关,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达到文化与文学变革的目的,当时的文人学者大力引介外来文学,并将文学作为传递新文化、新思想的有效工具。然而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毕竟存在着语言与文化的隔膜,为此各期刊在外国文学译文的编辑方面也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策略,从而有效地消除阅读障碍,推动了作品在读者中的阅读与接受。以“专号”“特辑”等方式对重点作家作品做出推介,是民国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策略。相对于书籍出版,期刊的翻译更加迅捷、及时,但也存在着译介零散、不系统的问题,而有关外国文学的专号、特辑的出现,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专号(特辑)多围绕特定作家或主题进行,如最早由《新青年》推出的“易卜生专号”,是我国期刊发展史上第一个作家专号,为此后的期刊译介外国文学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小说月报》先后推出安徒生、拜伦、罗曼•罗兰等作家专号,《西洋文学》推出“拜伦专栏”“乔易士特辑”“叶芝特辑”。也有专号围绕更广泛的主题进行,如《小说月报》推出的俄国文学、法国文学、被损害民族文学、非战文学专号等。“专号”“特辑”的出现,一方面与编译者的文学倾向有关,体现出编者在一定时期内对外国文学的关注重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期刊本身对外界事件的迅速反应。1932年高尔斯华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年《现代》刊登“约翰•高尔斯华绥特辑”。1933年2月萧伯纳来华,在接下来的3月份国内期刊中出现3个专号,分别是《论语》“萧伯纳游华专号”、《青年界》“萧伯纳来华纪念”、以及《矛盾》“萧伯纳氏来华纪念特辑”。一些外国著名作家的诞辰、纪念日等也成为开设专号的好时机,1924年拜伦逝世100周年《,小说月报》推出纪念号“拜伦专辑”;1923年,《创造》也推出了“雪莱纪念号”;类似的还有1932年《现代》的“司各特百年祭特辑”等。从以上专号的内容来看,以国外近现代作家为主,但也有例外,如莎士比亚特辑在民国期刊中就曾多次出现,1937年《新演剧》《戏剧时代》分别推出“莎士比亚特辑”,1941年《戏剧春秋》为莎士比亚逝世325年推出“莎士比亚纪念辑”,1948年《文潮月刊》也推出了“莎翁专辑”。
特辑、专号往往包括了作家小传、作品译文、相关评论等内容,对作家作品做出了更为立体和深入的呈现,从而有效推动了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以“编者注”或“译者注”的形式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介绍,也是民国期刊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策略。虽然自晚清以来,随着翻译业务的逐渐发展,国内读者早已接触到国外的文学,但民国期刊中出现的大多数作家作品对当时读者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为了消除隔膜,更有效地推动外来文化与思想的传播,各期刊往往会在刊发译文的同时,对作家作品加以说明,内容一般包括作家生平、作品介绍、创作背景等,编者(或译者)有时也会对作品做出点评,这些或长或短的注解构成了读者在阅读译文之前的“期待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读者对特定作品的理解和接受。1923年第4期《创造》季刊登载了多首雪莱诗歌译文,诗前都有一段文字,不仅介绍了诗歌创作的时间、地点、缘起,同时也多有短评,如认为《西风歌》(OdetotheWestWind)“原诗音调极其雄厚,真如暴风驰骋,有但丁之遗风”。而更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的是《学衡》的翻译,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学衡》编辑经常会加入“编者注”,有意识地引导读者阅读。以1925年第39期华兹华斯诗歌翻译为例,在译文前编者先以“按语”的形式对华氏文风做出介绍,认为其诗“高旷之胸襟,冲和之天趣,而以简洁明显之词句出之,盖有类乎吾国之陶渊明、王右丞、白香山三家之诗也”。将华兹华斯与中国古典诗人相提并论。而对于下文所译“露西”组诗第二首的解读,“按语”也从中国古典诗歌托物喻志的传统出发,认为该诗“盖威志威斯(华兹华斯)理想之所寄托”。通过“编者按”的形式《,学衡》编辑对华兹华斯这位浪漫主义诗人“改头换面”,使其带有了中国古典诗人的色彩,并进一步实现了借外国文学来彰显古典文学价值的目的。图文并茂,以插图的形式使读者获得对外国文学更直观的认识,是民国期刊译介和推广外国作家作品的又一个策略。插图的采用一方面有助于读者对外国作家产生直观印象,消除距离感,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作家形象的深入人心,因此成为民国期刊在推介外国文学时经常采用的编辑策略。如1923年14卷9号的《小说月报》推出“太戈尔号”,封面即印有泰戈尔像,刊内除登载泰戈尔作品译文以及各类评论文章之外,还附有7幅插图,分别是“太戈尔像”(两色版)“、一八七七年时的太戈尔”“壮年时的太戈尔”“幼年的太戈尔对他父亲唱歌”“太戈尔的手迹”“在美国时的太戈尔”(2幅)。1924年15卷4号《小说月报》刊登“诗人拜伦的百年祭”,其中也加入了6幅插图,包括了拜伦不同时期的画像,诗人手迹以及故居图片等。插图的加入使纪念特辑有点有面,诗人形象更加生动可感,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外国作家作品在国内读者中的传播。1925年鲁迅的小说《伤逝》中就曾提到“一张铜版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同时还提到了“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伤逝》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其中提到的这一细节却真实反映了杂志刊登的作家肖像在读者中的影响。一些外国作家如拜伦、雪莱等的偶像气质,及其在青年读者心中的深刻影响,都与期刊中频繁出现的作家肖像有关。
三、民国期刊与外国文学译介
大量期刊的存在及其对翻译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国时期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传播。一方面,与书籍出版相比,期刊的周期短、价格低廉,覆盖的读者群体也更广泛,通过期刊的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在国内传播的时间大大缩短,同时也有机会面对更多的受众。另一方面,期刊的包容性与灵活性,也使其容纳了更多样的外国文学作品,从而使国内文学翻译更加丰富和多元化。民国期刊对于外国文学译作的大量需求,在客观上促进了译者队伍的发展。从译者身份来看,当时期刊译文的来源主要有3种途径,一是名家征稿,现代文学史上知名的学者、作家如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闻一多、沈雁冰等,同时也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名家,他们大多有国外留学的背景,精通一门或几门外语,因此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也为多家杂志供稿。张芝联在回忆40年代的杂志编辑时,就提到“当时滞留上海的著名翻译家”,以及“西南联大的一些成名译者”都曾为《西洋文学》提供稿件。另一种来源是期刊编辑的译稿以及自组稿件,如前文所述《学衡》出现的一诗多译,主要译者都是主编吴宓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期刊所选译文则是他们在翻译课上的作业,其中陈铨、贺麟、张荫麟等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读者投稿,一般在推出系统的翻译专号之前,期刊都会提前发出通知向读者征稿,如《论语》第52期发出消息征集译文,并在第56期时推出了“西洋幽默专号”。
儿童文学翻译博硕论文研究
1.引言
当下,家长更为重视儿童教育,为满足家长和儿童的需求,翻译出版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相比之下,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却长期得不到重视,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得不到有效理论指导,译作良莠不齐。为促进儿童文学翻译实践,给孩子提供更高质量的译作,必须进行系统深入的儿童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儿童文学翻译博硕论文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知网的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博硕论文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理论视角,以期对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促进作用。
2.研究方法
笔者收集了中国知网2005年至2014年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视角相关的硕士论文338篇。将这些论文分为传统理论视角和特定理论视角两大类。传统研究视角39篇,其中包括31篇语言视角,8篇文化视角。特定理论研究视角299篇,其中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94篇,描写学派视角52篇,美学/接受美学视角62篇,语言学视角25篇,功能对等理论视角23篇,哲学视角12篇,生态学视角5篇,计算机技术辅助视角5篇,心理学视角4篇,伦理学视角3篇,“信达雅”视角2篇,社会学视角1篇,信息学视角1篇,另外10篇归入其他视角,主要包括一些翻译家的翻译理论。
3.分析
3.1总体分析笔者发现2005年至2014年有一篇针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博士论文,其他皆为硕士论文,这说明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论文数量来看,2005~2014年分别为4、11、12、13、23、22、30、66、79、78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各类论文的数量上可以看出,特定理论视角研究多于传统理论视角研究,特别是功能主义/目的论视角和美学/接受美学视角为主流,另外也有一些崭新的视角,但数量较少。
3.2分类分析
3.2.1传统视角分析
伦理模式的文学翻译论文
方华文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美好的追求。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着社会形态的性质、面貌和人们的精神活动。世界各国人民在文学艺术上的优秀创造也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借鉴。而文学翻译工作对于提高我国公民的文化素质以及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该观点只谈到了外译中的情况,即把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翻译给中国读者的过程不仅是呈现“他者”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与“他者”交际的过程,在这个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过程中,译者推动了互为“他者”的中外双方之间的跨文化合作,同时使中国读者受益。实际上,该观点已经蕴含了切斯特曼的交际伦理思想。文学翻译的复杂性和困难度要大于非文学翻译,所以要求译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归纳起来,方华文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必须具备进步的思想品质。
方华文认为译者不能单凭个人的好恶进行选材,而应该根据社会的需要和祖国的需要加以取舍,只译有利于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健康作品,而不应翻译反动落后、黄色淫情的作品。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明的时代,进步的时代,健康的时代,但也不乏低级趣味的文学作品。作为翻译工作者,必须树立健康向上的人生观,热爱自己的祖国,善于区分正确与错误,区分思想崇高的作品及下流淫秽的作品,不为了经济利益的得失丧失自己的立场。文学翻译工作者不仅把文学作品当作艺术品,还将其视为政治、思想、生活修养的教科书,译出高品质的作品,服务于我国的各项事业。我们可以看到,该素质要求译者译有所为,亦有所不为,选择原文本时除了考虑个人兴趣,还须考虑社会和国家的需要,为社会和祖国服务,同时履行翻译的职业道德和个人道德。这已蕴含了切斯特曼的服务伦理和承诺伦理思想。
2.必须具备深厚的语言基本功,掌握驾驭语言的技巧。
方华文认为从事翻译工作,特别是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译者对语言的了解应该是深入的,而不应该停留在肤浅的层次。语言在翻译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是信息的载体、内容的外形,是交际的主要手段。译者应该善于捕捉语言发送的信息,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全部意义,赋予译文漂亮的外衣。林纾的译文在当时之所以赢得了那么多的读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译文语言精美。当然,我们并非要片面地强调“语言精美”而置原文的实际含义于不顾。一个成功的译者,是能把二者统一起来,既忠实于原文(以吃透原文的词句为前提),又有能给人以美感的译文。方华文认为,立意走这条路的人在未动笔之前,应多读外语的文学书籍,积累词汇及其他语言知识,还要多读母语的文学作品,必要时亦应经常练笔写写文章,这样才能把书译得好。该素质要求译者遵守再现伦理,忠实地再现原文的全部意义,即再现原文、作者的意图以及原文的文化等;同时要求译者服务目标语读者,使译文符合目标语规范,符合目标语读者的期待,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这也蕴含了切斯特曼的基于规范的伦理思想。
3.应该具备一定的艺术想象力和审美趣味。
方华文认为,文学翻译活动和文学活动一样,也是艺术活动,翻译作品亦是艺术品。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人,应该具备艺术想象的能力和审美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运用贯穿于整个翻译活动的始末。起始阶段,译者应该善于运用艺术想象力,穿破语言的外壳去了解原文的实质,挖掘出真正的“神韵”。真正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事物的概念和情节的记叙,还应该具备能够吸引读者的艺术意境,即通过艺术的形象,使读者对书中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强烈的感情。译者必须有能力置身于这种“艺术意境”,在和原文中的人物“共鸣”之后,才算了解了原文。当然,这种与原作的“共鸣”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其中之一就是要研究原作的背景知识,“吃透”原作的内容。译者的大脑并非空白的,原先就应该具有一定数量的艺术细胞,贮藏着一些艺术影像,这些影像都是由生活中提取出来的。拿我们中国的译者来说,从幼年时代便开始接触《三字经》以及唐诗这样的文学艺术品,并且把它们贮藏在记忆库里。除此以外,译者还会记下无数其他的艺术真实和艺术影像。在接触到原作后,译者大脑里的艺术细胞被激活,与原作里的艺术因素产生碰撞、吸收和凝聚,构划出了以原作里的艺术形象为模本的新的艺术形象。这一过程就是文学翻译的再创造过程。在文学翻译活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即表现原作的阶段,译者也必须具有艺术想象力,准确、生动地把聚合在大脑中的艺术形象展现出来。在以上吸收和再创造的过程里,已经体现出了译者的审美趣味。译者从原作的语言中分析出内含的艺术真实,第二步就是再现这一艺术真实。译者在完成第二步骤时,必定会加入自己的审美趣味。由于每个译者的审美趣味都有着自身的特色,或俗或雅、或浓或淡,所以他们的译文修辞手法丰富多彩、风格千姿百态。译者的审美趣味由诸多因素决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个人的性情、社会地位、文化素养、世界观等。审美趣味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长期培养出来的。译者的审美趣味越深厚,他的译品就越具思想性、越有艺术情味。所以,每一位文学翻译工作者平时都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加强文化修养。我们可以看到,该素质是文学翻译者更好地实现再现伦理和服务伦理的必备条件。
4.必须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
朝鲜文学翻译论文
一、关于《作风》杂志
《作风》的开篇诗中,有这样的段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习俗里开始他底奋斗,像铁牢里雄狮的狂吼欲恢复他底自由;倘有人因他而奋起追求,倘有人因他而打破幽囚,他只感谢,他只感谢志友,他只感谢,因他得和志友来同把这革新的责任担负。在这段诗里,反抗与斗争的意味相当明显。与此相呼应,2003年金田兵在回忆《作风》的内容时,有如下的表述:“内容着重于反战、反掠夺及反映放逐、贫困生活的作品。当时是针对侵略战争,敌伪实施的‘国兵法’、‘抓劳工’、‘思想矫正法’以及‘出荷’、‘配给制度’等形势翻译的。”[1](PP.101-102)由此可见,和内地的弱小民族翻译作品集一样,伪满洲国的《作风》,也在通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来曲折地、间接地回应和控诉处于伪满洲国殖民统治之下的中国人们丧国丧权的政治和生活现状。这里需要特别谈一下放逐题材的作品,也就是在附表中被归类为“望乡”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以同情的口吻描写被放逐出祖国的漂泊者们的思乡之情。它们虽然并不直接对应伪满中国人的处境,也与弱小民族文学的概念有冲突之处,却能间接地传递伪满中国人思念祖国、渴望重新成为祖国一部分的情怀。
①具体来说,在伪满的中国人,并非从祖国放逐到伪满洲国,而是在自己的家乡被殖民,所以难称“放逐”;而《作风》中许多被放逐者,比如白俄和墨西哥人,都是因为家乡的解放革命而被迫流亡的被革命对象,所以同情他们的流亡,事实上恰恰与“弱小民族”概念所内含的民族解放独立精神相左。但是,在一方面涌动着难以压抑的民族主义情怀;另一方面却不能直接批判殖民主义的伪满洲国,放逐成为传递中国人向往祖国之心的替代性题材。这种以他国人民的放逐题材替代本国民族主义书写的策略,不仅出现在翻译作品中,也出现在伪满中国作家的创作作品中。举例来说,《作风》同人作家石军在194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混血儿》,就曾因“通过亡命满洲的白俄人的痛苦和感慨来唤起满洲民众的祖国意识”而遭到检举。②总体来说,金田兵的总结与我最初阅读《作风》杂志的感受基本一致。从文末的附表中可以看出,被放逐者的反战和望乡之情,以及底层人民生活的贫困,的确是《作风》所选作品中最普遍和突出的主题。而作品间主题的对应性,又更加渲染了单篇作品的进步意义。一些本来可以有多种诠释的作品,因其中进步的主题能和其它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相呼应,而使阅读整本杂志的读者有可能将其作进步方向的解读。举例来说,《雪莱与现代》这篇文学评论,作者是日本学者横山有策,以30年代中国的标准来看,并不能算弱小民族文学作品。但是评论全篇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来解释雪莱作品的意义,不仅本身属于进步作品,而且在《作风》杂志中紧随雪莱的散文《圆形竞技场》之后,还可以影响到读者对雪莱散文的解读。雪莱的这篇作品,本来是一篇含义模糊而丰富的哲学性散文,在《雪莱与现代》的观照下,其自由解放的思想得以凸显。遗憾的是,《雪莱与现代》一文,因为思想倾向过于激进,在《作风》出版后不久就被伪满洲国当局勒令删除。[1](P.102)关于其它作品间主题的呼应,将在下文讨论朝鲜小说的翻译时详述。正如《作风》的编者所说,这样大规模的翻译作品的募集,在当时的伪满洲国还属首次。在那前后,从1939年到1941年,伪满洲国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翻译作品集,比如《世界著名小说选》[6]、《世界名小说选》(1-5)[7],《近代世界诗选》[8]等,但这几本都只是将已经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翻译作品编选在一起而已。与此不同,《作风》杂志是由编辑者先联络散落在东北各地的有翻译能力的作者,在他们同意投稿之后,由他们自选作品进行翻译。
③因此,这本翻译集包括了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并且大多从原文直接翻译,而非通过日译等中介译本转译。如前所述,《作风》的编辑有一些总的编选倾向,译者们选出的作品,也大多符合编选原则。当然,也有一些作品,比如爵青翻译纪德的《放埒之书》,就明显是出于自己对纪德的喜好,对编辑的进步倾向似无过多考虑。换句话说,采用编者统筹、译者自选的方式,在伪满洲国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有组织的自主翻译,在当时的确前所未有,这种编辑方式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整本杂志的主题保持统一,凸显进步色彩,又尽可能给予译者选择和翻译的自由,提高他们的参与热情。当然,译者自选的方式,也就必然会产生一些不能很好呼应统一主题的作品。
二、《作风》中的朝鲜文学作品翻译
《作风》中收录的朝鲜文学作品共有三篇,按顺序分别是王觉翻译的李光洙的《嘉实》,以及古辛翻译的李孝石的《猪》和金东仁的《赭色的山》。译者王觉为在伪满洲国参与国民党反满抗日活动的国民党地下党员,作品可能是通过收录在《嘉实:李光洙短篇集》中的日译转译成中文的。[9](P.146)译者古辛背景不详,其翻译的两篇作品均在1940年于日本出版的《朝鲜小说代表作集》[10]中出现,可以推测也是从该书中通过日文转译。这三篇朝鲜文学作品的选择,都和杂志的反战、放逐、贫困的编选主题相符。《嘉实》的故事发生在古代,讲一个新罗的农村青年在和邻家女子订婚之后,代女子的父亲服兵役。可是在战场上和高句丽士兵的对话,却让他发现两边的士兵都因受统治者所蒙骗而被卷入毫无意义的战争。后来,他被迫留在高句丽的一个村落中生活,但始终想要回到新罗的家。在故事的结尾,他终于踏上了归乡之途。《猪》则反映底层农民的贫困,讲述一位农民因为疏忽导致猪被火车撞死后的心痛。《赭色的山》将背景放在满洲,以一位在满洲旅行的朝鲜医生的视角,讲述在满朝鲜农民受到中国地主的迫害后,一个不事生产的朝鲜混混挺身而出去讨公道,结果被中国地主打死的故事。在死前,这位朝鲜混混望向祖国的方向,要求医生为他唱怀念祖国山水的爱国歌,歌声最后变成了全体村民的合唱。
当然,和所有文学作品一样,这三篇朝鲜小说,其文本本身也都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但本文想要强调的是,由于《作风》整本杂志有统一的编选原则,所以选集性质的杂志便具有了规约文本意义、引导读者以既定方式解读文本的作用。因此,上面谈到的故事梗概和解读,也只是在《作风》这一选集的空间内获得的阐释。下面,我将以具体作品、特别是《赭色的山》为例,对此观点作进一步说明。首先,虽然前文已经说过,《作风》和弱小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编者的后见之明,但这里仍可以探讨一下将朝鲜文学作为弱小民族文学翻译的可能性。在前文中介绍的上海出版的一系列弱小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集中,截至1934年为止,还没有朝鲜文学作品出现,但1936年胡风的《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中,正式将朝鲜文学作为与台湾相同的被殖民地文学介绍给上海的读者。此后出版的《弱小民族小说选》中收录了胡风书中张赫宙的小说《山灵》,《弱国小说名著》则收录了张赫宙的另一篇小说《姓权的那个家伙》。也就是说,到30年代中期为止,当时的殖民地朝鲜已经普遍被中国内地认为是弱小民族,其作品也得到上海文学翻译界的关注。而将朝鲜小说作为被殖民地文学翻译到伪满洲国,则有更微妙的意义。当时,对上海的进步知识分子来说,殖民地朝鲜成为面临存亡危机的中国的警示,而朝鲜人民则是同在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阵线上的同志,这成为他们翻译朝鲜文学作品的出发点。但对于已经沦为殖民地的伪满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翻译讲述朝鲜移民贫困生活和思乡情怀的小说,直接成为高压统治下自身现实命运的曲折代言。不仅如此,在满朝鲜移民和其它那些因为国内解放革命而流亡的白俄等人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而被迫流亡,可以说是最符合“弱小民族”概念的表现对象。我以为,这些是《作风》翻译朝鲜作品的出发点,也客观上规约了在《作风》中对这些作品的解读方式。以《赭色的山》的翻译为例。这样一篇强调伪满中朝民族矛盾的作品却会被《作风》的译者选中翻译,引人深思。小说的满洲背景,曾引起伪满中国读者的关注。[5]此外,作品中的压迫者是中国地主,而非全体中国人,中国读者由此可以从阶级压迫而非民族矛盾的角度来解读。这些都可能曾是译者的考虑因素。不过我以为,译者选择此文翻译,最主要的动因当属故事的贫困和放逐主题,特别是后者。若说满洲背景,在此文的翻译底本,即日译《朝鲜小说代表作集》中,有三篇都和满洲有关。此文之外,还有金东里的《野蔷薇》和李泰俊的《农军》。
①前者写一位朝鲜农民的妻子,在新婚丈夫赴满之后,在妈妈的帮助下辛苦地攒出旅费,即将赴满和丈夫团聚的故事;后者则取材伪满洲国里中国农民和朝鲜农民之间的纷争。在这三篇小说中,译者唯独选择了《赭色的山》,或因为作品不仅描写了朝鲜移民在伪满洲国受压迫的悲惨生活,更在文末大写他们思念祖国的望乡之情,这和《作风》中多篇作品的放逐主题相呼应:如《嘉实》中流落高句丽的新罗青年的思乡之情、英国小说《败北》中因战争而流落德国沦为妓女的俄罗斯姑娘的孤独、法国小说《大尉索古普的茶》中白俄流民和墨西哥移民在巴黎的偶遇和互相温暖、俄国小说《放逐》中一群流落西伯利亚的被放逐者们对故乡生活的回忆等等。①反观日译《朝鲜小说代表作集》中另两篇满洲题材的作品,则并未突出民族主义意识。在朝鲜,金东仁小说发表当初,并未有什么反响,但战后很长时间,该小说都被当作韩国民族主义文学的典范广为传播,还一度被收入小学课本。另一方面,已有韩国学者指出,金东仁的《赭色的山》的创作,客观上声援了日本帝国主义。小说最初发表于1932年,正是1931年7月的万宝山事件刚刚结束之时。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挑起的中朝农民冲突,冲突发生后,由日本操控的朝鲜媒体大肆夸张,编造鲜农死亡的新闻,在当时的朝鲜国内引发排华惨案。金东仁从未去过满洲,受新闻报道的影响,民族主义情绪勃发,写下了这篇和他的其它作品完全不同的爱国小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通过夸大在满中朝农民的矛盾冲突,把自己打造成在满朝鲜农民的保护人,从而获得在该地区扩张势力的口实。而金东仁的《赭色的山》,正应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11](P.21)这或许也正是日译《朝鲜小说代表作集》中会翻译《赭色的山》以及其它满洲相关小说的原因之一。不过,正如上文所说,《赭色的山》能被翻译成中文,却是因为其中民族主义情绪有可能和伪满中国读者反满抗日的爱国情绪产生共鸣。也就是说,如果说《赭色的山》的原作中隐含着日本殖民者和中国地主两种伪满洲国朝鲜农民的压迫者的话,那么在作品被翻译成日文和中文的过程中,因为收录的选集性质不同,被强调的压迫者也就不同,这导致了作品的社会效果和作用不同。就《作风》而言,通过文学翻译和选集编选,《赭色的山》中与日本帝国主义共谋的负面作用被削弱,爱国思乡的反帝国主义倾向得到了强调。
基于MTI文体意识的文学翻译论文
一、MTI文学翻译教学现状及问题
MTI近年来发展迅猛,但在很多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研究发现,中国内地对MTI文学翻译教学的研究尚未完全展开,在《清华同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更新至2013年底)输入关键词“MTI”,共有66篇相关论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大部分或是聚焦于MTI课程设置和培养计划等宏观层面的研究论述,或是论证开设如科技翻译、法律翻译和汽车行业翻译等非文学翻译课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于MTI教学,尤其是文学翻译教学探析甚少。此外,国内高等院校在设置MTI课程时,“只有65%的院校设立了文学翻译课”。这意味着多达35%的院校取消了文学翻译课程的设置,认为这门课程对于培养高素质的翻译人才没有任何意义或价值,而开设这门课程的很多院校仍采用本科阶段的教学模式,这几乎无益于培养高素质的翻译人才。诚然,MTI的课程设置要体现其专业性和实用性,但培养一位真正合格的高层次翻译专业人才,最基本的文学素养却是必不可少的。对专业的高层次翻译人才来说,文学素养的培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有针对性的文学翻译练习,而翻译中是否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则直接关系到译文质量的高低。因此可知,文学翻译课程在MTI课程设置中的地位未得到充分重视,其教学效果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MTI文学翻译教学特点
经过本科阶段的翻译积累,MTI研究生已具备相对扎实的翻译基础。因此,对任课教师而言,教学不应再专注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转换水平,而应致力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翻译理论素养与文学素养。任课教师应清楚地认识到,MTI文学翻译教学不同于本科阶段的文学翻译教学。一般说来,后者往往注重翻译技能的培养,关注语法分析和翻译对比,强调具体词性和句式的转化,比如汉英翻译中如何将动词转化成名词,如何将主动句转化成被动句等,重视语言层面上词或句的对等,以翻译的准确性为第一标准。然而,仅仅从词汇、句法等语言层面讲授文学翻译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学生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关注字词之间生硬的意义转化,却忽略文本的整体构造和美学价值。因此,MTI文学翻译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培养翻译技巧的基础阶段,应寻找新的教学突破口,把文体学理论和翻译实践结合起来,以文体学理论为切入点,配以适量不同文体的翻译实践,注重培养学生翻译中的文体意识,引导学生在动笔前对原文的语言特征和文体风格进行仔细的辨析,并在译文中如实地加以再现,以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
三、MTI文学翻译教学与文体意识建构
针对目前MTI文学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教学特点,教师应该如何提高MTI文学翻译教学质量,结合MTI教学实践,笔者认为MTI文学翻译教学应结合文体学理论,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入手,加强建构学生翻译中的文体意识。具体讲,在理论部分阶段,针对课程特点,应在传统翻译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引入文体学理论;在实践部分阶段,通过练习的选材、批改、评析及课程反思等环节,在翻译实践中积极建构学生的文体意识。在实际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文体翻译理论的讲授有利于宏观地建构学生的文体翻译观;适量不同文体的翻译实践则可以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根据词汇、语法、修辞、篇章等具体的文本语言特征对原文进行文体分析,并在译文中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文体效果,从而大大提高译文的质量。
(一)文体翻译理论教学与文体意识建构
MTI以翻译实践为中心,但是翻译理论的讲授却必不可少,因为“翻译的理论素养不仅对翻译实践能力有宏观指导作用,而且是翻译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MTI文学翻译教学来说,仅仅讲授基础的翻译理论还不够,还必须将文体学相关理论引入教学,配以相应的翻译练习,以加强学生的文体意识,提高学生的文字敏感度和鉴赏力,综合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翻译素养。就文学翻译而言,一般最难把握的是文体,尤其是风格的传达与再现。因此,在MTI文学翻译教学中,建构学生文体意识的第一步是让学生对文体与翻译的密切关系有着宏观、清醒的认识,从而促使他们在翻译实践中有意识地传达原文的文体风格。任课教师可在学期初向学生介绍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翻译专家关于文体与翻译的关系的论述,之后简要介绍与翻译相关的文体学理论,并将其用于指导翻译实践,借此不断强化学生的文体意识。比如,被誉为“西方翻译理论之父”的M.T.Cicero对文体与翻译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生动的论述:“我在翻译时将自己当做是演说家,而不是解释员:保留原文的思想与形式,或者说是保留思想的‘修辞’,但却使用符合我们表达习惯的语言。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没有必要逐字翻译,而是要保留原文的整体风格与力量。”换言之,翻译不仅仅是意义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要保留原文的文体风格。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E.A.Nida、A.F.Tytler等知名学者:Tytler提出的翻译3原则强调“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文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自如”;Nida认为“翻译是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者JeanBoase-Beier在《翻译文体学研究》一书中论述了文体对翻译的影响,通过实例阐释了翻译研究的文体学途径。鲁迅、王佐良、刘宓庆、申丹等中国内地学者也强调翻译中文体风格的传达。刘宓庆教授指出:“翻译是接受语复制原语言信息的最通似的自然等值物,首先是在意义方面,其次是在文体方面的自然等值物。”26-35申丹教授也曾详细地论述了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的关系,强调将文体学应用于文学翻译这一领域的必要性。综上所述,翻译中传神地再现原文的文体风格是保证译文质量的关键,对于文学翻译尤其如此。特定的文体形式会产生不同的文体价值和美学效果。为了让学生在动笔翻译前学会系统地分析原文的文体特征,提高学生在文学翻译中的文体敏感度,MTI文学翻译教学应重点引介文体学理论,并将理论用于指导翻译实践。那么应该如何分析文本的文体特征?英国文体学家GeoffreyLeech和MichaelShort在其著名的《小说文体论:英语小说的语言学入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文体分析模式,即从词汇、语法、修辞、篇章等4个层面对文本进行较为全面、客观的文体分析。这个模式可以让学生系统地观察原文的文体特征,从而能够有意识地在译文中再现这些特征。在不同文体的翻译实践过程中,学生可逐渐体会到:“文体是一种选择的过程,各种选择都将对翻译产生影响。”因此,在动笔翻译前应细致地辨别原文的文体特征,“根据语言结构和文体价值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处理好“译文与原文之间特殊的文体关系”,努力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风姿原貌,提高译文的质量,以更多的翻译文化精品让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巅。
儿童文学作品文学翻译论文
一、被动显形:文学系统外的操控因素———意识形态
任溶溶早期翻译的大都是苏联儿童文学作品。根据马力的统计,在1948—1962年间,任溶溶翻译了40部作品,其中35部都是译自前苏联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显然也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苏联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苏联文学及其儿童文学也是如此。“50年代,由于中国奉行‘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一边倒政策,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儿童文学蜂涌而入,大量翻译俄苏作品几乎成了一种浩大的运动。”1952年,新中国第一家少儿读物专业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任溶溶任译文科科长,该社成了当时儿童文学译介的中心。此时的任溶溶,集译者与“赞助人”于一身,又构成了其译介儿童文学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此期间,任溶溶翻译了大量苏联的儿童诗,他选取的原文作者都是声名显赫的诗人,如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阿•托尔斯泰、盖达尔等。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占主导地位,当时的社会迫切需要用“勇敢”“无私”“奉献”等精神来提高中国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修养,因此翻译的作品主要也是以革命励志类为主。例如,1953年时代出版社出版了任溶溶翻译的《古丽雅的道路》,立刻成了一本畅销书,7个月后印数就接近50万册。苏联的道路,青春和理想,为祖国奉献的精神,这一切让小英雄古丽雅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致使译者的意识形态不自觉地与主流意识相靠拢,当这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时,译者的翻译活动就如鱼得水,既顺应了时代潮流,又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而此时译者的身份地位也得以凸显,译者的声音亦更响亮。当时的“古丽雅热”让更多的读者认识了任溶溶,他翻译的其他作品也因此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然而,当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骤变的时候,处于该系统中的文学系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一点在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的选材方面有着很明显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外国文学译介领域向苏联一边倒的状况出现了极大的逆转,苏联儿童文学作品随后被禁止出版。而此时,任溶溶翻译的《马尔夏克儿童诗选》虽已全部校订好,但也只能压下来。”
从马力列出的任溶溶译事年表也可以看出,在随后的17年间,任溶溶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呈现零产出的情况。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汉斯•弗米尔(HansVermeer)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他强调当译者在被赋予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译者的“无作为”或者“零作为”也要被看作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任溶溶在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沉寂,也正是因为受到社会政治因素和赞助人,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而不得不顺应的一种行为。当时陷于“”期间的中国急需了解世界,每个出版社在干校都有自己的连队,有关部门特地抽调翻译人员组成“翻译连”,开始翻译世界各国的历史书籍,其间任溶溶就担起了翻译《北非史》的任务。任溶溶的翻译从儿童文学的偏离,也正是与当时社会不重视儿童,儿童文学的边缘化地位紧密相关的。1978年10月,陈伯吹、严文井、叶君健、柯岩、金波、任溶溶等一批儿童文学工作者来到庐山,出席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儿童文学界从长达十年的政治噩梦中开始复苏。儿童文学的重点转向儿童读者本身,儿童本位的儿童观逐渐确立。而任溶溶正是这一潮流的领军人物。这一时期任溶溶翻译了大量北欧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为中国几代小读者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进入新世纪以后,年过花甲的任溶溶仍然能够紧跟时代大潮,翻译了大量英美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如美国作家怀特的《吹小号的天鹅》、《夏洛的网》以及英国作家伍德尔的《飞翔的鸟拒绝忧伤》等。这些作品无不体现着新时代的气息,书中“成长型”明星角色如蜘蛛夏洛、哑天鹅等教会新时代的儿童如何面对竞争、挫折、失败、压力,让他们学会与人交往、团结合作、勇敢坚强,向小读者注入的都是这个时代儿童所急需的“正能量”。因此,可以看出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其典型的时代特征,这是译者和翻译文本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明显体现,也是译者的角色在翻译活动中的“被动显形”。
二、被动显形:文学系统内的操控因素———主流诗学
上文提到,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内因是由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他们关注的是诗学。安德烈•勒菲弗尔还指出,内因(文学家及其诗学观念)是在外因(赞助人及其意识形态)所制定的参数范围内起作用的。也就是说,代表某一文化或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一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价值参数;文学家和翻译家则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这里所说的诗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学手法、体裁、主题、象征、典型性人物及情景;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在任溶溶长达六七十年的翻译活动中,诗学这只无形的手也无时无刻不在操控着译者的选择。比如任溶溶早期翻译的前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便是顺应当时主流诗学的做法。那些作品中的“小英雄”们,如古丽雅、铁木儿等与当时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张嘎、潘冬子、小英雄雨来等形象是非常相似的。但是作为声名显赫的儿童文学译者,任溶溶同时又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有时候他也会向主流诗学提出挑战,因此主流诗学和译者的个人风格相互作用,这一点在任溶溶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也有着显著的体现。80年代初,任溶溶将瑞典著名儿童文学女作家的《小飞人》三部曲和《长袜子皮皮》三部曲译介到中国来。书中的小飞人卡尔松和皮皮这两个调皮捣蛋而又叛逆的“问题儿童”的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学中英雄榜样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对中国儿童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连原文的作者都不得不“显形”来协助译者,以帮助译文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林格伦为“皮皮”的中译本写了序言,提到“皮皮没受过多少教育,所以你们不要学她的样。”勒菲弗尔也曾指出:“有些作家会因他们早期的某些少数作品而对主流诗学产生一些显著的,甚至有可能令人不安的影响,但随后他们却发现自己逐渐成为了主流,因为他们为主流诗学引入了新元素,或因为他们将文学赋予了一个新颖的功能,或两者兼而有之。”
任溶溶便是这样一位“译家”。刘绪源先生针对任溶溶新时期的译介评论说:“中国读者开始用惊异的眼光打量这些全新的作品。当时人们的思想刚开始解放,出版社很是为难,一方面知道它们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方面又怕它们被定为‘坏书’而挨批。……好在那时的时代气氛总体是积极开放的,在孩子们的一片叫好声中,中国的儿童文学界和理论界也开始正视林格伦的这些奇书了。”如果说之前的儿童文学以教化功能为主,那么可以说任溶溶翻译作品中的游戏精神和热闹风格赋予了儿童文学一个新功能,即娱乐功能。任溶溶本人也说,他翻译儿童文学“无非想让小朋友读到有意思又好玩的书,同时向我国儿童文学作者介绍世界儿童文学的精品,让大家开开眼界。”的确,任溶溶对林格伦的译介,令中国儿童文学界大开眼界。由此而掀起的“热闹派”童话创作,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百花齐放的局面。主流诗学通过专业人士主要是评论家们操控着文学创作和翻译,但是作家和译者也可以向主流诗学提出挑战,本来处于边缘地位的诗学观也有可能因为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逐渐成为“主流”。这跟作家或译者本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主体性是分不开的。
三、主动显形:译者的儿童观与个人情操
任溶溶的儿童文学译作以其题材的轻松幽默和语言的通俗易懂著称。这与译者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和他的个人经历、审美情趣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翻译选材的倾向与译者的个人特征和生活经历息息相关。译者通常会选择那些与自身的秉性气质、审美情趣、文化取向等相契合的作品进行译介。例如在任溶溶早期的译介活动中,他在大的方向上顺应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翻译的是苏联以教化功能为主的儿童文学作品,但译者本人幽默爱玩的性格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却左右了他对翻译作品的具体选择。比如任溶溶翻译了大量马尔夏克的儿童诗,是因为马尔夏克“善于在自己的诗里讲述有关重大社会内容的那些最复杂的概念……他的讲述往往采用游戏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那么生动活泼,那么迷人心窍并且是那么易于被娃娃所理解”。上文所说的任溶溶对林格伦的译介也恰恰是因为这位作家的作品符合译者的审美情趣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不仅翻译如此,任溶溶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翻译活动的影响,任溶溶创作的儿童诗通常是站在儿童的立场来观察生活,新奇幽默,充满童趣。其次,在翻译策略上,任溶溶也做到了时时刻刻心中有读者。他曾说:“翻译无非是借译者的口,说出原作者用外语对外国读者说的话,连口气也要尽可能像。我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原作者的书既然是写给不同年龄的孩子看的,自然要让他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我们译者也就应该做到这一点,让我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9]大多数情况下,任溶溶采取的是以“忠实”为主的翻译方法,但他并不是盲目地忠于原作,他始终本着儿童本位的思想,采取以儿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方法。如当涉及一些语言和文化差异时,任溶溶便能将其深厚的英汉双语功底发挥到极致,使译作与原作在功能上达到“对等”。例如,一些英美儿童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文字游戏,读者读起来非常有趣,但是因为英汉语言的差异,这些文字游戏如果直译的话就会变得趣味全无,甚至晦涩难懂。又不能像成人文学那样采用加注解的方法,任溶溶觉得:“不得已时,偶尔加个注解还可以,多了可就不行,孩子受不了,干脆不看了。”
基于目的论的文学翻译论文
一、翻译目的论概述
翻译目的论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要关注的是译作的目的,这个目的决定了译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最终才能产生功能上能满足需要的译文。因此,译者必须知道为什么要翻译原文以及目的语的文本功能是什么。正如赖斯和维米尔那本书的书名所提示的那样,他们提出翻译目的论是为了找出一套能够适用于所有文本的通用型翻译理论模式。然而,目的论实际上无法担任此种重任,它是一种宏观性的外部翻译理论,并没有对具体的翻译过程以及原文的内容及美感给予一定的关注,而是关注翻译之前的目的语中行动参与者以及外部因素等方面的分析。但是,某些人对于目的论的希望却让其在很多方面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遭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和批判。根据诺德的归纳,当前学术界针对目的论的批判声音主要来源于十个方面,即行为不一定都有目的性,翻译也不一定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功能理论超越了翻译界限,目的论本身并不是创新理论,功能理论的基础并不依靠经验总结,并导致了唯利是图的翻译人员出现,它与原文并不能保持高度一致,其实质只是一种编译理论范畴,并不能适用于文学翻译领域,还具有文化相对性等。然而,张南峰却认为诺德的归纳与总结方面也有自身的问题存在,即他认为诺德对于目的论的适用范围有所夸大,妄图用其指导所有的翻译实践活动而忽视了具体翻译实践中的不同翻译特点,造成了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二、文学作品翻译中的目的论
(一)文学作品的非目的性
翻译目的论宣称是通用理论,但实际上仅对一些非文学文本与其他少数文学文本奏效,这是因为真正的文学文本有着较为复杂的创作风格,或者其根本就没有较为明确的创作目的。具体来说,首先我们应该很好地区分什么是文学作品什么是非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具有虚构性、目的的不显著性和读者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就不能按照翻译目的论的要求以通用的翻译理论去限定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而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译者更应该考虑的是向本国的读者介绍优秀外国文学作品。但从目的论的角度看,纯文学作品的翻译几乎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涉及到目的论的功利性问题。正如陈大亮指出的那样,目的论已经让翻译行为具有了获取金钱与财富的商业性目标,久而久之就使得翻译行为成为了一种庸俗的功利性商业行为。因此,目的论最终让翻译者的内省成为了泡影。而翻译的真实目的应该是以目的受众作为根本性接收者的语言文化转化行为,一般要在特定的语境中产生。对于文学翻译而言,文学作品并不是物质实体,也许也很少能为译者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与非文学翻译不同,文学翻译更注重译作是否能传达出原作要想读者表达的艺术美感以及人生的体验和富含哲理性的感悟等,它是要把文学作品中的精神内涵传达给目标语的受众,否则,文学翻译就是纯粹的文字翻译,它将失去人学的特征。一般来说,文学语言具有深刻的联想内涵,以诗一般的语言给读者以各种美的体验。品味文学作品的过程就如同品茗,不同的读者对个中滋味也会有百般的解读。著名翻译学者许渊冲也曾提出,“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一般译者可对社会作出贡献,但文学翻译却需要创造才能,因为文学翻译是艺术”。在目的论者看来,只要能满足翻译行为的需求人的要求就可以算是成功的翻译活动,它不需要译者要尊重作品的原文,只要能够达到语句通顺连贯就可以。因此,弗米尔也进一步认为,翻译行为的好坏,并不是基于其是否具有原文的语言特征与文体风格。这样就使得原文在翻译过程中其主体性很大程度上被弱化了,而仅仅是以翻译委托人的要求为先决条件。但事实上,文学翻译是再创造的过程,需要译者具有敏锐的感觉和深厚的文学鉴赏力及独到的表现力。这并不像目的论中所说的那样,只要能满足翻译委托人的需要就能算做好的。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许多文学翻译作品在市场上并不受鉴赏水平较高的读者的欢迎。如若译者抱着功利的想法去译文学作品,其译文质量可想而知。一味地冲着市场销量而去的译作,不仅极少能正确地表述原意更谈不上给译文读者以艺术美的享受。
(二)文学作品的非实用主义
文学是“非实用主义的”,它给原文或译文读者的审美体验并不能够如同那些科学性体验者,能够感受到直接且实际的目标。实际上,有时候它只是作者个人的一种情感的抒发,或者是描述事物的一般情况。翻译目的论在形成之初,只是为了解决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要让翻译能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并尽可能满足顾客的翻译需求,并根据顾客的需求来进行翻译策略的实际调整。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目的论却不其然地走向了功利性的方向,很多目的论者认为翻译就应该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而进行主观性的翻译操作。这就造成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对原文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增添或者是删减进而对原文的文本进行削弱。似乎只要译者能在原文中获取到足够的信息,原文的文本最后被译成译文后哪怕是被改动得面目全非也不为过。这样做在不强调文学性而强调实用性的非文学翻译中是具有一定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在非文学翻译中,其主要目的就是完成交流与沟通,这样的翻译便算是成功。但是在文学翻译中,这样做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牺牲。经过对原文本的占有和掠夺以及删改后,原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也被大大地削弱了。
(三)目的论在文学翻译中的主体性缺陷
扩展阅读
免责声明
本站为第三方开放式学习交流平台,所有内容均为用户上传,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若内容不实请联系在线客服删除,服务时间:8: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