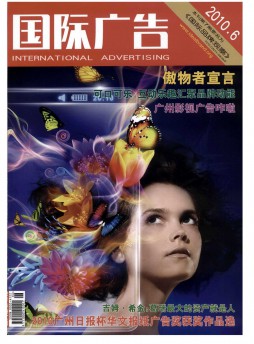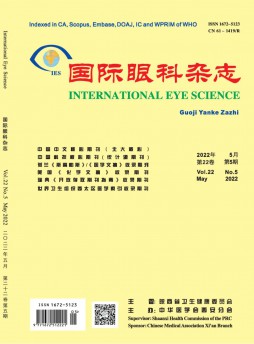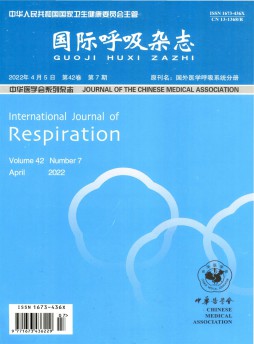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国家形象;综合实力;软实力
随着国际政治研究的日趋成熟和信息化时代的不断发展,国内学术界关于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逐渐发生了转变: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从以往对国家、政府间组织的研究扩展到非政府组织间的研究,以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不断增多;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学者从以往对传统政治、军事的关注逐渐扩展为对环境、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研究;学界对外交领域的研究也进一步扩展,由以往只关注政府间外交即官方外交,逐渐扩大到关注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等领域。
基于这些国际政治研究方面的变化,对“国家形象”一词的研究开始不断受到学界的关注。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被认为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①因此,国家形象的研究对我国“软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提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国外研究成果综述
一般而言,国外学术界对于国家形象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被看成是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国家以及军队形象是西方国家研究的一个角度,但分析较为简单,主要体现为政治军事著作中的零星思想和只言片语。工业革命后,国家形象的研究开始凸显,但其目的主要为国家政治和军事的合法,其研究重点是如何通过国家形象的塑造为战争做宣传,但尚未形成体系。信息技术革命悄然兴起后,国家形象作为开始被学者广泛关注,并且随着国际竞争加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国际政治学角度研究国家形象。②在国际政治方面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基本上秉承了4种研究路径③:
其一,现实主义“软实力”研究路径。西方大量政治哲学家认为,威望、声誉(reputation)即指“国家形象”,声望因素往往是产生冲突的动机之一。二战后,声望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安全领域,麦尔瑟在《声望与国际政治》一书中试图解决威慑论的核心问题――即在危机关头,坚定的声誉是否真正奏效。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声誉的关注逐渐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展。学者们试图运用声誉这一工具,分析国际合作、国际组织、地区一体化等问题。
其二,建构主义研究路径。肯尼斯・布尔丁(K.E.Boulding)在此方面首开先河。他认为,人们是在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价值观念下塑造国家形象,即使同一个国家,在持不同价值观念的媒体的“刻刀”下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国家形象,他强调了价值体系在国家形象形成中的重要性,拓宽了国家形象问题的研究视角。
其三,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路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对国家形象形成的根源和不同国家形象对决策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认为,在两国关系中,目标的一致性、相对实力(能力)和相对的文化地位是形象形成的三个结构性因素。根据三者的不同组合,两国关系中存在着敌人形象、盟友形象、依赖形象、屠夫形象和帝国形象等五种相互认知。不同的形象认知影响一国对另一国的政策取向。
其四,公共关系的研究路径。在国际公共关系框架内研究国家形象,其中涉及国际公关活动、国际媒体探讨等方面。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迈克尔・昆兹克(MichaelKuncz-ik)1997年编著出版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公共关系》是该领域的第一本权威著作。
二、国内研究成果综述
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基本处于无意识的自发阶段,除了个别研究和著作中提到国家形象的观点外,基本查找不到相关理论研究。90年代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西方大量“中国”、“中国崩溃论”等理论的引进以及为了回应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中国学术界开始对“国家形象”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探索。
在中国知网中,关于国家形象研究论文共920篇,实际有用论文809篇。通过统计,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包括6个领域:即,从文化的角度、哲学视角、传播学的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政治视角、经济角度以及从符号学、解释学等其他角度研究国家形象。
从数量对比上不难看出,国内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播学视角、政治视角和文化视角,其他方面的研究视角略有涉及,但并非学者研究主流。
由于本论文主要涉及传媒和国际政治领域研究,故对这两个领域中以往学者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进行综述,主要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公共外交和媒体传播策略三个角度。
(一)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在对国家形象的界定上,学术界基本具有一致意见,认为国家形象是一国综合实力的表现。具体而言,管文虎等一批学者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④孙有中认为,“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包括政府信誉、外交能力与军事准备等)、经济(包括金融实力、财政实力、产品特色与质量、国民收入等)、社会(包括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士气、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实力、教育水平、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与地理(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⑤
从国家形象定位及构建角度,管文虎(1999)是国内最早比较详细论述国家形象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中国的国家形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⑥刘明对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的核心要素做出了一般性概括,探讨了如何准确定位、构建精致化的国家形象。陈生洛(2007)指出中国大学生心中韩国正面的国家形象,反映了其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留恋,以及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在自己的国土上不断流失的无奈和伤感。
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王红英运用“博弈理论”,提出了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和外交政策的相关机制――外部的社会回报和社会惩罚。邓超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提出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际传播、外交政策以及国家内部情况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⑦从现实主义“软实力”的角度,张锰(2008)提出国家形象可以从本源、表象、途径三个方面来理解,本源性是国家形象的基础,表象性是国家形象的推动力,传媒是国家形象的表现途径。⑧陈正良(2008)在分析国家形象内涵及国家形象塑造的意义、中国国家形象的现状的基础上对塑造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增强中国魅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考。
(二)公共外交角度。从这一角度对国家形象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少,多从公共外交政策制定的角度,为政府决策提供意见参考,政治化倾向较为明显。王义桅、唐小松等致力于美国公共外交对国家形象影响的研究,从提升国家形象的策略角度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提出了对策和方式。赵玉霞(2007),冷战后中国对外宣传积极向公共外交转变,并初步建立起公共外交体系,中国公共外交已在多领域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只有不断完善公共外交对国家形象的塑造,才能树立真实全面的中国形象,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服务中国崛起。⑨
(三)媒体传播策略角度。国内学者从传媒角度对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形象传播现状、传媒理论和报纸研究三个方面。徐小鸽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⑩刘继南、何辉等把国家形象界定为:“在物质本源基础之上,人们经由各种媒介,对一国家产生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总体感知。”从传媒理论角度,程曼丽(2008)从议程设置角度提出中国的国家形象(即外部公众对中国的印象)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所设置的,其中充满了“固定的成见”,中国要想突破西方国家既有的认知、评价藩篱,就必须参与到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中去。⑾从以具体媒体对国家形象塑造角度,张玉(2007)以《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为例,运用内容分析和定量研究的方法,指出日本媒体关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形象。
综上所述,通过对国家形象相关论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学者对国家形象的关注涉及多个角度,程度正在不断加深,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形象的研究上仍然存在问题:国内外研究涉及的角度并不全面,例如对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体中的国家形象塑造研究非常有限,且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为定性研究,这就造成研究方法单一,多是零散的、缺乏理论的简单归纳,无法向读者呈现一个完整、系统的国家形象图谱。
[注释]
①BouldingK.E:NationalImagesandInternationalSystems[J],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1959(3):P119-131.
②袁赛男:《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11月第12卷第6期.
③杜雁芸:《国家形象的内涵及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年第71期.
④管文虎:《国家形象论》,四川: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⑤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国际论坛》2002年第16期.
⑥管文虎:《国家形象论》,四川: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⑦邓超:《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的国家形象塑造》,《中国传媒大学》2006年第1期.
⑧张锰:《软实力理论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大视野》2008年第7期.
⑨赵玉霞:《论中国公共外交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暨南大学》2007年第1期.
⑩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2版.
⑩程曼丽:《论“议程设置”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舆论导向作用》,《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P45.
[参考文献]
[1]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刘继南、何辉:《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版.
第2篇
关键词:“安全困境” 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 新自由主义 化解
作为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焦点之一,“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关系、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对于国际关系如何超越“安全困境”,理论家们长期争论不休,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理论
“安全困境”思想最初萌芽于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已有所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1。尔后,许多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家在描述国际政治现状和解释国际政治关系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安全困境”的思想。近代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阐述了国家学说,他认为政治家的职责在于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以此论证了统治者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合法性,从而把政治和道德分离开来。霍布斯继承了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的传统,认为强大的权威是终止人类无休的斗争的有力武器。马克斯·韦伯也深入研究了政治和国家理论,他把对权力的追求当做政治理论的核心。可以说,现实主义先驱们的国际安全理论为后来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并且使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首先对“安全困境”概念进行详细阐述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Herbert Butterfield)和美国政治家约翰·赫兹(John Herz)。
巴特菲尔在他的《历史与人类关系》中描述了“安全困境”,把“安全困境”叫做“霍布斯主义的恐惧”(Hobbesian fear)。他认为战争往往发生在那些刻意避免冲突的国家之间,正是刻意的避免行为导致了战争的发生。即使是在均无有意伤害对方的双方之间,战争的悲剧依然会上演。“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蓄意出来危害世界的大恶人的干涉,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也可能爆发。它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任何冲突的大国之间爆发。”2
赫兹则在学术界第一次使用“安全困境”术语。在1950年发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中,赫兹首次提出“安全困境”概念,随后又在1959年出版的《原子时代的国际政治》一书中更为系统的阐述了“安全困境”对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影响。赫茨认为,“‘安全困境’或‘权力与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情势(状态)中,权力的单元发现他们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并肩存在,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把行为的标准强加给它们,从而使它们互不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驱使这些单元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安全。但这种努力证明有违自己得到安全的初衷,因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3。每个独立主权国家都是独立的权力单元,每个单元相当于独立平等的单子。但是,这些单子之间没有像莱布尼兹般的来自上帝的前定和谐,它们是浑然无序的,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中。谁也不相信谁,谁也不听谁,没有强大的权威作为它们行为的统一标准,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却只有猜疑和恐惧。为了求得生存,只得时时防备,并提升自己的实力。殊不知,越是防备,获得的安全感却越少。
“安全困境”概念被巴特菲尔和赫兹提出以后,它越来越受研究者的关注。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诸如罗伯特-杰维斯、杰克-史奈德、阿兰-柯林斯等都发表了相关论文阐述了“安全困境”观念。
现实主义以人性恶的前提假设出发,对伦理道德持怀疑主义的态度,坚持政治与道德的划分,否定伦理在国际关系上的作用。它“对人性和政治权力采用现实的态度,以一种现实和历史的方式去看待涉及国家利益的国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尽量克服理想主义和道德伦理主义的干扰”4。现实主义把道德从政治理论中剔除的做法必然导致对建立国际间合作和信任机制可能性的否定。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中,由于国家之间缺乏一个超越各主权国家之上的最高权威,所以处于无法治的混乱状态。并且,它们互信不足,相互猜疑,把对方的一举一动都视为对于自身的威胁。为了避免对方的威胁,寻求安全,求得生存,双方只能按照“理性自私”原则依靠自身力量形成自助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弱肉强食”是重要的竞争法则,来自他国的威胁无处不在,自卫与威胁形成强烈的紧张关系。因此,各国不得不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权力政治,一方面加强国内实力,另一方面扩军备战,与其他国家形成对峙。但是,一国所采取的这一行动,又引起了他国的关注,被看成是对他国的威胁,他国也被迫采取应对措施,以达到力量的抗衡。可以说军备竞赛不断,力量对抗不断升级,战争一触即发,而战争的发生将会给双方造成两败俱伤,最终不利于各国的生存与安全,反而对于国家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的一种恶性循环状态,这样就使得各国陷入“安全困境”之中。约瑟夫·奈总结道,“安全困境的产生,同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即无政府状态,或国家之上缺少一个政府,是密不可分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可能导致所有的国家更不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其势力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个国家的侵害,那么第二个国家在看见第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后,可能也会增强自己的实力,以防备第一个国家。这样一来,每一方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得双方更不安全。”5
第3篇
关于体系层次与单位层次建构主义问题,温特坚持体系层次建构主义。但我以为,建构主义在层次上的“回落”(或曰还原到单位层次)是有道理的,因为国家身份的确定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是体系层次观念结构决定的。用一位中国学者的话说,就是“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章百家2002)。在建构主义与其他理论的融合方面,温特认为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因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包含了社会性内容。但我觉得如果融合可行,建构主义就只能保留其作为社会分析框架的地位,它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假定就失去不可通约的性质,因此它的国际政治理论地位就不复存在。另外,我提出了一个地缘-文化建构主义的概念,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层次上的不同路径问题,目的是可以发展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建构主义流派(如中国建构主义学派等),可能有一定的开发价值。
现征得温特本人同意,将部分通信内容翻译整理出来,并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以对话形式予以发表。(秦亚青)
一、体系层次和单位层次的建构主义
秦亚青:社会建构主义近些年来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很有学术意义的趋向,也显示了建构主义仍有着很大的学理发展空间。许多学者在分析层次和思想内涵两个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1987 年,你在发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的论文时(Wendt 1987),强调的是一种社会性互动,亦即施动者和结构之间的互构。这主要是一种双向的活动。比如奴隶和奴隶主的身份互构,因为不是因果关系,所以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奴隶、奴隶主和奴隶制三位一体,相互建构,相互依存。但是在你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Wendt 1999),我觉得虽然你说你的体系理论同样是重视互构的,但相互建构却基本上变成为一种单向建构,即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国家之间的互动则成为次要的内容,温特建构主义以体系理论为主,因而也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
温特:我同意你的说法。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自上而下的向度是我的理论的主导向度,单位层次的因素因此受到了压抑。我在1987 年的论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中强调的更是一种互构互动的关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提出的是体系理论,不是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所以,我有理由强调体系层面的理论建构,强调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正如我在书中说的那样:“在这本书里,我的兴趣在于国家间(或曰‘国际’)体系的结构及其产生的影响。所以,我将采用‘体系理论’来研究国际关系。”(Wendt 1999: p.11)
秦亚青:但是,一些批评者认为,如果没有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也就没有身份政治可言。比如,齐菲斯( Zehfuss)在她2002 年的著作《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中,批评你的理论是没有政治内容的身份/认同理论(Zehfuss 2002) 。她说,温特认为国家的自生身份,即由国内政治形成的身份,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是先于国际体系的,是外生的和给定的(Zehfuss 2002: p.44)。据此,她认为你的中间道路抽去了“政治”这一灵魂。国内政治提供了基本语境,没有这种语境,国家的身份/认同就失去了依托。
温特:的确,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许多批评都认为我的理论忽视了国家身份/认同的国内因素。但是,我认为这种批评有失偏颇。我承认,国内政治进程因素,对于国家身份形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本书中,我想要提出的不是解释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而是揭示国际体系的运动定律(the laws of motion of the system)。在这一方面,我与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相似的。华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理论与对外政策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像华尔兹的理论一样,我的理论也是体系理论。正因为如此,我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没有强调国家的身份形成和对外政策等内容。
秦亚青:许多学者采用体系层次的建构主义理论,获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比如芬尼莫尔(Finnemore)对于国际规范的社会性研究(Finnemore 1996) 。但是,其他一些学者在分析层次上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单位层次上面发展了建构主义理论。比较熟悉的是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江忆恩的理论主要是考虑国内的政治和历史进程如何建立起一个国家的集体战略文化,而且这种战略文化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影响到一个国家冲突还是合作的行为取向。另外,勒格罗的论文也在单位层次上面对建构主义理论进行了发展。
他提出了一个研究问题:是体系层面上的国际规范还是单位(次单位)层面上的组织文化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更大。他发现在许多情况下,“组织文化”这一解释变量比体系层次的“规范”变量更能够解释行为体的行为。我观察中国过去20 年里的发展历程,也发现单位层次的观念结构,在身份形成和再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秦亚青2003)。
温特:我的理论是体系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学者不能建立关于国家身份形成的建构主义理论。江忆恩、勒格罗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理论正是这样的理论。但是,由于我的理论主要是体系理论,强调的是体系因素的影响力量,所以,批评者认为我的理论忽视了国内层面的研究,实际上,这是一种理论建构中的必要忽视(necessary neglect)。
二、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
秦亚青:另外一个方面也很有意思,这就是关于建构主义与其他主流理论的融合问题。你有一次来信就曾经谈到“现实建构主义”或“建构现实主义”问题,是否可以继续讨论一下这个题目。在思想方面,建构主义有没有与其他理论融合的空间?
温特:巴尔金最近在《国际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的《现实建构主义》论文中," 试图将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相融合。这可能是拓展建构主义的一个突破点。
温特:我想先谈一下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我是否将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融合在一起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尤其是自由主义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信念对我影响很大。但是,我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高度的国家中心主义,因此,在这一方面不包含自由主义对个人高度关心这一标识性特征。同样,我的理论之中也没有关注非政府组织、全球市民社会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理论又表现出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在我的论文《为什么世界国家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中(温特2003) ,我至少也是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取向。在这篇论文中,我借鉴了“新黑格尔”的观念(黑格尔往往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鼻祖[proto-realist]),强调在世界国家形成过程中,群体性社会组织是核心单位,或者说强调了这一过程中的“集体单位(communitarian)”向度。虽然其中也包含了自由主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动力因素,但现实主义的成分是主要的。所以,我既是自由主义者,又不是自由主义者。到底是什么身份,还要取决于怎样解释“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在我的理论中包含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理论的成分。
我认为,在评价巴尔金关于将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融合在一起的论述的时候,考虑的关键问题应该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是否具有根本的社会理论内核(core)。我认为现实主义是具有这种内核的,这就是物质主义。这种物质主义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不仅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具有这样的内核,其他现实主义学者从根本上来说也近似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者,只不过他们将马克思强调的阶级换成了国家而已。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多德尼(Deudney)的论著(Deudney 1995)。正因为如此,我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表达了与巴尔金相似的观点,即不应将现实主义完全等同于华尔兹纯粹彻底的物质主义(当然,有的时候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华尔兹纯粹彻底的物质主义理论中,观念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相比之下,卡尔和摩根索等人的古典现实主义表现出更为精致、更为通融的本体论意识。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这就是比卡尔(Barkin)和摩根索走得更远,从根本上否认现实主义也必然是物质主义这一观点。即便是微弱的物质主义色彩,巴尔金也不予承认。我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如果他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是否还存在真正的“现实主义”呢?如果依照他的说法思考问题,现实主义就缺少了一种作为根基的本体性。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将现实主义视为一种建立在具有某种物质性社会理论基础之上的理论。这样一来,现实主义确实很难与建构主义融合在一起(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这要取决于怎样理解“建构主义”所包含的意义!)。
秦亚青:虽然你认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包含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理论的成分,因此巴尔金的观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我认为,巴尔金的观点失之偏颇的成分更大。因为,他将建构主义仅仅视为社会理论,而没有将它视为国际关系理论。我想,在你的论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你提到建构主义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而是一种分析方式或曰分析框架(approach)。这是第二层面2005 年第1 期(second order)的讨论,亦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讨论。你说:“第二层面的问题属于社会理论问题。社会理论涉及社会研究的根本假定:人作为施动者的本质以及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理念和物质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社会理论的适当形式等等。这些涉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不仅仅与国际政治有关,而且与任何人类团体有关,所以,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不仅仅专门用来解释国际政治。”(Wendt 1999:p.5)
你认为社会实践活动不仅会造就友善的康德文化,也会导致充满敌意的霍布斯文化。这也许是同样的道理,即建构主义可以融合自由主义的思想,也可以融合现实主义的理念。但是,在第一层面(first order),亦即在实在理论的层面上,你主要是吸取了自由主义的理念,这确实是将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比如,对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式发展、希望并相信康德文化的出现、暴力权力的逐步消失等观念,乃至集体身份和世界国家的形成,都明显或含蓄地表现了你的自由主义理念。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巴尔金认为,美国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有着深嵌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内涵。马丁·肖(Martin Shaw) 的批评更加尖锐,他认为温特建构主义是美国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为美国实现以自己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理念整合和建构(或重建)世界观念结构服务的(Shaw 2002)。
我们回到建构主义与其他理论的融合问题上来。在你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误的话,你是既要建立一个社会理论,又要建立一个国际政治理论。也就是说,在第二层面上建立社会理论;在第一层面上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你书中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政治领域的实在理论。你提出的三种文化、集体身份的建立等重要问题,是专门用于国际社会的。在这个意义上,你" 的理论已经不是一个社会分析的一般性模式。在第一层面上,社会建构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
如果说社会建构主义的目的是建立国际政治理论,那么,根据科学实在论的基本原则,它必须有着明确的基本假定,并且这些假定与其他的理论范式的基本假定不可通约。古典现实主义的几个基本假定(诸如国际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是冲突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诸如相对权力并非极端重要,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是和谐合作等)相比,是不可通约的。当年,人们批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所谓的“新新趋同”,指两大理论流派的基本假定相互通约。建构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流派,其基本假定是不能与其他理论的基本假定趋同的,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正因为如此,我以为,巴尔金的最大挑战不是他试图将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起来,以建立现实建构主义的理论流派,对抗你的自由建构主义。他的挑战在于,如果这种融合成功,那么,建构主义就只剩下一个躯壳,而失去了它的精神。巴尔金的“建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建构现实主义”。他在文中也确实使用了“建构现实主义”的说法,也就是说,建构主义是分析框架,现实主义是思想实质;建构主义是标,现实主义是本。如果这种研究议程成为建构主义的主导发展取向,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主义就会名存实亡。
三、地缘-文化建构主义
秦亚青:不过, 巴尔金的批评倒是给了我一点启发。既然他使用了温特建构主义或曰美国建构主义的概念,他就含蓄地引入了建构主义的另外一种分类方法,亦即以地缘-文化为基本特征的建构主义。既然有美国建构主义,就可能有英国建构主义、欧洲建构主义、中国建构主义、东盟建构主义等等。你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指出,存在两种结构:一是微观结构,二是宏观结构。在微观层面亦即单位层面上,可能存在多种路径,最终形成某种宏观的、体系层面上的观念结构。所以,我想提出这样一个地缘-文化概念,对建构主义另行分类。这样进行分类,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考虑。第一,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与自然结构不同,前者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亦即受到历史和地理位置的限制; 第二,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划定了社会活动的境域(context),行动者只能在这种境域中互动,他们不可能在超越这种境域中的空间和时间里进行互动,在这种境域中的互动产生了共有知识;第三,由于在微观层面上的互动有着明显的地缘文化特征,不同社会在微观层面上很少能够以完全相同的路径走向宏观结构。如果我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以地缘-文化为特征的建构主义学派就可以出现。也就是说,不同地缘-文化境域中的社会可以产生不同地缘-文化特征的建构主义流派。地缘-文化建构主义观是具有时空两个纬度的。你在过去的一封信中谈到中国的建构主义学派,并认为现实建构主义是可能出现的中国学派。但我觉得,中国建构主义研究议程中包含了较多的自由主义的成分。
温特:我非常喜欢你提出的地缘-文化建构主义的概念,不同地缘-文化可以产生不同流派的建构主义,遵循不同的微观层面路径,形成宏观层面的结构。实际上,你的论点说的是国际体系文化中的区域分异(differentiation)问题,亦即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结构。
我认为,这不仅仅在经验层面上是真实的,而且在理论层面上,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所以,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发掘(仅举一例,如果将这种理论与“文明冲突论”进行比较研究,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就涉及另外一个因素,即以国家冠名的理论,比如中国的建构主义学派。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提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自由建构主义比现实建构主义更有影响,我不知道这是否反映了真实的情况。我很想知道这方面的发展。我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米尔斯海默访问中国。他回来之后,谈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交流。从他的谈话中,我的感觉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是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也许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表现出其他的观点和自由主义的倾向。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自由现实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占主导地位,中国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外政策是现实主义成分多还是自由主义成分多。这可能是验证中国是否沿着一条独特的地缘-文化路径走向全球宏观结构这一命题。在这一方面,我不知道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是否能够充分解释中国的路径。还是在这一方面,我也不清楚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是否能够解释美国的对外行为,至少是目前美国的对外行为。
秦亚青:虽然在谈论中国建构主义的时候,我使用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词,但我觉得真正的、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主义还是不能与其他主流理论融合的。建构主义的大部分核心假定是社会性的。这可能是巴尔金的观点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是,一旦这些假定作为分析框架用于国际政治,它们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理论假定的不可通约特征。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这类实体理论的核心假定不是十分清晰,所以,融合说具有吸引力。我以为,需要进一步发展社会建构主义的核心假定,使其明显地不同于其他主流理论派,而不是通过观念谱域的拓展使其与其他理论融合。这样,才能够使建构主义在理论之林中保持独立的理论范式地位和独特的解释能力,而不至于消失在现实主义或是自由主义或是两者的思想海洋之中。
参考文献: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5, 2003, pp.325-342.
J. 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t Constructiv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6, 2004, pp.349-352.
E. H. Carr,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39/1964.
Daniel Deudney, “Dividing Realism: Structural Realism vs. Security Materialism on Nuclear Security and Proliferation,” Security Studies, No.1, 1993, pp.7-37.
Ma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Jeffrey W. Legro, “Which Norms Matter? Revising the ‘Failure’ of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1997,pp.31-56.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Knopf, 1948/1973.
John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1998, pp.855-885.
Martin Shaw, “Waltzing Alexander: Constructing the New American Ideology,” sussex.ac.uk/Users/haf3/wendt.htm, 2000.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Wesley, 1979.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1987, pp.335-370.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aja Zehfuss,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