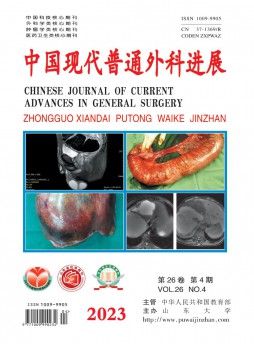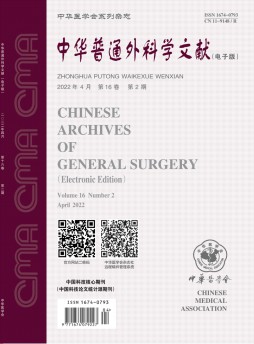普通论文范文
前言:写作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探索。我们为你提供了8篇不同风格的普通论文参考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给你带来宝贵的参考价值,敬请阅读。

普通论文范文第1篇
在《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里(2005年)终于找到答案。论文百事通那是该论文集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品,题目是“根深流长的杭州茶文化之开发畅想”(以下简称《畅想》)。这篇论文很长,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许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本文是专就《畅想》第一部分展开讨论,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两节叙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在这两节里展开他的“考古”和“论证”的。
关于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
说跨湖桥有茶,是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跨湖桥》发掘报告(2005)附录彩版四五第23。彩版的照片是一颗炭化的植物种子,附有茶的学名Camelliasinensis。在附录部分附录表二一(365页)地层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种实遗存和数量统计表中,注明探方T0510有一颗茶子,与彩版相呼应。此外,《跨湖桥》发掘报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态与经济》的“植被和气候”节,详细叙述了跨湖桥植被的演变内容,分为六部分:1,阔叶、针叶混交林阶段;2,干旱、较干旱稀疏林~草丛阶段;3,阔叶、针叶混交林发展阶段;4,沼泽植被发展阶段;5,干旱阔叶林混交林~草丛、沼泽发展阶段;6,落叶、常绿混交林~草丛发展阶段。这六节里叙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独没有提到茶(不论野生或栽培)。这不是遗漏或疏忽,是因这颗唯一的炭化种子,在制作附录彩版说明时,工作人员觉得它象茶子,临时给它一个茶的学名,因并未经专家鉴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叙述,就是说,所谓茶子只供业内人讨论鉴定,不供发表引用的。严格地说,这也是整理报告时不够慎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炭化种子的定名写作Camellia?表明没有最后鉴定,便不致引起误会。
听说《畅想》一文的作者??访问过文物考古所,该所同志一再告诉他这是初步鉴定,不可据为定论引用。但《畅想》的作者坚持作为茶子引用,所以这事与考古所无关,是《畅想》作者个人的见解。遗憾的是,《畅想》作者不去质疑或纠正考古所的鉴定,反而作为肯定依据,并大加发挥,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现今的茶树资源,除栽培种Camelliasinensis外,还有C.japonica,C.cuspidata,C.fraterna,C.lucidissima,C.chekiang-oleosa等(见《浙江林业自然资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业厅编,2002)。现在仅凭一颗炭化的种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种,不是其他茶种?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颗炭化种子根本不是茶属种子,这类差错在其他出土种子的鉴定失误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误鉴定为蚕豆、花生、芝麻,后来纠正)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介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种子鉴定的失误,是单纯的鉴定水平不够,鉴定人对被鉴定物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图。而“畅想”作者显然是抱着追溯茶文化源头,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调子发挥的。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釜,里面有一块焦黑的残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号的“药”釜和“药”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页)说明这份标本曾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叶类,没有进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茎叶。但“畅想”作者根据茶、药同源的理论,认为“药”釜应即茶釜(见《中国文物报》(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都没有肯定的“药”釜,一变而成肯定的茶釜,这样的“考古”能有说服力吗?百事通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釜,种类繁多,有大口的,小口的,平口的,??口的,文字部分将它们归纳为9型、18亚型、28式(218页),《畅想》对这些都不过问,只认定那个破釜是“茶釜”做文章。
无独有偶,《畅想》在另一段文字中还指出“从分布于杭嘉湖地区距今约6000年的崧泽文化中出土了最早的擂茶??来看,吾中华饮茶是诞生及成就于杭州湾一带的。”陶釜出土了,就定性为茶釜,陶??出土了,又定性为擂茶??。文物考古所的研究人员研究来研究去,没有肯定的陶器用途,到了《畅想》作者手中,马上定性为茶釜和擂茶??!多么干脆俐落。
关于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畅想》作者说他是“通过以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考证法”才认识到:“茶是诞生于森林中的,所谓‘茶’(古越语读若zo),最初其实是指‘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含意。因此,起初不仅许多食物与草药作‘茶’,就连房屋等也称为‘茶’,如‘舍’(古音so)等,即‘茶’之遗呼。同样,‘船’在古时又称‘槎’,也是茶之遗呼。”这真是一段绝妙的语言学和文字考证结合的论证,下面单就所谓古越语茶“zo”和“杂”的妙解提出质疑(舍和船的错误类似,从略)。
先要问作者怎样知道古越语的“茶”发zo音?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还是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如是引用他人的研究,应注明研究者和文献的出处;若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为什么不说明这"zo"的音是怎么得出来的?否则,读者怎么能轻易就相信?所谓古越语当然指2500年前春秋时的吴越国人说的语言(吴语和越语相通)。古越语与中原夏语根本不同,要经过翻译才能沟通。楚灭吴和秦灭楚越以后,秦及西汉,曾数次强迫越人大规模北迁至黄淮海一带,不愿迁徙的越人往东逃到沿海岛屿,(小部分更渡海去了日本)被称为外越;留下来的越人逃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深山密林里,被称为山越。北迁的越人最早和汉族融合,山越和外越经过与汉族的不断斗争(从略),最后与汉族完全融合(唐宋文献不再有山越的记载了)。
古越语汉化后,变成流行至今的吴方言。(吴方言通行于苏南、上海、浙江、江西东北、??南和闽西北,约有110多个县市,使用人口7000万左右。)所以古越语是已经消失的语言,谁也没有听过古越语。著名的古越女子所唱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是古汉语对古越语的翻译,《越人歌》的原音已无法听到。因壮语含有古越语的成分,故只有今天的壮族知识分子能破解《越人歌》的大部分内容。
现在的苏州话和温州话称茶为zo,这个“zo”音,在普通话里没有,在字典里也没有收。因此,笔者怀疑“畅想”作者所说的古越语称茶为zo,是误以吴方言为古越语。古越语有极个别词的音,还保留在现在的日语里,那是古越人东渡日本带去的,典型的如日语称稻为“ィネ”,即是古越语的稻词。而现在的吴方言称稻为dao,同普通话差不多,和古越语完全是两码事。古越语保留在汉语里、用汉字标音的也不少,但都是人名和地名的发语词,如人名“勾践”、“勾吴”之勾,及地名“姑苏”、“无锡”、“芜湖”、余姚”之姑、无、芜、余等,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有音无义。同样,“ィネ”之“ィ”也是发语词,“ネ”才是稻。如果古越语称茶为“zo”,试问发语词在那里?总之,《畅想》以吴方言之"zo",冒充古越语,是张冠李戴,以假乱真,但这种“论证”对于没有历史语言常识的人,有很大的权威性和欺骗性。
更为好笑的是,《畅想》作者说茶“最初是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遗意”,这种文字游戏论证,只能骗骗识简化字、不识繁体字的读者。“杂”字是解放后新创的简化字,原来的繁体字作“?s”,也可作“?j”,简化字“杂”是取“?j”的左半为“杂”,仍保留?j的音和义,以前的古籍和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个“杂”字。作者拿1950年代新造的简化字,同几千年前的“茶”字沟通论证,这种“贯通古今”的论证,真是象作者自己所标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百事通
如果作者辩解说,他文中的“杂”即指繁体字的“?j”。“?j”的本义是色彩驳杂,其右半的“隹”是静止的鸟,指它的羽毛色彩驳杂,发“杂”的音,如此而已。?j的驳杂义,如杂志、杂家、杂文、杂乱、杂交等,至今仍然广泛使用,唯独没有“对森林的利用”的义,这是作者的“独创。
作者在另一段中说“茶之音为古越语,则杭为越人。”所谓茶之音为古越语,已经驳正如上,接着这“杭为越人”更犯有常识性错误。“杭为越人”当然指杭州人是古越人后裔的意思。作者似乎对杭州的地理历史毫无所知。杭州的诞生与西湖密切相关,西湖在距今约万年前还是一个海湾,经历着不断的潮沼化和陆化,现代西湖形成的年龄,约在距今1860--1850年,即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233-237页,1997,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的前身是东汉时的钱塘县。那时的钱塘县,在现今西湖之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三面为山,一面滨湖,湖外尽是沙滩,不过是个山中的小县。杭州脱离山中小县的地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钱塘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后20年,到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以杭州为大运河的起点,地位才逐步显要起来。杭州的繁荣开始于唐,与本文无关,就不说了。“杭”与“航”同音同义,指过渡的地方,古代人是在这里渡航到南岸肖山的。2500年前的吴越国时期,吴国都在苏州,越国都在会稽(绍兴),吴越两国以钱塘江为界,在杭州一带渡航钱塘江,故杭州的吴山不称越山。现在的杭州那时还是水面下的滩涂,那儿来的“杭为越人”?作者可以辩解说,所谓杭为越人是指广义的杭州,包括今富阳、肖山、余杭在内,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上面已说过,秦灭越后,古越人经历各种斗争变故,业已完全与汉族融合,不管是狭义的或广义的杭州,称“杭为越人”都不能成立。即令杭为越人可以成立,那末,“苏为越人”、“绍为越人”、“姚为越人”、“宁为越人”…都可成立,“杭为越人”并没有专利权。新晨
普通论文范文第2篇
在《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里(2005年)终于找到答案。那是该论文集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品,题目是“根深流长的杭州茶文化之开发畅想”(以下简称《畅想》)。这篇论文很长,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许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本文是专就《畅想》第一部分展开讨论,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两节叙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在这两节里展开他的“考古”和“论证”的。
关于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
说跨湖桥有茶,是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跨湖桥》发掘报告(2005)附录彩版四五第23。彩版的照片是一颗炭化的植物种子,附有茶的学名Camelliasinensis。在附录部分附录表二一(365页)地层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种实遗存和数量统计表中,注明探方T0510有一颗茶子,与彩版相呼应。此外,《跨湖桥》发掘报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态与经济》的“植被和气候”节,详细叙述了跨湖桥植被的演变内容,分为六部分:1,阔叶、针叶混交林阶段;2,干旱、较干旱稀疏林~草丛阶段;3,阔叶、针叶混交林发展阶段;4,沼泽植被发展阶段;5,干旱阔叶林混交林~草丛、沼泽发展阶段;6,落叶、常绿混交林~草丛发展阶段。这六节里叙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独没有提到茶(不论野生或栽培)。这不是遗漏或疏忽,是因这颗唯一的炭化种子,在制作附录彩版说明时,工作人员觉得它象茶子,临时给它一个茶的学名,因并未经专家鉴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叙述,就是说,所谓茶子只供业内人讨论鉴定,不供发表引用的。严格地说,这也是整理报告时不够慎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炭化种子的定名写作Camellia?表明没有最后鉴定,便不致引起误会。
听说《畅想》一文的作者曽访问过文物考古所,该所同志一再告诉他这是初步鉴定,不可据为定论引用。但《畅想》的作者坚持作为茶子引用,所以这事与考古所无关,是《畅想》作者个人的见解。遗憾的是,《畅想》作者不去质疑或纠正考古所的鉴定,反而作为肯定依据,并大加发挥,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现今的茶树资源,除栽培种Camelliasinensis外,还有C.japonica,C.cuspidata,C.fraterna,C.lucidissima,C.chekiang-oleosa等(见《浙江林业自然资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业厅编,2002)。现在仅凭一颗炭化的种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种,不是其他茶种?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颗炭化种子根本不是茶属种子,这类差错在其他出土种子的鉴定失误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曽误鉴定为蚕豆、花生、芝麻,后来纠正)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介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种子鉴定的失误,是单纯的鉴定水平不够,鉴定人对被鉴定物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图。而“畅想”作者显然是抱着追溯茶文化源头,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调子发挥的。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釜,里面有一块焦黑的残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号的“药”釜和“药”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页)说明这份标本曾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叶类,没有进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茎叶。但“畅想”作者根据茶、药同源的理论,认为“药”釜应即茶釜(见《中国文物报》(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都没有肯定的“药”釜,一变而成肯定的茶釜,这样的“考古”能有说服力吗?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釜,种类繁多,有大口的,小口的,平口的,圏口的,文字部分将它们归纳为9型、18亚型、28式(218页),《畅想》对这些都不过问,只认定那个破釜是“茶釜”做文章。
无独有偶,《畅想》在另一段文字中还指出“从分布于杭嘉湖地区距今约6000年的崧泽文化中出土了最早的擂茶缽来看,吾中华饮茶是诞生及成就于杭州湾一带的。”陶釜出土了,就定性为茶釜,陶缽出土了,又定性为擂茶缽。文物考古所的研究人员研究来研究去,没有肯定的陶器用途,到了《畅想》作者手中,马上定性为茶釜和擂茶缽!多么干脆俐落。
关于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畅想》作者说他是“通过以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考证法”才认识到:“茶是诞生于森林中的,所谓‘茶’(古越语读若zo),最初其实是指‘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含意。因此,起初不仅许多食物与草药作‘茶’,就连房屋等也称为‘茶’,如‘舍’(古音so)等,即‘茶’之遗呼。同样,‘船’在古时又称‘槎’,也是茶之遗呼。”这真是一段绝妙的语言学和文字考证结合的论证,下面单就所谓古越语茶“zo”和“杂”的妙解提出质疑(舍和船的错误类似,从略)。
先要问作者怎样知道古越语的“茶”发zo音?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还是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如是引用他人的研究,应注明研究者和文献的出处;若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为什么不说明这"zo"的音是怎么得出来的?否则,读者怎么能轻易就相信?所谓古越语当然指2500年前春秋时的吴越国人说的语言(吴语和越语相通)。古越语与中原夏语根本不同,要经过翻译才能沟通。楚灭吴和秦灭楚越以后,秦及西汉,曾数次强迫越人大规模北迁至黄淮海一带,不愿迁徙的越人往东逃到沿海岛屿,(小部分更渡海去了日本)被称为外越;留下来的越人逃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深山密林里,被称为山越。北迁的越人最早和汉族融合,山越和外越经过与汉族的不断斗争(从略),最后与汉族完全融合(唐宋文献不再有山越的记载了)。
古越语汉化后,变成流行至今的吴方言。(吴方言通行于苏南、上海、浙江、江西东北、晥南和闽西北,约有110多个县市,使用人口7000万左右。)所以古越语是已经消失的语言,谁也没有听过古越语。著名的古越女子所唱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是古汉语对古越语的翻译,《越人歌》的原音已无法听到。因壮语含有古越语的成分,故只有今天的壮族知识分子能破解《越人歌》的大部分内容。
现在的苏州话和温州话称茶为zo,这个“zo”音,在普通话里没有,在字典里也没有收。因此,笔者怀疑“畅想”作者所说的古越语称茶为zo,是误以吴方言为古越语。古越语有极个别词的音,还保留在现在的日语里,那是古越人东渡日本带去的,典型的如日语称稻为“ィネ”,即是古越语的稻词。而现在的吴方言称稻为dao,同普通话差不多,和古越语完全是两码事。古越语保留在汉语里、用汉字标音的也不少,但都是人名和地名的发语词,如人名“勾践”、“勾吴”之勾,及地名“姑苏”、“无锡”、“芜湖”、余姚”之姑、无、芜、余等,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有音无义。同样,“ィネ”之“ィ”也是发语词,“ネ”才是稻。如果古越语称茶为“zo”,试问发语词在那里?总之,《畅想》以吴方言之"zo",冒充古越语,是张冠李戴,以假乱真,但这种“论证”对于没有历史语言常识的人,有很大的权威性和欺骗性。
更为好笑的是,《畅想》作者说茶“最初是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遗意”,这种文字游戏论证,只能骗骗识简化字、不识繁体字的读者。“杂”字是解放后新创的简化字,原来的繁体字作“雜”,也可作“雑”,简化字“杂”是取“雑”的左半为“杂”,仍保留雑的音和义,以前的古籍和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个“杂”字。作者拿1950年代新造的简化字,同几千年前的“茶”字沟通论证,这种“贯通古今”的论证,真是象作者自己所标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
如果作者辩解说,他文中的“杂”即指繁体字的“雑”。“雑”的本义是色彩驳杂,其右半的“隹”是静止的鸟,指它的羽毛色彩驳杂,发“杂”的音,如此而已。雑的驳杂义,如杂志、杂家、杂文、杂乱、杂交等,至今仍然广泛使用,唯独没有“对森林的利用”的义,这是作者的“独创。
作者在另一段中说“茶之音为古越语,则杭为越人。”所谓茶之音为古越语,已经驳正如上,接着这“杭为越人”更犯有常识性错误。“杭为越人”当然指杭州人是古越人后裔的意思。作者似乎对杭州的地理历史毫无所知。杭州的诞生与西湖密切相关,西湖在距今约万年前还是一个海湾,经历着不断的潮沼化和陆化,现代西湖形成的年龄,约在距今1860--1850年,即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233-237页,1997,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的前身是东汉时的钱塘县。那时的钱塘县,在现今西湖之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三面为山,一面滨湖,湖外尽是沙滩,不过是个山中的小县。杭州脱离山中小县的地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钱塘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后20年,到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以杭州为大运河的起点,地位才逐步显要起来。杭州的繁荣开始于唐,与本文无关,就不说了。“杭”与“航”同音同义,指过渡的地方,古代人是在这里渡航到南岸肖山的。2500年前的吴越国时期,吴国都在苏州,越国都在会稽(绍兴),吴越两国以钱塘江为界,在杭州一带渡航钱塘江,故杭州的吴山不称越山。现在的杭州那时还是水面下的滩涂,那儿来的“杭为越人”?作者可以辩解说,所谓杭为越人是指广义的杭州,包括今富阳、肖山、余杭在内,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上面已说过,秦灭越后,古越人经历各种斗争变故,业已完全与汉族融合,不管是狭义的或广义的杭州,称“杭为越人”都不能成立。即令杭为越人可以成立,那末,“苏为越人”、“绍为越人”、“姚为越人”、“宁为越人”…都可成立,“杭为越人”并没有专利权。新晨
普通论文范文第3篇
现有学者对期刊特征和被引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期刊载文量、基金论文比、论文合著者、引文特征、出版时滞等方面,具体如下:
(1)期刊载文量。Elizee等[1]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读者数量增加,用户可以更方便地获取论文,期刊载文量的增加可以提高期刊被引量。陈留院[2]以36家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为例,发现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与载文量成正相关。刘岩等人[3-5]的研究都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但是,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的观点。譬如,王钟健等[6]以农业经济类期刊为样本的研究显示,期刊载文量的增加与期刊学术质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2)期刊基金论文比。Shen等[7]对ACMSIGIR、ACMSIGKDD两个国际会议论文的研究,以及Pqi等[8]对2010~2012年WOS收录的自然科学论文的研究均表明,基金论文的学术影响力高于普通论文。戚尔鹏和叶鹰[9]通过分析WOS数据收录的2010~2012年基础学科论文,发现除逻辑学以外,所有基础学科的基金资助引用优势为正,这表明基金论文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力普遍高于非基金论文。刘睿远等人[10-12]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但是,王谦等[13]对中文医学核心期刊的研究和林丽芳[14]对高校学报的研究却显示,基金论文比与期刊评价指标不完全具有相关性,基金论文与其学术影响力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而徐晶等[15]分析2007~2011年口腔医学类期刊基金论文的引用情况之后,指出基金论文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期刊质量,但是不能单纯依此评判期刊的质量。
(3)论文合著者。Glänzel和Thijs[16]的研究发现,生物医学、化学和数学领域论文的平均引用率随着合作者的数量而增长;Leimu和Koricheva[17]进一步指出,4个共同作者的平均引用率高于3个、2个或1个。钟镇[18]以2004~2008年WOS图情学科研究型论文为样本,发现按照合著人数进行分组,图情学科4人合著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最高,但合著者的数量与论文被引影响力之间不能划等号,合著作者数的提高未必能带来论文被引频次的提高。类似的,Glänzel和Schubert[19]的国际合著研究也发现,相当一部分国际合著论文的被引绩效低于研究样本的平均水平。Abramo和Ange⁃lo[20]的研究同样拒绝了作者数量与期刊影响力之间的正相关假设。论文合著研究除了作者之间的合作,还包括机构之间的合作。赵金燕[21]发现,机构分布数与被引频次高度相关,对被引频次有较强的解释能力。盛丽娜[22]也认为,用作者机构的分布情况评价科技期刊影响力优于使用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
(4)引文特征。Biglu[23]以SCI和WOS为数据源,发现期刊的引文量和被引量具有一定的线性关系。期刊的篇均引文量越大,相应的被引量也就越高,期刊引文量和期刊的被引量之间会形成“马太效应”。Didegah和Thelwall[24]也认为适当数量的参考文献将提高其获得更多被引用的可能性。在国内,程慧平和万莉[12]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平均引文量表明了学术论文的研究起点和深度,可以反映论文的学术水平,而且周吉光等[25]还提出,期刊引用半衰期衡量了期刊刊载文献的参考文献的时效跨度,期刊引用半衰期短,意味着该刊对较短期内发表的较新的研究文献的兴趣度。
(5)期刊出版时滞。Tsay等[26]对医学期刊2000年JCR相关数据的研究发现,出版频次较高的期刊被引频次也高。Shen等人[27]以Nature、Science、Cell三种期刊为对象的研究显示,期刊发文时滞与被引频次之间存在相关性。与此类似,Pautasso和Schäfer[28]发现,生态学期刊平均编辑延迟天数与影响因子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是,韩牧哲等[29]对图书情报学中文核心期刊的研究却表明,虽然论文的影响力与其发表时滞的长短存在相关关系,具有能使论文影响力最大化的理想时滞区间,但是,发表时滞并非越短越好。同样,刘俊婉等[30]以Scientometrics和《情报学报》为例,发现期刊论文的发文时滞与论文被引频次之间仅具有相关性趋势,但并不显著。综上,虽然已有不少研究分析了期刊特征与被引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许多方面并未达成共识。为了准确地揭示国内期刊特征与被引之间的关系,从而有针对性地指导工作实践和管理决策,本研究在系统梳理现有期刊评价指标的基础上,提炼出11个期刊特征指标,分析它们与期刊被引之间的关系。
2数据获取与主成分回归分析
2.1数据获取
学术期刊论文效用的体现是一个逐步呈现的过程,因此,本研究以期刊后,5年内累计获得的被引用频次作为衡量期刊影响力和质量的指标。为了保证数据来源的一致性,我们以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中国引文数据库》、《期刊发展要素统计分析》作为期刊特征指标和被引用数据的来源。具体如下:(1)《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可被引文献量、可被引文献比、基金论文比、引用半衰期、引用期刊数;(2)《期刊发展要素统计分析》:作者数、机构数、出版时滞、本刊比重、全国比重;(3)《引文数据库》:篇均引文量和总被引。由于中国知网最新数据统计截止到2015年底,所以,本研究采用生物学、物理力学、地质学三个学科,共218种期刊2011~2015年的被引频次,以及各刊2011年的特征指标。
2.2主成分回归分析
本研究运用因子分析提取原始特征指标的公因子,进而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特征指标与被引之间的线性关系。数据分析使用SPSS20.0。
2.2.1因子分析
(1)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见表1)显示,生物学、物理力学和地质学三个学科的KMO分别为0.699、0.726、0.683,Bartlett球形检验p值均小于0.001,所选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2)贡献率和载荷矩阵。采用固定提取方法,生物学和物理力学提取出F1、F2、F3、F4、F5、F6六个主成分,地质学提取出N1、N2、N3、N4、N5五个主成分(见表2)。这些主成分对生物学、物理力学、地质学期刊被引的累计贡献率分别为92.638%、92.712%、86.413%。
2.2.2回归分析
(1)模型拟合度R方检验。以被引为因变量,以因子分析提取的公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生物学、物理力学、地质学三个学科的确定系数R2分别为0.762、0.913、0.699,表明生物学和地质学回归模型拟合度较高,物理力学回归模型拟合度非常高。
(2)显著性检验。回归模型的F检验结果(表4)显示,生物学、物理力学、地质学三组样本的p值均小于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
2.2.3贡献度分析
对回归方程进行偏回归系数t检验,以此为基础进行逐步回归得出具有显著相关性变量的贡献度。对回归方程进行偏回归系数t检验,结果(见表5)表明:生物学中F1、F3、F6三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t检验p<0.05;物理力学中F1、F4、F6三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t检验p<0.05;地质学中N1、N2、N3、N4四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t检验p<0.05。同时,采用逐步回归法分别分析得出(见表6):生物学中F1的贡献度最大为62.9%,F3和F6的贡献度分别为5.7%和6.2%;物理力学中F1的贡献度最大为83.1%,F4和F6的贡献度分别为4.5%和2.1%;地质学中N1的贡献度最大为40.7%,N2的贡献度为18.1%,N3的贡献度为6.3%,N4的贡献度为6.5%。
3讨论
3.1强贡献度公因子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F1(N1)公因子与被引显著相关,并且对被引有较高的贡献度。尤其是物理力学期刊,其贡献度高达83.1%。本研究支持了何荣利、王群英、赵金燕、Glänzel等人的研究结论,即载文量、作者数和总被引成正相关[16,21,31,32]。期刊论文在文献传播过程中,作者数和发文机构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扩大论文的传播范围,使得其快速地被部分群体所认知,从而形成引用,提高期刊的被引频次。同样,引用期刊数反映了期刊的引用广度,体现了该期刊对相关学科的渗透和交融,引用期刊数越多越容易获得相关学科的关注和引用。F1和N1公因子均从可被引文献量、作者数、机构数、全国比重、引用期刊数五个原始变量中提取。五项特征指标的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可被引文献量、作者数、机构数、全国比重彼此之间都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该结果进一步体现了F1(N1)对被引强贡献度的合理性。
3.2弱贡献度公因子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篇均引文量、基金论文比、本刊比重、引用半衰期、可被引文献比等指标虽对被引具有一定的作用,但贡献度相对较低。
(1)基金论文比。将基金论文比作为期刊评价指标是否合理,一直备受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要重视基金论文比的作用[11,34];而另一些学者则明确表示,基金论文比是一个欠科学的期刊评价指标[35],甚至应该被彻底否定[36];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持比较中立的态度,认为基金论文比有一定的作用,应客观对待[37]。本研究结果显示,生物学和物理力学期刊的基金论文比对被引频次的贡献度分别为6.2%和2.1%,地质学期刊的基金论文比和篇均引文量共同提取的公因子贡献度为18.1%。总体而言,基金论文比对期刊被引的贡献度不高。因此,可将基金论文比作为期刊评价的辅助指标,但不应过分强调基金论文比的作用。
(2)篇均引文量。本研究发现,期刊的篇均引文量对被引存在学科差异。地质学期刊篇均引文量和基金论文比对被引的总贡献度为18.1%,生物学期刊篇均引文量对被引贡献度为5.7%,而物理力学期刊篇均引文量与被引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一结果部分支持了Biglu、梁春慧和葛赵青等的观点[23,38,39]。从引文功能的角度,期刊的引文具有文献再发现的功能,一篇论文引用的文献越多,越容易得到相关领域研究人员或机构的关注,其被引用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再者,研究人员检索相关文献时一般采用关键词、主题词或者通过引文索引检索,因而无论是从文献本身的功能,还是从研究人员查找文献的习惯,都会导致平均引文数量较高的期刊获得更多的关注,相应的被引率也会提高。从引文价值的角度,较多的引文数量可以反映该论文的研究基础扎实,可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因而获得更多研究人员的关注和引用。
(3)引用半衰期。引用半衰期是计量学科知识老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引用半衰期越短,意味着期刊引用的近期文献越多,表示该刊更关注最新的研究成果。而最新的研究成果会得到更多研究人员的关注,被引用的概率也就越高;反之亦然,期刊引用的文献比较老,意味着该期刊发表的论文很可能存在重复性研究,其被引用的可能性降低。本研究结果显示,地质学期刊的引用半衰期与被引虽存在负相关性。这虽然支持了顾璇提出的期刊引用半衰期越短,被引越高的观点[40],但是,应该注意到引用半衰期对被引的贡献度仅为6.5%。而生物学和物理力学期刊的引用半衰期与被引之间的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组数据的分析结果提示,将引用半衰期作为评价期刊质量或办刊水平指标的依据似乎并不充分。
(4)本刊比重和可被引文献比。由表3可知,地质学中N3(本刊比重、可被引文献比共同提取)对总被引的贡献度为6.3%,物理力学中F4(本刊比重)对总被引的贡献度为4.5%。本刊比重虽然可以体现期刊的专业化程度,且对期刊被引具有一定贡献,但是整体影响有限。如何评价该指标与期刊影响力乃至期刊质量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探索。
3.3无贡献度因子
许多研究者认为,出版时滞长会导致文献老化,从而降低甚至失去被引用的机会。Tsay、Pautasso以及高慧芳等的研究都支持了上述观点[26,28,41]。但是,本研究结果却显示,无论生物学、物理力学还是地质学期刊,出版时滞与被引之间的关系均不显著。这种现象是仅存在于这三个学科还是普遍现象,抑或国内外期刊存在差异,尚有待进一步验证。
普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辅仁大学;沦陷时期;战时教育;董毅日记
北平沦陷后,原有高校大量南迁或停办。整个沦陷时期,一直坚持原有办学的高校为数不多[1],其中,辅仁大学作为沦陷前北平“五大学”之一,坚持传统的办学特色,抵制日伪的奴化政策,被誉为“抗日大本营”[2](p.164)。学界对于沦陷时期的辅仁大学已有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多聚焦于校长陈垣及国民党政权对辅仁大学的组织等问题,而对辅仁学生在校的真实学习状态少有关注。本文以1938年9月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的董毅的日记①为主体史料,从一个普通学生的角度观察辅仁大学在沦陷时期的办学特色,以及沦陷区青年学生对抗战的感受和认知。
一、坚守在沦陷区进行战时教育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大学教育受到严重破坏,清华等多所高校陆续南迁,最初几年,“硕果仅存,赖以支撑这半壁江山的,只有燕京、辅仁两私立大学。这两所学校,因是教会所立,由外人为靠山,所以尚能苟延残喘”[3](p.27)。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在“惊涛巨浪中,屹然未动”,一同被视为“鲁殿灵光”[4]。1942年“珍珠港事件”之前,“燕大、辅大还保持着半独立”[5](p.11)。“珍珠港事件”之后,燕京大学也最终被迫关闭[6](p.58),仅剩辅仁大学与其他日伪直接进驻的大学有所不同[7](p.240),故在一般民众眼中,当时的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站在教育界的先锋”[8]。沦陷时期,青年学生报考高校会有所比较和考量,如有人所言:“处在日寇占领时期,京津地区比较有名的大学是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北大虽是老字号,但是日伪直接管理的学校,不甘心报考。燕京大学是英、美系统的大学,已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随时将面临被封闭接收的噩运。只有辅仁大学,虽校龄很短,但因是德国教会主政,而德国是轴心国之一,日寇因同盟关系,不得不在形式上宽松些。许多著名老师也多齐集辅仁,因此成为大多数青年学子报考的焦点”[9](p.264)。所以,在整个沦陷时期,辅仁大学不仅“仍照常开办”[10](p.697),其规模还得到进一步扩大。北平沦陷后,“辅仁在应付上,虽较困难,差幸尚能上课”[11]。师生们深切地感受到学校所处的困难境遇,但“上下一心,中外一致,每次应付困难事件,总抱不屈不挠的态度……英、美、德使馆方面,也能随时赞助”,以至在整个沦陷时期辅仁大学能坚持原有教学风格[10](p.697)。辅仁大学借助教会的力量应对日伪政府管控的同时,一直和国民政府保持联系,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秘密指令,保持开放状态,基本延续原有注重民族文化的教学设置,培养了青年的爱国精神。辅仁大学还建议与京津地区其他国际教育组织协力合作,以如下三条原则为指导:“(一)独立管理(二)学术自由(三)不悬伪旗帜;以示正义不屈。”[12](p.7)正因辅仁大学在抗战时期坚持原有的办学特色,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把辅仁大学与后方大学一同对待,无条件地承认战争结束时辅仁大学的学历证书。而沦陷时期日伪控制的其他高校的毕业生,则必须参加补习和考试才能得到国民政府的学历认可[13](pp.209-213)。这是国民政府对辅仁大学在沦陷时期坚持原有教学方针的认可,同时也是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的落实。战争开始时,对于教育是要服务于战争,是应该保持正常的教育体系,社会上存在很多争论。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虽然教育不可以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但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不应把所有的青年都无条件地从课堂、实验室、研究室赶到战场上去[14](pp.128-129)。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鼓励青年学生在战争时期坚持完成教育。
二、坚持开设传统文化课程
占领北平后,日本“为使中国人民彻底认识‘东亚新秩序’理念”,非常重视各种教育,控制了北平原有学校,开设了各种师资训练学校和“职业学校”,强迫中国子弟入学。就大学教育方面,日本开展所谓事业本位的教育,设立了伪“北京工商学校”,以及伪“北京大学”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理学院、文学院等。日伪政府除从日本方面聘请教授,设立日本文学、日本美术、日本精神讲座等科外,还组织了“临时政府教科书编审科”,将各校课本一律改成奴化色彩浓厚的所谓“汉奸”教科书[15](p.24)。沦陷时期,很多过去的国立大学,都由日伪组织直接控制,校门前竖起日本国旗,派入大批日籍教师和教官,有的学校师生每天进校门时,要向日本国旗、日本军官行礼。学校强迫学生读日文,有的学校必须用日文课本,或不准读中国历史,有的大学则用从东北运来的伪“满洲国”编写的历史教材,进行奴化教育。日本在华北的教育政策不似东北那样强化,重在控制而不是发展,因此,“也不是无漏洞可钻”[13](pp.174-175)。辅仁大学虽然从外部也不能摆脱日伪统治的管理,如当时日伪政权各种管理机构不下十几个①,但由于德国人及教会方面与日伪政府周旋,经过往复协商,校内教学体系仍保持了一定的自主性,如文理各科课程仍用原有教材,不用日文课本,不悬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程[7](pp.239-240)。与日伪直接控制的大学不同,辅仁大学在整个沦陷时期的课程设置仍基本保持原有体系,坚持用中国课本。如学生在第一学年一般性的必修课较多,专业性课程较少。学校特别要求,无论何院、何系,在第一学年必修“国文”及“英语”等语文课,而“国文”每两周有一次作文,并选优者于“以文会友”玻璃橱窗公开展示。“于此不难想象校方强化语文教育,以乃重视民族文化,辛勤耕耘的一番苦心”[16](p.270)。董毅第一学年,每周四也选了必修课国文[17](p.37)。辅仁大学国文课的目的是强化语文教育。董毅所上国文课内容有二:一是讲授、背诵汉文经典。如董毅在国文课上听授了《洪亮吉与崔瘦生书》《让太常博士书》,背诵了《后汉书•吴裕传》等[17](p.12)。二是训练学生的汉文写作能力,如写作《论文字之功用》《读书小记(别记)》《春日纪游》等题目的文章。有时教师也会给学生讲“普通错汉字”[17](p.99)。国文考试所出题目也以此为宗旨,如标点几段《后汉书》、写作《一年来对国文作文之兴趣》为题的文章等[17](p.106)。对于国文系学生来说,这些是最基本的训练。董毅显然比较喜欢国文,认为自己这个科目学得不错,在考国文的时候自认“不甚难,答的还满意”[17](p.21)。辅仁大学加强汉语教育,以此来重视传统民族文化,国文作为必修课只是其中一个措施。其他科目辅仁大学也基本保持了沦陷前的课程设置,董毅1939年所选课程便可证明这一点。董毅在日记中记载了他选的课程,1939年上半年(即一年级第二学期),除了体育、英语、国文等必修课,专业课程有目录学、声韵学、中国文学史、逻辑学、文字学、中国现代文学,只有日语课是为了应付时局而开设的新课。1939年下半年(即第二学年第一学期),除了英语外,其余均为专业相关课程,包括唐宋诗、词及词史、文字学名著、经学通论、各体散文习作、伦理学、中国小说史、新文艺习作。这些专业课程都是延续沦陷前国文系的课程设置,教师也多是沦陷之前即在国文系授课,如目录学余嘉锡、声韵学及文字学名著沈兼士、逻辑学英千里、文字学陆宗达①、唐宋诗储皖峰、词及词史孙人和、伦理学伏开鹏、中国小说史孙楷第等。从教师配置与课程设置来看,辅仁大学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继承性,特别是国文系,依然侧重语文教育,重视民族传统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日伪的文化殖民、文化侵略,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脉与内在精神。如储皖峰开设的唐宋诗课程,训练学生作诗填词。
1939年10月的一次课,储先生出的两道题目,一是《重九登白塔》,一是《晚秋新雨》[17](p.219)。董毅交上了自己所做的诗,一周后,储先生发回修改后的诗。1939年11月的一次课,储先生又出了两个题目,让学生写《雾松》和《司马池》。董毅自称“向来不会作诗”[17](p.219),但经过学习,能够按时完成这些诗词作业。日伪政府为进行奴化教育,很多有关中日关系及现代中国的书籍都被查禁,但对中国历史书籍的查禁不太严格,对大学内中国历史的课程监控也不甚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就在校内开设了历史课程。1939年下半年,作为国文系学生的董毅选修了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陈垣对学生要求严格,在课堂上讲授《史记》《汉书》等经典史书,并留了许多课后作业。如1939年10月初,陈垣让学生整理三国以前现存书目录。董毅为了完成作业,到学校图书馆查阅了《四库总目提要》,还到国立北平图书馆查阅了一些参考书[17](p.197),花费了很多工夫,一个多星期后的10月16日课上交了作业[17](p.205)。之后,陈垣又给学生们陆续留了两个题目,整理“史汉异同目录”与《玉函山房辑佚书》引用书目。董毅和大多数普通学生一样,从心里认可校长的讲授,认为“很有条理也明白”[17](p.205),认真地去完成作业。以整理《玉函山房辑佚书》引用书目为例,董毅共“抄了共有五百六七十种之多”[17](p.242)。陈垣对学生的作业认真批改。董毅对历史的学习是主动的,并不是羡于校长的名望,因此,听课“两小时精神专一”[17](p.268)。课余时间,董毅也会去图书馆看历史书籍,旁听感兴趣的历史课程[17](p.190)。从董毅的日记还可看出,国文系各科的考试也多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方面的题目。如1939年11月的季中考试,词及词史的考试题目是作一首词《浣溪沙》或者“温韦李三人合论”[17](p.254);文字学名著的题目是“试述读段注说文之方法”[17](p.256);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题目是“后汉书之叙事法与史汉有大不相同之点,试详述之”[17](p.257);经学通论考试题目是“‘经学展史’开辟时代书后”[17](p.259)。即便是与时代联系比较紧密的新文艺习作也考的是诸如“如何写一个剧本”“舞台艺术的重要”“评父归”等题目[17](p.255),与日伪政府所进行奴化宣传的内容毫无联系。从以上课程设置和董毅所学内容可以佐证,辅仁学生“对于北京市政府提出的意识形态或有关日本和德国研究的题目毫无兴趣”[13](p.210),而是仍专注于学习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辅仁开设的科目培养了青年的爱国精神,延续了民族教育。
三、辅仁师生对时局的应对
国文系教师多是沦陷前就已经在辅仁大学任教,如前述余嘉锡、沈兼士、储皖峰等,他们在相关研究领域内皆颇有声望。其中,沈兼士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亦是潜伏在北平的国民党党务人员。北平沦陷后,受教育部委托维护辅仁大学校务,并和辅仁大学秘书英千里、教育学院院长张怀等秘密组织“炎社”,取顾炎武的“炎”字,以示抗日①。沈兼士还受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骅的委托,组织北平文教协会,以抵抗日伪文化殖民[18]。教师中除了沈兼士和英千里二人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其他人大都在党派之外。但身为中国知识精英,处于日伪统治之下,民族感情受挫及心态压抑是普遍存在的,他们虽能正常上课,领得一份薪水以养活家口,但授课时往往表现出消极、愤懑的情绪,甚至敷衍应付的态度。作为学生的董毅,在上课时对此有真切的感受。董毅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英语课由宋致和讲授。1939年春季学期3月6日开学,但只讲了三个月,6月10以后便连续三次课告假,直到会考[17](pp.101-105)。沈兼士在给学生上声韵学和文字学名著时,也常发牢骚,讲些与课程无关的话,有时也不去上课[17](p.217)。或许是忙于秘密抗日工作,或许是发泄心中悲愤,在作为学生的董毅看来,沈兼士“劲头还不小,脾气也不好,时常要骂一顿人才舒服似的”[17](p.193)。其他课程如中国现代文学、国文、经学通论、小说史、唐宋诗、伦理学等的教师,在董毅看来,在上课时也时有偷工减料等现象[17](p.38)。从表面看,这是教师对教学的应付,但实则是在沦陷的大环境下教师们的消极抵制态度。在沦陷的北平,由于各种原因难以离去的教师,面临着远比年轻学生沉重得多的精神和生活压力。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继续留在大学任教,虽然辅仁大学与其他日伪直接控制的学校有所区别,但教师们仍感受着当“亡国奴”的屈辱,授课时难以保持如战前的教学热情与责任感,这是年纪尚轻的董毅所不能完全理解的。沦陷时期,辅仁大学依然遵守战前南京政府设定的教学日历和国立节假日。辅仁大学有宗教背景,天主教会的相关节日,如教皇即位日、耶稣升天瞻礼、公教瞻礼、圣诞日等皆放假。日伪政权规定的纪念日,如9月22日“临时政府”成立纪念日、“政府”成立周年纪念日等,也命令各学校放假[17](p.278),但辅仁大学对其名称做了一定变通,尽量减少日伪色彩。如“政府”成立周年纪念日,辅仁大学不得不与全市大中小学一同放假,但“却美其名曰‘停课一日’”,董毅理解校方的用心,称赞此举“妙哉!”[17](p.78)日军打了胜仗,往往令各学校举行集会庆祝,辅仁大学则坚持“不参加‘祝捷’集会”等活动。[19]同时,辅仁大学还继续遵行南京政府战前设定的假日,如上半年放春假,元旦放三天假,以及双十节放国庆假等。辅仁大学这样的节假安排,对学生保持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具有一定作用。辅仁大学从创校起,就非常重视开展各种体育活动,以锻炼学生身体素质。
在沦陷时期,开展体育活动,隐含着为国家培养强健青年、增强民族力量的爱国意味,陈垣等校领导更予重视和支持。体育课主要教授健康操(相当于现在的广播操)、各种球类和田径的基本技能,不及格者不得毕业[20](p.191)。董毅在一年级第一学期,每周上两次体育课[17](pp.6-38),第二学期,每周又增加了两次课外运动,分别在周一、周五的早上7—8点,全体一年级学生集中做一个小时的“辅仁十一”团体运动。体育及团体运动的强化,有益于提高青年学生的身体素质与团体合作精神,这在国难时代有着特别的意义。在日伪政府的压力下,辅仁大学为了生存不得不开设了日文课。担任董毅日文课的教师不是日本人,授课多应付,“讲得很少”[17](p.95),有时“胡聊有半小时”就下课了[17](p.38)。这位教师虽然教授日文,但显然有民族意识,关心时局。1939年过完年,3月9日第一次上日文课,这位教师没有讲日文课本,而是讲述了去上海的所见所闻。在日伪言论管制下,董毅记日记有所避忌,他在日记中并未写明教师所讲的具体内容,但他说学生们听得“着实过瘾”[17](p.37)。可以推测,能引起青年学生如此兴致,应该是大家关心的时局新闻。董毅入学时,一年级已开设了日文课,学生们对日文课的反映是:“谁念日文就是准备做汉奸”[21](p.207)。但又不得不上,学生们只得消极应付,“简直是应卯”[17](p.48)。董毅说日文是其“不高兴的功课”[17](p.61),平时“一点也没念”[17](p.93),考前临时学几句,“马马虎虎”[17](p.21),应付考试而已。像董毅一般的青年学生,在遭受日本侵略和奴役之下,普遍怀有仇日爱国之心,对于日本占领者强制推行的日文教学,自然视之为“汉奸”课程而抱有抵制态度。据辅仁大学学生回忆,当时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学生们,“每天所见所闻所受的都不是一个青年人所能忍受的”,“‘走’的意念时时刻刻都酝酿在心头”[21](p.205)。董毅的许多亲友同学去了南方,与董毅保持着通讯联系。董毅在心中“羡慕他们,钦佩他们的勇敢,而自惭自己不能去南方”,担心他们笑自己懦弱、无能、没有魄力、不爱国,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焦虑,他在日记中记到:“个人有个人的环境,环境及一切允许,你自然可以毫无所留恋的远走高飞,但是我是不同的,家庭第一样经济是不允许我走,第二样尤其是重要的,母亲没有人照顾,弟妹们都很小,父亲既老且病,所以我为了父亲的病即便暂时也得留在家中,至少我觉得我在家中比不在家中好些,可是什么事都不能太圆满,至于别的不合适,只有顾不到了,所以我不去南方有我自己的一番道理和苦衷,或可以说是理由吧!”[17](pp.39-40)留在辅仁的学生有不少与董毅情况类似①。虽然辅仁大学受到日本人干涉较少,但在整个北平都沦陷的情况下,师生们同样感受到当“亡国奴”的屈辱,不甘心受敌伪统治,愿意离开北平到非敌占区生活学习。从沦陷开始,辅仁大学学生便纷纷南下到国统区。如1939年8月,辅仁大学的训导主任伏开鹏护送学生南下[22](p.377)。1940年1—2月间,北平市公安局查知辅仁大学的20余名学生准备联合赴重庆、昆明等地投考西南大学及航空军校[23](p.241)。1940年3月,北平市公安局又侦查得知辅仁大学3名学生准备前往昆明投考西南联合大学等[24](p.243)。在沦陷时期,平津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普遍向往南方,有条件的纷纷南下,南方非敌占区寄托着沦陷区青年学生的民族感情与爱国情怀。
四、结语
普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学科体系;研究范式;反思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探寻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发展的变迁过程,以及在变迁过程中所呈现的研究特点,进而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反思和重构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萌芽时期:职业教育理论的初步发展
这个历史时期可以限定于1840-1949年,这个历史时期既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萌芽时期,也是传统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由于我国当时特殊的国情与经济形势,职业教育实践形态主要是学徒制,同时也伴有部分的学校制。随着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其理论体系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显然,在这一历史时期,职业教育理论的体系发展与一大批具有实干精神的教育家是分不开的。他们对于实业救国、实业教育的倡导、论证、指导、实践,对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1902年,山西大学堂总督办姚文栋在“添聘普通教习文”中对职业教育的作用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论教育之形式,与国民关系最为密切者,乃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属教育之两端,缺一不可。”[1]这个表述应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职业教育的认知。随着职业教育的实践发展,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概念开始探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陆费逵先生,当时他担任《教育杂志》总编,在该杂志创刊词中,他发表了如下观点,即中国教育最需要改进的是国民教育、人才教育和职业教育,而其中最紧迫的乃是职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是教人谋生的教育形式,是教人拥有一技之长的教育形态”[2]。从这个表述可以看出,其对职业教育的内涵做出一个基本界定,这个界定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实践属性,即职业教育是技术技能教育。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学者开始注意到职业教育的理论问题,但在当时,教育研究的主流依然是普通教育,特别是在科举被废之后,对普通教育的形式、实践形态的讨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民族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既激发了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也从客观上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不少教育先驱对职业教育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工作,在蔡元培、黄炎培、晏阳初等人的引领下,创办了一批职业教育的学校,同时也开展了大量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涌现出一批学术成果,包括引进和翻译的国外职业教育著作和论文。如1916年出版的,由朱景宽编写的《职业教育通论》,是我国近代第一部职业教育的专著,后来,相继出现了朱元善翻译的《职业教育精义》(1917年)、顾树生的《外国职业教育学》(1917年)、潘文安的《职业教育ABC》(1927年)、陈表的《各国劳动教育概览》(1930年)、何清儒的《职业教育学》(1941年)等;除了这些著作以外,像陶行知、晏阳初等人还发表了多篇论述职业教育特性方面的论文。显然,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工作,既是对当时职业教育实践的总结,也对当时职业教育实践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还论证了职业教育实践与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何清儒的《职业教育学》,用今日之眼光看,依然是一部观点清晰、体系严密的学术著作[3]。整体观之,这一历史时期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职业教育的概念、性质、作用、地位以及与普通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些问题是职业教育理论的基本问题,因此,在总体上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尽管如此,这些先驱的探究对于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这个时期既可以称为传统职业教育理论时期,也是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萌芽时期。
二、依附时期: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探索
1.对普通教育理论的依附职业教育从一开始引入中国就未能取得独立地位,在理论研究上,也是从普通教育内部脱胎而形成的,可以说职业教育理论是借鉴普通教育理论而形成的。换言之,普通教育理论犹如“母体”,而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是由“母体”孕育的“子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深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在实践及理论研究方面也是完全照抄照搬苏联的,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的理论依附性表现得更为明显。直到1980年代中期,职业教育的研究者才开始意识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区别以及二者理论体系之间的差异,此时才开始尝试运用普通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对职业教育的内涵、概念、价值、形态、地位、规律等基本问题进行探究,逐渐建立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4]。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论文也较多,最有代表性的是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编著的《技术教育概论》、天津师范大学编著的《职业教育概论》等,较为系统地以普通教育理论为基准来阐释职业教育理论体系。
2.对国外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依附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后,国内学界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积累严重不足,以及职业教育实践刚从“”中恢复不久,因此这一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研究者开始将目光瞄准国外,希望通过翻译和引介国外的职业教育理论来完善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当时,关于国外的职业教育研究成果丰富,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形式丰富多样。既有翻译国外学者关于职业教育的著作,如1981年由河北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翻译的日本仓内史郎、宫地诚哉的《职业教育》,也有国内学者研究具体国家的职业教育相关论文,如王晓明发表在1985年第4期《比较教育研究》上的《谈谈联邦德国的职业教育》;陈希莲发表在1985年第10期《人民教育》上的《西班牙的劳动教育和职业训练》等。第二,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较为广泛。既有对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介绍的,也有涉及国外职业教育管理的,还有涉及国外职业教育政策方面的,更有涉及国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另外,部分学者探讨了国外职业教育的课程及教法。总之,这些研究涉及领域众多,理论性较强。第三,国外职业教育研究关注面较广。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对国外教育包括职业教育的借鉴和学习时,基本上离不开苏联及东欧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学者的视野开始从苏东转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特点等方面的研究成为国外职业教育研究的重点领域。如梁忠义、金含芬1990年共同主编的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七国职业技术教育》,就是对西方七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及特点做出详细介绍。在这个历史时期,研究者对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做了一定的探索,但整体研究还不够成熟,职业教育理论体系还没有独立性。特别是对国外职业教育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处于简单的翻译、介绍阶段,研究内容还没有与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相结合,研究的方法也较为单一,研究层次较为粗放[5]。纵观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总体上存在深度不够、研究对象简单及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大部分的研究者在对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总结过程中无法逃离国外职业教育理论和国外普通教育基本理论的束缚,研究的逻辑出发点与这两个领域也较为类似。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拨乱反正开始到1980年代末这短短十余年时间,至少开创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模块,逐步开始呈现职业教育的学科体系,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完善时期: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基本形成
1.职业教育系统的理论著作开始出现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探索和积累,在199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成形。在这个时期,系统的理论著作既是研究者的追求,也是体现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载体。因此,经过广大职业教育研究者的努力探索,不断关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对职业教育的理论进行升华,使得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呈现出一个动态化的发展过程。如1995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纪芝信主编的《职业技术教育学》以及1998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教委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编著的《职业技术教育原理》是这一时期两部代表性的著作,其中,《职业技术教育学》还被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客观而言,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并没有摆脱普通教育学理论的窠臼,但是已经摆脱了对普通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模仿,充满了对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理性总结和思考。即便是放在今天,这些成果依然是比较经典的论著,奠定了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在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2.职业教育本体研究开始出现本体问题既是任何一个学科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实践发展的需要。在此阶段,研究者开始关注职业教育的本体研究,主要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重新认识职业教育的基本概念与内涵属性。概念与内涵属性是任何学科的基础理论,很多学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对职业教育进行界定,重新审视职业教育的时代内涵及属性特征。第二,重新界定事业教育的本质问题。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态,其必然与其他的教育形态存在差异,这个差异就是其本质属性的体现。因此,很多学者开始研究“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的教育形态到底有何不同”“不同点又在何处”。总而言之,在这一历史时期,经过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的不断努力,基本上建构了一个较为完备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具体而言:首先,在研究思路上,研究者开始纠正过去一味地向国外学习的思路,对国外的经验开始有了理性的思考,既注重研究和解读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成就,也注重总结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其次,从研究的具体内容看,研究者从最初关注职业教育的概念、属性、内涵等局部开始转向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系统构建,全面总结了职业教育实践发展的理论过程,但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在当时还是不够深入,改革还是不够彻底。仔细分析,这些研究成果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职业教育的特色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比较欠缺,这实际上是涉及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问题,部分学者的研究还带有普通教育学理论的痕迹。显然,如果职业教育的特色把握不准,就无法系统彰显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特征[6]。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还较为单一,需要进一步拓展。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以学理分析为主,结合职业教育实践过程的实证研究不多,反思性研究也较为匮乏。不过站在当时的角度看,能够取得这些研究成果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建构的反思与转型
在过去的四十年时间里,我国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基本成型,在学科体系建设、梯队建设、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尽管如此,过度地强调学科中心体系的构建模式,使得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出现一些问题。具体而言:第一,过于注重学科中心的视角,使得职业教育理论研究陷入“营造”的困境中,这是导致当前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中很多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各种学术观点的分歧较大,影响了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7]。第二,过于重视理论问题的思辨和分析,忽视了对职业教育实际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由此使得部分研究成果与实践脱节,有些理论缺乏实践指导意义而被束之高阁。第三,职业教育研究的丛林法则凸显,学术研究背后呈现出“虚假的繁荣”,其背后无法掩盖观点的巨大分歧。第四,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对职业教育教学实践缺乏指导性,使得职业教育教学模式未能脱离普通教育模式的窠臼,职业教育实践发展也无法脱离普通教育的藩篱。最为典型的就是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学科化色彩过于浓厚,对教育内容的排序过于学科化,学科化具有较强的强制作用,使得部分课程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由此可见,职业教育长期以来是作为一个学科体系被建构起来的,这种学科体系的建构模式,使得其理论体系带有较强的抽象性。用一种系统化的研究方法对经验世界的内容进行挑选之后进行凝聚或提炼,并依据其内在逻辑结构构建新的命题。从理论层面来看,职业教育的研究者也必须改变过去的“学科中心”的研究范式,建立跨学科、多视角的职业教育研究框架,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可以解决传统研究方法和视野的不足。长期以来,学界身心学科体系构建是理论体系构建的唯一资源,职业教育学界同样也持如此观点。经过研究的深入及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结果发现,职业教育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而存在,其与一般的教育学理论有着不同的逻辑结构,即职业教育在发展中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密切关系,反映到学科体系中来就是要与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保持密切关系。因此,职业教育只能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如果执着于学科体系的建构方法,就会使得职业教育理论和体系陷入工具主义的困境中,也就无法解决职业教育实践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无法解决当前职业教育实践面临的新困境。有学者认为,以学科体系来审视职业教育,既无法为职业教育实践提供针对性指导,也无法解决当前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8]。
职业教育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将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来构建存在一定的局限,不再坚持以学科中心论为基调来构建职业教育理论体系,而是寻求构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多种资源与基础。由此,职业教育研究者开始反思传统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与方法,这种反思既是一种自我的反思,也是一种现实的反思。具体来看:第一,不再坚持教育学是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唯一理论来源,这实际上是看到了职业教育发展与其他学科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在教育学基础上增加了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用这些理论体系来为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提供养分。第二,从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体系看,其主体结构有较大幅度的调整,由原来的教育学结构体系转向以实际问题为基础的体系结构,更加强调理论体系研究与职业教育实践的融合。比如,从近年来获得的各类职业教育的纵向课题看,越来越多的课题开始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关注职业教育实践发展,并由此出现了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第三,从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研究思路看,对普通教育学和西方职业教育学理论的盲目接受开始转向批判反思,并提出中国职业教育理论本土化建构模式。学者开始探究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中国化命题,如概念、范畴与逻辑等。第四,从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研究方法看,传统的学科分析方法不断弱化,实证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方法日渐成为主流研究方法。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开始加入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中,推动职业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促进跨学科之间的对话,为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研究提供新的思维和视野。
目前,传统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面临较大的转型,从过去侧重于教育学意义上的建构转向在批判的前提下进行逻辑性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职业教育研究者提出新的研究观点。这些转型的观点值得关注:第一,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论”。将逻辑作为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前提条件,运用逻辑学的方法,从抽象到具体,在逻辑推导的前提下推进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第二,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问题系统论”。这种研究范式认为,职业教育研究必须以问题导向为基础,确立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构建学科体系的前提条件,围绕这些问题开展论证和实证,推动问题逻辑下次级问题的衍生,进而构建一个层次分明、体系严密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9]。第三,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范畴水平论”。此种研究范式认为,确立职业教育的学科范畴至关重要,它是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只有确定了其范畴体系,才能理论结合实践,按照逻辑推导进路,形成逻辑严密且理论性强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尽管上述研究在观点、立场、方法、逻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至少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即职业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而并非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看,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研究不能囿于“学科中心论”,必须跳出学科束缚,侧重于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建立跨学科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职业教育的基本概念、内涵、属性与逻辑,进而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经验、中国范式的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陈选善.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M].上海:中华职教社,1933:47.
[2]周明星,唐林伟.职业教育学科论初探[J].教育研究,2006(9):66-69.
[3]唐林伟.职业教育知识论初探[J].职教论坛,2010(16):4-9.
[4]张丹丹.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初探[J].继续教育研究,2014(11):131-132.
[5]潘瑞萍.论职业教育课程学问体系的解构和行动体系的重构[J].高等继续教育学报,2017(3):55-59.
[6]姜大源.学科体系的解构与行动体系的重构———职业教育课程内容序化的教育学解读[J].教育研究,2005(8):53-57.
[7]肖凤翔,唐锡海.我国职业教育学科自觉的思考[J].教育研究,2013(1):113-118.
[8]周明星,刘晓.我国职业教育学科建设:使命与方略[J].高等教育研究,2008(3):61-65.
普通论文范文第6篇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普通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声调是字音(音节)的要素之一。音节有声调是汉藏语系语言的特点,在汉语以及与汉语同系的语言中。声调在区别词的意义方面的重要性和声母、韵母相等。本文从古音声母清浊方面,就汉语的声调及其发展演变,对中古语音的声调、近代语音的声调以及现代语音的声调做了简单的思考与论述。
所谓声调,是指音节读音高低升降的变化。
汉语从何时起就有了声调的存在,现在还无法断言。通常认为,上古汉语也应该有声调的区别,但究竟有多少个调类,它们可能的调值如何,至今尚无定论。而中古时期的汉语语音的声调区别已经得到了共识,并且,当时的音韵学者已开始对这种区别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的研究。
一、中古语音的声调概述
汉代以前,人们还不知道有四声,直到齐梁间骈体文盛行,受佛教转读佛经声调的影响,逐渐觉察到自己的语言中也有声调存在,开始以“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字音进行归纳,随后定出“平、上、去、入”,通称为四声。《切韵》、《广韵》、《韵镜》及《七音略》等都是按照“四声”分韵的。
四声的名称起于南北朝齐梁时代(五世纪末六世纪初),据《南史•陆厥傅》说:齐永明年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x,琅?e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J善识声韵。约等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永明时期的这段叙述是平、上、去、入“四声”名称见于记载的较早的材料。此外,《梁书•沈约传》云:“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周?J传》记云:“?J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
“四声”只是归纳了中古时期语音的调类,至于各个声调具体的调值如何,古人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从古人的形象的描绘中感受到大致的概括:“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急而促。”我们由此可推测,中古时期四声中的平声是平调,入声是短促调。因为平声没有升降,较长,而其他三声或有升降或短促,所以“平声”与“上、去、入”三声形成了平与仄两大类型。
中古时期的“四声”,发展到现代汉语方言里,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则只有三个(宁夏银川话只有平、上、去三个声调),多则有十一个(广西南宁心圩平话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甲、阴去乙、阳去、阴入甲、阴入乙、阳入甲、阳入乙等十一个声调)。但是,不管声调多少,或是如何变化,都与古代“平、上、去、入”四个声调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平、上、去、入”四个声调由于受古声母清(全清、次清)浊(全浊、次浊)的影响而发生了分化。有的分,有的合。
二、由中古语音声调到近代音声调的演变
近代音的声调,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明确列出,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与现代北京话的四声完全一致,只是具体的归字有所不同。概括的说,近代语音声调突出的特点就是: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入派三声。
平分阴阳
《中原音韵》里,每一个韵部的平声都明确标出“平声阴”和“平声阳”。平声的分化以清浊为条件,中古清音声母的平声字分化为阴平,中古浊音声母的平声字分化为阳平。这一变化,使得中古平声清浊的对立转化为声调类别的对立。
浊上变去
中古的上声字在《中原音韵》中分化为上声和去声两大类。上声的分化也是以清浊为条件的,其规律是:原清音声母、次浊声母,上声字仍读上声,全浊声母上声字则变读为去声。
入派三声
到了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把古入声字归入阳平、上声、去声。汉语音韵学称之为“入派三声”。“入派三声”的规律性很强,由于声调的变化常常受声母清浊的影响而变化,古入声字的变化也受声母清浊的影响而“入派三声”:
清声母字变读上声,例字:笔、法、尺、塔;
全浊声母字变读阳平,例字:白、读、舌、绝;
次浊声母字变读去声,例字:纳、辣、灭、热。
有些学者如陆志韦、杨耐思、李新魁等先生认为元代仍然存在入声。《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说:“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者,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然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
三、现代汉语声调的发展
现代汉语声调,与近代汉语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入声字的分配有所不同。中古入声字,在现代汉语中大部分读去声,其次是阳平,再次是阴平,最少的是上声。次浊入声字的演变最有规律,现代汉语一律读去声,全浊入声的演变也比较有规律,一般读为阳平,清入声读为阴阳上去四声的都有,缺乏规律性。
以平声字来看,在现代汉语方言里,除极少数地区平声不分阴阳外(如银川地区),绝大多数地区古平声分为阴平和阳平两类:即古清声母平声字今为阴平,古浊声母平声字今为阳平。如:全清古声母“当”,次清古声母“康”,今读阴平。全浊古声母“堂”,次浊古声母“郎”,今读阳平。
以上声字来看,在现代汉语中,只有少数地区上声分阴阳(古清声母上声字为阴上,古浊声母上声字为阳上)。如:全清古声母“古”、“走”,次清古声母“口”、“丑”,在现代汉语广州话中读作阴上,全浊古声母“近”、“是”,次浊古声母“五”、“女”,在现代汉语温州话中读作阳上。
以去声字来看,古音浊上变去的现象,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去声不分阴阳,全浊声母上声字变读为去声。这种语音现象在北方方言区普遍存在。如:古声调中为全浊上声的“近”、“是”,在现代汉语中,北京、济南、兰州等地均读作去声。另一种情况为,去声分阴阳,全浊声母上声字变读为阳去。这种语音现象在南方的许多方言区普遍存在。如:古声调中的全浊上声字“近”、“是”,在现代汉语中,苏州、长沙、南昌等地都读作阳去。
以入声字来看,全浊声母入声字变阳平,次浊声母字入声变去声,《中原音韵》与现代普通话基本一致,但是《中原音韵》归到上声的清声母入声字到了现代普通话里,有的读阴平,有的读阳平,有的读上声,有的读去声。
除北方方言区外,其它方言区都保留古入声,但是各地保留的情况不一,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1、保留-p、-t、-k三种塞音韵尾:粤方言、客家话、闽方言的一些地方都比较完整保留-p、-t、-k三种塞音韵尾。2、收喉塞音韵尾:吴方言、闽方言的福州话、晋方言以及北方方言区的江淮官话保留喉塞音韵尾。3、塞音韵尾消失,古入声字自成一个调:湘方言、闽方言的一些地区以及北方方言区的部分地区古入声字塞音韵尾消失,但自成一调。例如北方方言区西南官话的西昌话,古入声字自成一调,古入声字“急、竹、曲、黑、各、尺、岳、合、白”等字都读31调。新晨
四、小结:
关于语音声调的发展变化,以上均是根据“古音声母的清浊”来展开讨论的,此外,影响声调变化的因素还有(1)声母是否送气、(2)韵母主要元音的长短等等。
(1)例如南昌话的阳平,今不送气纳“魔棉蒙麻泥南人来劳罗额牙”等为一类,今送气的纳“婆朋菩排掐从层除前求群”等为另一类;
(2)例如广州话的入声分为3类,其中阴入分为2类,阴入1读55,主要元音不是长元音;阴入2读33,不如阴入l短促,一般总是以长元音为主要元音。
声调在汉语语音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声调的地位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本文只在古音声母的清浊方面对声调的演变做了简单的讨论,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
【参考文献】
[1]唐作藩.音韵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2]刘纶鑫.音韵学基础教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2
普通论文范文第8篇
作者何勤华,1955年生,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法学”一词,是一个舶来品,它的故乡在古代罗马,是经过二千余年的发展、演变,才为西方各个国家所接受(1),并于近代传入中国。那么,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流变是什么样的?它反映了古代、近代中国人怎样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
在中国近代以前的辞书(如《康熙字典》)或现代出版的解释中国古典文献的辞书(如《甲骨金文字典》、《辞源》、《辞海》等)中,是没有“法学”一词的。据高名凯、王立达和实藤惠秀等中日学者的研究,“法学”一词是近代中国人在向日本学习过程中,从日本传入中国的(2)。然而,这个结论仅仅在下述意义上才正确,即现代含义的汉语“法学”一词是从日本传入的;“法学”一词早在中国古代即已出现。
在我国,“法”和“学”字出现得都很早,至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古语中,“法”字写作“灋”。在中国现存最古的文字甲骨文中,已出现了(鹿去“比”加“与”去“一”为灬)字,写作□(读zhi)(3),相传是一种善于审判案件的神兽。有的学者认为该字事实上就是我国法的缔造者蚩尤部落的图腾(4)。在西周金文中,便出现了“灋”字,写作□(克鼎)(5)。至战国时代,出现了灋的简体字“法”。然而,一直到秦代,灋字仍被频繁地使用(这从前几年考古发现的云梦秦简《语书》中可以得知),有时也与“法”字一起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6)。汉代以后,灋字逐渐消失,为“法”字所取代。
“学”字比“法”字出现得更早。在甲骨文中,便已有了“学”字,写作“□”。在金文中,“学”字有进一步的发展,写作“D”(7)。古代教、学通用,释义为:
一、教也,《静簋》:“静學(教)無□”;
二、學也,《静簋》:“小子□服□小臣□尸仆學射”;
三、學戊,神名(8)。至春秋战国时代,在孔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文献中,上述含义的“学”字已是频频出现,如《论语》一书的开篇是“学而”,《荀子》一书的开篇是“劝学”等。(文中□为甲骨文,详见图)
“法”和“学”连在一起,作为一个专门用语“法学”来使用,最早是在南北朝时代。《南齐书·孔稚珪传》中云:“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故释之、定国,声光汉台;元(帝)<常>、文惠,绩映魏阁。”(9)至唐代,在白居易的《策林四·论刑法之弊》中,有“伏惟陛下:悬法学为上科,则应之者必俊乂也;升法直为清列,则授之者必贤良也。”(10)然而,“法学”一词虽已出现,但极少使用,在表示对法律之学问时,人们一般都使用“律学”一词(孔稚珪和白居易在这里使用的“法学”一词,其含义仍接近于“律学”;与现代“法学”一词有重大区别)。
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在人民革命斗争的推动下,清政府被迫进行了法律改革,并开始打开国门,向西方以及东邻日本等国家学习,包括大量翻译他们的法律和法学书籍,现代意义上的“法学”一词也从日本传入中国,逐渐印入中国士大夫的意识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在司法官员和知识分子的论文,还是在法律学堂的课程、讲义,以及政府官员的奏章中,“法学”一词都已被广泛使用。比如,在梁启超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1896年)一文中,不仅突出强调了“法律之学”,而且明确提出了“法学”之用语:“……天下万世之治法学者,……”(11)。20世纪初叶,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时,也使用了“法学”和“法学家”等词(12)。而在沈家本的作品中,“法学”一词出现得更多。他的著名论文《法学盛衰说》(约写成于1908年前后),全文不过2000余字,但“法学”一词出现了20次(13)。在法律课程设置方面,在1905年3月开办的京师法律学堂之三年制本科和一年半制速成科,1906年7月设置的直隶法政学堂之二年制预科,都正式开设了“法学通论”的课程(14)。在一些政府官员的奏章中,“法学”一词也不断出现,如在《大清光绪实录》卷五八
三、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己酉(1907年12月26日)条中,我们就看到有如下文字:“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福铣奏:……请聘日本法学博士梅谦次郎,为民商法起草委员,下修订法律馆,寻奏。查欧洲法学系统,均分法、德、英三流。日本初尚法派,近尚德派,自当择善而从。……”(15)可见,尽管近代中国人对“法学”一词的理解还很不一样,但自19世纪末以后,“法学”一词开始大量出现则是事实。
二
由于近代意义上的“法学”一词及其观念是在近代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从日本输入的,所以,有必要考察“法学”一词在日本的出现和演变历程。
在日本古代,并没有“法学”一词(16)。神龟5年(728年),日本仿造中国隋唐官制,设置了律学博士。从此,在日本出现了“律学”一词和以此为业的职业身份。8世纪中叶,“律学”博士改称“明法”博士(17)。以后,“律学”、“明法”又常称为“明法道”、“明法科”,但“法学”一词始终未曾出现。
明治维新前后,随着日本国民革命意识的高涨,西方的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也开始传入日本。1868年,在福田孝平所著《日本国当今急务五条之事》(载1868年4月10日《中外新闻》)和津田真道编译的《泰西国法论》中,首次使用了“法学”一词。当然,前者只是提出了“法学”这一用语;而在后者的“凡例”中,则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法学,法语称之为jurisprudencc或Science
dudroit,英语称之为jurisprudence或scienceof
law或单称law,德语称之为Rechtswissenschaft(18)。汉土的语法与英语相似,故将此学的总名译为‘法学’。”(19)明治4年(1871年)以后,在日本政府的文件中,也开始广泛使用“法学”一词。而作为课程讲义的名称,则是由穗积陈重(1855-1926)于明治14年(1881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首次使用的,即Enzyklopadie
der
Rechtswissenschaft(即“法学通论”)(20)。至19世纪末,“法学”一词在日本已成为一个基础性概念,在一些法律论著,如高桥达郎编译的《英国法学捷径》(1883年)、河地金代译《法学通论》(1886年)、穗积陈重著《法律学的革命》(1889年)、冈村司著《法学通论》(1900年),以及各大学法学部的法学通论讲义中,“法学”一词都已被广泛使用。
根据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冈田朝太郎著《法学通论》的阐述,当时日本人对“法学”一词的理解,已是近代型的、西方型的,比如,作者认为:“法学者,乃国家的科学之一部分。国家的科学者,乃心的科学之一部分。”这话乍听起来颇为费解,但若看看冈田朝太郎所画的关于“法学”的位置图便可了然(21):(图略)
那么,在日本被创造出来,并开始被广泛使用的“法学”一词,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的呢?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翻译、引进西方法律。1863年,出版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翻译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International
Law)一书(22)。此后,北方的同文馆和南方的江南制造局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徐维则的《东西学书目》的统计,从1862年至1895年,译出的西方法律书籍有18种。不过,由于这些书的内容均为法典和国际公法,并未涉及“法学”之用语(23)。1904年修订法律馆成立,在沈家本的主持下,清王朝开始了又一轮更大规模的翻译外国法律文献的活动。至1907年5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同办理折》中对翻译活动作了一次统计,已译好的有法兰西刑法、法兰西印刷律、德意志刑法、德国民事诉讼法、普鲁士司法制度、俄罗斯刑法、荷兰刑法、意大利刑法、日本刑法、日本改正刑法、日本海军刑法、日本陆军刑法、日本刑法论、日本裁判构成法、日本裁判所编制立法论、日本监狱法、日本监狱访问录、监狱学、狱事谭、日本刑事诉讼法、日本新刑法草案、法典论、日本刑法义解,共26种。正在翻译的有:德意志民法、德意志旧民事诉讼法、比利时刑法、比利时刑法论、比利时监狱则、美国刑法、美国刑事诉讼法、瑞士刑法、芬兰刑法、刑法之私法观,共10种(24)。从这些书目可知,当时译自西方的主要是法典,涉及法律理论的则主要来自日本。
我们知道,日本学者在解释西方的法律术语时用的都是汉字。尽管这些汉字在日语中的结合和中文不一样,发音不同,并且有些词此时所表达的意思可能和它的原意也已大相径庭(25),但中国人一看就明白,稍一解释就能理解其内涵,故造成了当时中国人大量翻译、引进日本的法学著作,并且原封不动地照抄其汉字法律术语的局面(26)。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当时中国人通过翻译日本的法学著作,将日本的“法学”一词及其观念引入中国。笔者认为,这是“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第一个途径。
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唐宝锷等第一批留学生(共13人),此后,留日学生越来越多。至1905年前后,留日学生运动达到了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总数不下2万人(27)。他们感愤于清政府的腐败,满怀革命的激情,前往学习西方获得成功、并使自己强大起来的日本,探索救国救民的方略。在留日的学生中,学习法律的占很大的比重,20世纪初叶回国的留日学生中,在政治上最为活跃的大部分与法律(包括法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或在日本的大学法学部学习法律(如胡汉民、沈钧儒、章宗祥、曹汝霖以及等),或在那里阅读、研究法律(如梁启超、章太炎、杨度、吴玉章等),或在那里编辑法学杂志、出版法学书籍(如由中国人自己编译的中国近代第一本《法学通论(28)和第一本法律辞典《汉译法律经济辞典》(29)就是在日本出版发行的)。可见,中国近代留日学生的活动,是“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第二个途径。
以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设置法律学为始端,中国近代新型的大学普通高等法律教育正式起步。至1911年,北京和各地兴办的法律学堂已有近30所(30)。这些学堂,除了由中国人担任教师之外,还聘请了一批日本法学家为法学教师,如冈田朝太郎、志田甲太郎、松冈正义、小河滋太郎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897年至1909年,中国各法律学堂聘请的日本法学家共有57人次(31)。这些日本法学家率先在中国开设了“法学通论”的课程。因此,日文“法学”一词及其观念,通过日本教师的讲课活动传入中国,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明治维新后,中国政府加强了与日本官方的接触。而当时日本政府中比较活跃的人物,如外相榎本武扬(1836-1908)、井上毅(1844-1895)、广田弘毅(1878-1948),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西园寺公望(1849-1940)、原敬(1856-1921)、平沼骐一郎(1867-1952)等,几乎都是学法学出身或从事过法律工作的人。因此,尽管在这种接触交往中,不会对法学作一番理论阐述(32),但在互相介绍身份、中国官员赴日本实地进行考察等耳闻目染之下,无疑强化了日本法治社会和法学研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印象。关于此点,梁启超和董康(中国清末修律活动中的重要人物,民国初期的司法部长)等都有很好的论述。这是“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第四个途径(33)。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大体勾画出“法学”一词传入中国的途径(图略)。
四
通过对汉语“法学”一词之起源与流变过程的探究,使人们接触到了一些更为深层次的问题。笔者认为,至少下述四个问题应予以进一步探讨。
第一,古代中国人为什么使用“律学”而不使用“法学”?
如上所述,“法学”一词出现得并不晚,在魏晋南北朝时即已见诸文献,而且“法学”一词的出现和使用在时间上和“律学”几乎同时。然而,自唐以后,“法学”一词就极少出现,代之而起的是“律学”。虽然,就整个社会生活而言,律学也并不很受人重视,士大夫阶层对此始终持鄙视态度。但毕竟在魏以后的各个朝代,设置了律学博士之官职(元代以后开始废止),在律的制定和实施领域内,在各代律注释书中,“律学”一词也是频频出现。尤其是唐代以后,不仅在典籍、注释书中讨论律学问题,就是以“律学”为标题的作品也开始登台,如宋代的作品《律学武学敕式》(贾昌朝撰)(34)和明代的注释书《律学集义渊海》(作者逸名)(35)等。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笔者以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自公元前4世纪商鞅将李悝《法经》携入秦国,改法为律以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直至明清,历朝各大法典都是以“律”冠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使用“律学”一词而不使用“法学”一词应当是很正常的。法学以立法的发达为进化的基础,以成文法典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古代法律注释学时代,中国成文法典称为“律”的状况决定了对其注释、研究的学问形态也必然采用“律学”的名称。
其次,在中国古代社会,尽管“法”、“刑”、“律”可以互训,在实质意义上可以通用,如《说文》曰“法,刑也”。《尔雅·释诂》称:“刑,法也”,“律,法也”。因此,古代表示“法”的学问的三个词组:“法学”、“律学”和“刑名之学”之间,也是可以互相换用的。但是,从实际使用的情况看,“法”、“律”、“刑”这三个词之间还是有着微妙的差异。换言之,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对“法”、“律”、“刑”这三个词的认识和理解还是有所区别的。
按照《辞源》的解释,在古代文献中,“法”一般在八种意义上被使用:
一、法则、法度、规章;
二、刑法、法律;
三、标准、模式;
四、方式、作法;
五、效法、遵守;
六、数学上的乘数或除数;
七、佛教用语,泛指宇宙的本原、道理和法术;
八、姓。“律”主要用于:第一,乐器名;第二,法令;第三,爵命的等级;第四,梳理头发;第五,约束;第六,律诗;第七,戒律。而“刑”则表示:
一、处罚的总称;
二、割、杀;
三、法,典范;
四、效法;
五、成就;
六、治理;
七、铸造器物的模范;
八、盛羹的器皿。除此之外,在古代文献中,“法”字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用法,即第一,在中国古代,法(音废)、伐(音吠)音近,法借为伐,有“攻”、“击”之意,如《管子·心术》:“杀戮禁诛之谓法”即为一例(36)。第二,法借为废,表示“废除”、“不遵守”、“永不叙用”等,如《秦墓竹简·语书》:“……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泆)之民不止,是即法(废)主之明法殹(也),……(37)在《秦墓竹简》中,将法作为废来使用的共有十多处;同时,就“律”而言,晋以后,它事实上只表示刑法、刑事规范,用杜预在《律序》中所说的话来表达,就是:“律以正罪名”(38)。此外,在古代许多重要的场合,“律”表示的都是“军法”、“军律”,如《易经》称:“师出以律”,《史记》“律记”说“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似重。”(39)尽管如此,上述《辞源》对“法”、“律”“刑”的解释,与笔者接触到的古籍上对这三个词的说明基本上还是吻合的。据此分析,可以将“法”、“律”、“刑”以及“法学”、“律学”、“刑名之学”的关系图示(图略)。
由上可知,“法”、“律”、“刑”三个词,既有相同、彼此可以换用的地方,也有许多区别。特别是商鞅改法为律,决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字之改、名称之改,而是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第一,将“法”改为“律”,结果就使法的义务色彩更浓、刑罚的功能更加突出,从而更加适合不受法律约束的皇帝的专制集权统治。如果说,在春秋战国时,臣下还有要求君主守法的意识的话,那么,当法的义务观、惩罚观被突出、定型,皇帝不受法律约束之后,用“律”比之用“法”就更为符合最高统治阶级的利益了。而这一过程恰恰与秦汉建立中央专制集权国家(至唐宋而达到完备,至明清达到极端)、皇帝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的过程是一致的。第二,借用吴建璠先生的说法,由于“律”最初的含义是音乐,转变为“军律”后,强化了其强制性和镇压的力度。因此,改“法”为“律”,就是借用军事力量,突出其重要性和权威性,来保证法律的实施(40)。法的内容的这种演变,也影响到关于它的问题的名称“法学”、“律学”和“刑名之学”的使用上,于是就出现了隋唐以后只使用“律学”而“法学”和“刑法之学”几乎不被使用的局面(41)。
再次,秦亡后,秦代禁止私人学习、讲授和解释法律的局面被打破,律学研究开始勃兴,出现了许多以此为业,并世代相袭的家族,如西汉的杜周、杜延年父子(人们称其律为“大周律”、“小周律”)、东汉的叔孙宣、郭躬、马融、郑玄、吴雄,以及魏晋时期的杜预、张斐等,形成律注蜂起,著名注释者有“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的繁荣局面(42)。魏以后,我国又开始在中央设立律学博士。从此,律学博士成为国家的重要官职之一,从而使“律学”不仅成为一门约定俗成的学问、选官考试的科目、一个公认的研究领域,从事它的研究也是一种国家认可的职业、社会地位和谋生手段。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再使用“法学”这一用语了。
第二,古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和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的区别何在?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知道,古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是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之基础上产生的,而现代意义上的“法学”是西方商品经济和法治社会长期发展的成果,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两者所依据的世界观不同。中国古代之“法学”是建立在封建正统思想之基础上的,这种思想以强调社会等级、宗法制度、大一统国家和忠君孝悌等儒家学说为核心,以鼓吹君主专制,以法、术、势役使臣民的法家理论和主张君主无为无不为、君主南面之术的老庄学说为补充,重视德主刑辅、名分等级和臣民的义务,因而,它不是一种法学的世界观,而是一种律学的世界观,核心是将法视为役使臣民的工具,镇压人民的手段。而现代意义上的“法学”一词,是建立在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政治与法律学说之上的,它强调法的平等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将法视为制约统治权力、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的手段。
其次,两者的范围不同。古代汉语“法学”一词所包含的主要是法(律)注释学,而且基本上局限于刑法领域,当然,有时也涉及一些行政法学(事实上是如何役使官吏的“治吏之学”)和关于法律的起源与功能等问题的法哲学(事实上是“刑法哲学”)的内容,但这种法哲学仅是伦理学家和哲学家(如孔子、孟子等)或政治家(商鞅、韩非等)或官僚(如马融、张斐、杜预等)的法哲学。因此,它的范围相对比较狭小。而现代“法学”一词,不仅包含了法哲学(法学家的法哲学)、法律条文注释学,而且还包括法史学、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等诸多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即使是法律条文注释学,与古代的相比,范围也大为扩大,除刑法学之外,还有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和诉讼法学等,并且现代法学将这些法注释学都视为是一门科学,而不仅仅是条文和词句的注释。
再次,两者的重心不同。古代汉语“法学”一词所重视的是统治者的权力意识,强调臣民的义务、责任,注重从理论上阐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宗法等级秩序这种法律运行现实的合理性。而现代“法学”一词所体现的是民主的观念、平等的观念以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观念,它孜孜以求的是从理论上阐明法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中的作用和法如何才能成为保障公民权利的屏障。
第三,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学习西方、翻译西语“法学”一词时,日本学者为什么不使用他们比较熟悉、习惯的“律学”、“明法道”、“明法科”,而使用一个他们历史上所没有、对他们来说比较生疏的“法学”呢?
我们知道,即使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学者,其法学观大都还是以“法律应是以刑为核心”、“法等同于刑、律”的律学观。1875年,当铃木唯一翻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时,用的还是《律例精义》的书名;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制定刑法典时,还以中国刑律为蓝本,编纂了《假刑律》(1868年)、《新律纲领》(1870年)和《改定律例》(1874年)等。后来,这种情况在以下三种因素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化:第一,明治维新后,日本相继聘请了许多外国法学家(如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保阿索那特等)来日本立法、讲学,这些外国法学家不仅将西方的法、法学等名词,而且将西方的法学观也带了进来。第二,19世纪上半叶,随着“兰学”(研究以荷兰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的学问)的兴起,日本赴西方学习法律者也不断增加。当轮到明治时期著名法学家津田真道、西周、穗积陈重等人出国时,他们对西方的法和法学已有一定的了解,加上这些人在西方比较扎实、系统地学习了法学通论和各个部门法学知识,聆听了西方法学家的讲解,目睹了西方法治社会的运行现状,这种经历和环境使得他们比较深地理解了西语Law、Droit、Recht以及Legal
Science、Sciencedu
Droit和Rechtswissenschaft等词的真谛,他们感到再用“律”、“刑”等来对译Law、Droit、Recht等词,用“律学”、“明法道”等来对译Legal
Sciencesciencedu
Droit、Rechtswissenschaft等词是不确切的。第三,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整个民族向西方学习的心情都是非常迫切的,这从福泽谕吉(1835-1901)的一本介绍西方文化的书1866年一出版便销售了75万册一事便可得知(43)。当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法学家箕作麟祥(1846-1897)着手翻译《法国民法典》时,当时的司法大臣江藤新平(1834-1874)甚至指示:“即使翻错了也不要紧,只要快就行了。”(44)在这种氛围之下,日本各界的确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化包括法和法学的活动之中,箕作麟祥在翻译法国《六法全书》时,挖空心思、殚精竭虑,给一个个西语法律名词配上了对应的汉字,除“权利”(right)和“义务”(obligation)之外(前者在箕作麟祥之前已从荷兰语中译出(45),后者则来自汉译本《万国公法》),其他法律用语,几乎都是箕作麟祥呕心沥血推敲出来的。津田真道和穗积陈重也同样如此,不仅认真听讲,细心记笔记,而且不时向老师请教,以弄懂对东方人来说比较陌生的法律专业名词。从而用汉字“法学”一词比较确切地对应翻译了西语jurisprudence、science
dudroit、scienceof
law和Rechtswissenschaft等词。因此,津田真道、穗积陈重等人用“法学”而不用“律学”等词,是当时日本立法改革、法学观念进化的必然结果。
第四,由于数千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法学”一词仍抱有一种排斥心理。明明是“法学理论”,我们却一直称之为“国家与法的理论”,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50年代,虽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出版了以“法学”命名的杂志,但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法学研究所出版的法学研究刊物却称为“政法研究”(1978年复刊后始改为“法学研究”)。全国报刊索引的分类,在法学栏目,也不使用“法学”标题,而是用“法律”一词。至今,全国新华书店总店主办的《社科新书目》,在介绍法学著作栏目时,用的也是“法律类”一词。即使是专以复印、汇集各报刊法学文章为己任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法学》,直到1986年底为止,使用的仍是“法律”。甚至在目前,在司法部所属的五大法科大学,除中国政法大学拥有政治系外,其他如华东、西南、中南和西北四所大学均无政治系,但校名都是“某某政法学院(大学)”。
出现上述情况,虽然与我们受“左”的法学理论和继受苏联的模式有关,但是否与中国历史上轻视法学的传统意识有联系呢?仅此一点,就可以知道,在中国,虽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法学研究已经获得重大成就,但要真正树立法的权威并非易事,要发展和繁荣法学事业还需要我们作出长期持续的努力。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日本明治大学法制史教授冈野诚、明治史专家村上一博,以及北京大学法律史教授武树臣的热诚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1)参见何勤华《西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载《法学》1996年第3期。
(2)参阅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29页。
(3)方述鑫等编著《甲骨金文字典》,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718页。
(4)参见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129页。
(5)方述鑫等编著《甲骨金文字典》,第720页。
(6)参阅《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周礼·地官司徒第二》等。
(7)方述鑫等编著《甲骨金文字典》,第267页。
(8)同上书,第268页。
(9)(梁)肖子显编《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37页。
(10)《白居易集》(第四册),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57页。
(11)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93页。据笔者所见,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法学”一词的论著。当然,梁启超此处虽然用了“法学”一词,但其关于“法学”的观念还是中国传统型的。因为他认为这种法学“是研究规范人群同类不相互吞食的号令”的学问,而这种号令是“明君贤相”为百姓所立。为此,他对中国历史上法学的兴衰作了简单的回顾,强调在“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的同时,“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同上)。所以,梁启超这里所讲的“法学”一词的内涵与沈家本在《法学盛衰说》中对“法学”一词所阐述的相同,基本上接近于中国古代的“律学”。
(12)当然,在严译《法意》一书中,“法学”一词还出现得极少。在大多数场合,孟德斯鸠原文中使用的是“罗马法学家某某”,而严复都将其译为“罗马法家(有几处用了‘律家’)某某”。这说明在严复的观念中,“法学”的意识还不是很强的。
(13)见《沈寄簃先生遗书》(上),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版,第924-925页。
(14)汤能松、张蕴华、王清云、阎亚林编《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169页。
(15)岛田正郎著《清末近代法典的编纂》,创文社1980年版,第25页。
(16)笔者曾就此问题查阅了各种日本法律古籍,并特地请教了专治法制史的东京大学教授石井紫郎、明治大学教授冈野诚、国学院大学教授高盐博等先生,他们的一致答复是:在他们所看到的日本古籍中,没有发现“法学”一词。
(17)日本国史大辞典编集委员会编《国史大辞典》第14卷“律学博士”条(作者:久木幸男),吉川弘文馆1993年版。
(18)原文中是日语片假名,笔者据其读音将其恢复为上述法、英、德语。
(19)津田真道编译《泰西国法论》“凡例”,载《明治文化全集》第13卷,1929年初版。
(20)穗积陈重著《续法窗夜话》,岩波书店1936年版,第139-140页。
(21)冈田朝太郎著《法学通论》(汪庚年编《京师法律学堂讲义》,《法学汇编》第一册),宣统三年(1911年)北京顺天时报馆排印,第1、2页。
(22)该书作者是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惠顿(H.Wheaton,1775-1848)。
(23)参见李贵连《中国法律近代化简论》,载《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3期。笔者事后请教过李先生,他说这些书他都看到过,但未见到“法学”之用语。他认为,“法学”一词是从近代日本传入的,但其具体过程尚待研究。
(2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8页。
(25)如中国古代的“法律”一词是单音节合成词,它分别表示“法”和“律”这两个含义,而日文中的“法律”一词不仅与中文发音不同,而且它只表示一个含义,以对应于英语的Law,法语的Droit,德语的Recht等词。
(26)不仅“法学”是这样,其他术语也一样,如日本人用“哲学”来对译philosophy(国人原译“智学”),“经济学”对译economics(国人原译“资生学”、“计学”、“平准学”),“社会学”对译sociology(国人原译“群学”)。这此词(哲学、经常学、社会学等)在中文中原本都是没有的,但由于是用汉字组合,国人一看就明白,只要改变读音,便可以立刻当作中文来使用,所以,最后都接受了这些术语。
(27)施宣圆:《东瀛求索》,载1996年5月29日《文汇报》“学林版”。但李喜所著《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一书中则认为该时期留日学生总数有39056人(见前揭汤能松等编《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第208页)。
(28)该书由留学在日本法政大学的湖北法政编辑社社员编译,光绪31年(1905年)由设在东京神田区的中国书林发售。编译者在前言中宣称:“法律之学,吾国尚未发达。”“敝社同人,留学法政大学。该大学各讲师皆法学泰斗,其学说丰富,足以风靡一世。同人毕业后,深慨祖国前途,欲一表贡献之忱,用就所闻于讲师之讲义,并参考本讲师及诸名家之著述,悉心结构,以成此编。”“编译专门法律之书,以定名词为最难,本书所用诸名词,多取之日本,并注西文于其下,以备参考”(原文无标点)。
(29)该辞典由日本法学博士清水澄编写,留学东京大学的张春涛、郭开文翻译,陈介校阅,并由东京神田区的奎文馆于1907年发行。参见前揭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99页。
(30)见前汤能松等编《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第154-157页。
(31)同上书,第190页。
(32)明治政府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此时的“兴奋点”都在于如何扩张日本的势力,吞并朝鲜和中国。
(33)当然,由于近代最早将西方的“法学”及其观念介绍进中国的学者,如梁启超、严复、沈家本等,本身都是熟读中国古籍的人,所以,考证其使用的“法学”一词是采自日本的汉字,还是中国的古籍已相当困难,然而,现代汉语“法学”一词所表达的现代西方观念,通过日本传入中国则是无可怀疑的。
(34)见《宋史·艺文志》“刑法类”。《宋史》有贾昌朝传,但传中没有提及此书。
(35)孙祖基著《中国历代法家著述考》(1934年上海刊)和张伟仁主编《中国法制史书目》(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76年发行)均未记载此书,笔者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图书室看到过此书的藏本。
(36)蔡枢衡著《中国刑法史》序,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3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写《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
(38)见沈家本著,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1页。
(39)吴建璠:《唐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外法律史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212。
(40)参见《中外法律史新探》,第212页。新晨
(41)关于“刑名之学”,还需多说几句。该学原是战国时期名辩思潮的产物,研究的重点是推敲“法令之所谓”(法律之名实),强调对刑(形)、名的逻辑分析、演绎,核心在于“定分止争”(商鞅语)、“名法正义”(申不害语)、“循名责实”(韩非语),为战国时期封建地主阶级从奴隶主阶级手中夺得的统治地位寻找合法的根据。因此,随着法家学派的衰落和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成为历史,“刑名之学”也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
(42)《晋书·刑法志》。
(43)参见张灏《晚清思想发展试论》,载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