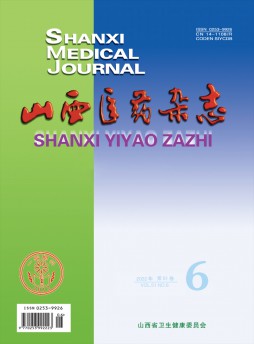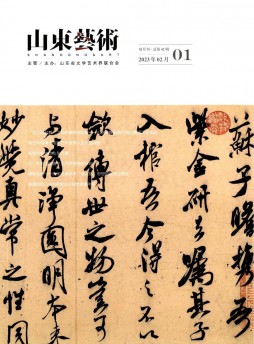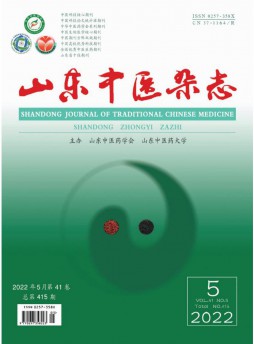善意取得制度范文

善意取得制度范文第1篇
所谓善意取得,是指无处分权的动产占有人让与动产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若受让人占有时出于善意,则依法即时取得动产之所有权或其他物权,故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
早在罗马法,就奉行“无论何人不能以大于自己所有的权让与他人”,“发现已物,我必收回”的原则,侧重对所有权的保护,受让人即使是善意且无过失,原所有人也得对其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但应予注意的是,罗马法并非完全无视受让人的利益,而是规定善意受让人需主张时效取得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并非罗马法。通说认为,大陆法系的善意取得制度源于日耳曼法“以手护手”制度。该制度认为“任意将自己的动产交付于他人者,仅能向其相对人请求返还,若该相对人将动产让与第三人时,原动产所有人仅可对相对人请求损害赔偿,而不得向受让人请求返还。”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就是以此为基础,并吸纳了罗马法上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得以产生起来的。
二、善意取得的价值取向
善意取得的实践根据为交易安全,或称动的安全。民法上素有“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的区分,所谓“静的安全”是对原权利人现存的既得利益加以保护,使其免受他人的不法侵害,力图保持秩序的和平稳定。“动的安全”则旨在保护善意的无过失的交易者取得利益的行为,以圆滑财产的流通,从而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秩序。若从保护静的安全出发,所有权将得到绝对的保护。所有权人得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而受让人只能依靠相应去寻求救济。这在罗马法时期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再绝对贯彻所有权的绝对原则,显然存在:1、任何善意的交易者,在依据法律和市场规则的规定做出交易后取得了标的物,却随时有可能并未取得所有权,甚至人财两空,这必然使人们失去对法律的信任,甚至对交易敬而远之。2、动产是以占有为公示手段的,占有其物便具有公信力,若对让与者的信赖未得到保护,则每个人进行交易时都要调查让与人是否为无权处分人,交易无法顺利进行。3、原权利人既然可以将原所有物转让于让与人占有,说明其对让与人的信赖,原所有人与之的关系显然较一个善意的交易者来得紧密。“让善意受让人对他无法控制的风险承担责任,而使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受可由其控制的风险的,无疑有悖于我们所信守的公平观念,更何况原权利人的控制成本常常低于善意受让人的调查成本”。经过利益权衡,显然交易安全应受到静的安全更大的保障。而善意取得恰恰是均衡这种侧重高效率与动态安全的保护,且兼顾静态安全的取向的有效法律元件。
三、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一)受让人必须是善意取得动产
所谓受让人的善意亦即第三人的善意。如何判断受让人的善意,上有两种判断标准的学说,一种称之为“消极观念说”,认为受让人的善意,就是第三人在取得该动产之时,根据客观情况和第三人的交易经验等考察,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出让人无权处分该财产。第三人的善意以接受出让人交付时为已足,至于受领财产后是否知道出让人的无权处分,并不影响他对财产善意取得所有权。这一观点为我国立法及多数学者所主张。另一种称之为“积极观念说”,认为受让人必须具有将他人(出让人)视为所有人的观念。相比较而言,消极观念说对受让人善意的判断比积极观念说要简便易行得多,因为前者具有客观性,容易把握;而若以后者为依据,则势必要对人之主观心理加以考察,显然较为困难。因此,采取“消极观念说”作为判断受让人善意的标准较为。
(二)受让人须通过交易性质的法律行为有偿取得财产
善意取是制度旨有实现交易安全,因而,受让人只有通过交易行为,始得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受让人取得财产是否必须有偿?西方国家民法多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学者对此意见不一。我认为,善意取得的适用应以受让人有偿取得财产为前提。理由在于;在许多情况下,无偿转让财产,本身就表明财产的来源可能是不正当的,而一个诚实的不贪图便宜的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应当查明财产的来源,如果不经调查即无偿受让财产,很难认其为善意;其次,由于财产是无偿接受的,受让人占有财产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因而返还财产并不会给其造成大的损失,尤其是当该财产在市场上有替代品时。唯有有效的法律行为方能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受到法律保护,根据善意取得理论,善意第三人善意取得财产的占有仅能补正让与人权源方面的瑕疵,不能补正行为其他方面的瑕疵,倘若交易行为因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等因素而发生,或行为人缺乏相应的行为能力,则受让人负有返还标的物之义务,善意取得无从适用。
(三)标的物为动产
善意取得的标的物,以动产为限。因为唯有动产才适用占有和根据占有对之作权利归属。民法物权保护制度的基础是公示公信原则。按照物权法的一般原则,物权变动应当遵守公示原则。所谓公示,是指当事人必须将物权变动的事实向社会公开,否则不能产生法律效力。直接保护变动物权的当事人和间接保护处于交易过程之外的第三人,可谓是公示原则的功能所在。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是占有,而不动产以登记为物权的公示方式。物权的存在既然以占有或登记为其表证,对于信赖此表证而同占人,登记人进行交易,纵使其表证与实质的权利不符,法律仍承认具有和真实物权相同的法律效果,此乃物权公信原则。物权公信原则以保护交易的动态安全为其使命,基于动产占有的公信力,善意受让人善意取得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自无疑义。不动产物权因为以登记为权属标志,交易中不至误认为占有人为所有人,故不发生善意取得问题。
(四)受让人须已实际占有受让财产
善意取得制度是从占有公信力出发保障交易安全的法律制度。占有是第三人取得权利的基础。纵然受让人与出让人已经订立了让与财产的契约,但受让人在尚未实际取得财产的占有之前,仅仅享有请求让与人交付财产的债权。原权利人对此项财产的所有权依然存在,在同一物上既存一个物权,又设定了一个债权,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民法原理,法律应优先保护原权利人。当原权利人向仍然占有财产的让与人请求返还原物时,无权让与人与善意受让人均不得以善意取得予以抗辩,善意受让人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只能向让与人主张赔偿请求权。在法制下,交付不仅包括现实交付,而且也包括观念交付。观念交付又有简易交付,指示交付和占有改定三种。在现实交付和简易交付情形下,受让人已实际占有动产,因此各国立法和学说一般都认为受让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财产权利。在以指示交付作为财产交付方式的场合下,让与人将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让与给受让人时,受让人便可取得财产权利。所谓占有改定,是让与动产物权时,让与人仍将继续占有动产,让与人与受让人得订立契约,受让人因此取得间接占有,以代替现实交付。占有改定是担保让与制度的法律基础。依占有改定方式交付财产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各国立法差异较大,德国民法对此持否定态度,而瑞士民法和我国地区的“民法典”则认为依占有改定而交付时亦可取得财产所有权。我认为占有改定不发生善意取得效力。理由在于:首先,善意取得制度是基于占有的公信力来维护交易安全的信赖基础。这种占有必须是直接的,易于识别判断的,而非观念上的,难以识别判断的占有。在占有改定情形下,善意受让人未取得物之直接占有,仅取得间接占有,难谓具有占有公信力;其次,善意取得制度的确立反映了物权制度从重“所有”到重“利用”的发展轨迹。物尽其用,财尽其效是善意取得制度的价值目标之一。而在占有改定场合下,这一价值目标自然无从实现;最后,依占有改定为交付方式的情形下,还会出现重复转让的情况,并据此而产生一物两权的混乱现象,何者权利优先实现,难以抉择。
四、关于善意取得的效力
善意取得制度起源于日耳曼法中的“以手护手”原则。根据此原则,所有人将自己之财产让与他人占有的,只得向占有人请求返还原物,如占有人将财产转让给第三人时,所有人不得请求第三人返还,而只能要求占有人(转让人)赔偿损失。立法者缘何设立善意取得制度?法律如何在所有权与交易间作出选择。对此善意取得的存在基础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各种学说莫衷一是。主要有这几种观点:(1)即时时效说。此说认为善意取得之所以能使善意受让动产之人从此前对动产之无权利状态变为取得动产权利,完全是“即时时效或瞬间时效作用”之结果。法国、意大利学者多采此说。(2)权利外像说。该理论认为依物权公示主义,凡占有动产的人即应推定为该动产所有人。(3)权利赋权说。认为是法律赋予占有人以处分他人所有权之权能,因而善意受让人取得权利。(4)占有效力说。认为善意取得系基于占有之效力而发生。(5)法律特别规定说。认为善意取得为一种由法律直接规定的特别制度。上述学说尽管角度不一,但其基本立场均是为了维护交易。
善意取得的实践根据为交易安全。在民法理论发展的历史中,有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两种安全。前者旨在保护原所有人之权利,有谓所有权绝对之说,后者则旨在保护善意的无过失的交易者取得利益的行为。两种安全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冲突,这一点尤为体现在无权处分财产中。然而法律只能偏向于保护一种安全,这就要求权衡利益得失,以确定法律所保护的对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顾虑到财产权之圆滑流通,在某种场合下,亦得牺牲真正权利人之利益(交易上静的安全),以保护善意无过失交易者之利益。”同时,由善意第三人对占有之动产充分发挥其效能,总之原所有人“平稳”地拥有动产,更有利于发挥物的使用价值,从而增加了社会总体财富。况且原所有人]之所以将动产转移占有,乃是基于对无处分权人的信任,对其无权处分行为,应负一定过失与风险责任,故“让善意受让人对他无法控制的风险承担责任,更何况原权利人的控制成本常常低于善意受让人的调查成本。”承认善意取得制度并非彻底否定原所有人的权益,原所有人的损失可通过向无权处分人主张赔偿请求权而得到补救。当然,善意取得制度的建立也要结合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考虑到静的安全,故此一般要对其构成要件予以严格限定,如无权处分人须占有动产,第三人方可基于占有公信力而“善意”地与其进行交易。因此,善意取得制度必须权衡两种安全的利益,经过利益权衡,显然交易安全应受到较静的安全更大的保障。但最公平、最正义的善意取得制度应该是均衡这种“侧重效率与动态安全的保护,且兼顾静态安全”价值取得的有效法律元件。
善意取得一旦成立,即在三方面产生法律效力:
(一)善意取得对受让人
善意取得制度对善意受让人的效力体现为善意受让人即时取得受让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这是善意取得最基本的效力。由于善意取得不是基于让与人的让与行为而取得权利,而是基于物权之直接产生,因此,善意取得之性质为原始取得。原有权利上的各种限制,原则上归于消灭,善意受让人取得完的所有权。其他人在该物上没定的权利,如添附等,也就不复存在。善意取得为原始取得,具有终局性,确切性,因而即使善意受让人将取得的动产再出让给恶意受让人,所作处分系有权处分,恶意受让人仍可取得财所有权。但是,倘若无权处分人又通过交易行为从善意受让人处取得财产,那么让与人能否主张财产所有的取得呢?此乃民法上的回首取得。我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是在原权利人与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为维护交易安全而做出保护善意受让人的利益的选择,让与人非交易安全保护之对象,不受这一制度的保护。因此,受让人将财产所有权返还于让与人时,原所有权人便回复动产所有权,同时该财产上的其权利也随之复活。
(二)、善意取得对原权利人
就原权利人而言,其在该财产上的一切权利归于消灭。不仅原权利人丧失了基于所有权或其它物权而产生的物上请求权和债上请求权,即便是其他人设定在该物上的他物权,也一并归于消灭,只能依侵权行为而要求不法转让人赔偿损失。
(三)、善意取得对不法转让人
作为不法转让人,他因侵害了原权利人之所有权或其它权利,其转移该财产所获之利益既无法律上之根据亦无合同作基础,实属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因此遭受损失者。如要其返还之不当得利仍不足以弥补原权利人之损失,则应由不法转让人负损害赔偿的责任。如果不法转让人以高于市场价格或财产实际价值的价格出让,与财产价值相当的利得毫无疑问应当返还,至于高于财产价值的那部分利得应否返还,其法理依据何在?有的学者认为高出的部分应一并返还给原权利人。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视为原权利人对无权处分人处分其财产的追认。我同意高出的部分应一并返还给原权利人的意见,但对于法理解释有不同看法,认为在此情形下准用关于无权追认的是不恰当的。因为无权的追认,应当有“被人”的追认之意思表示或有相当的情节足以推定“被人”的追认之意思表示,在此基础上方可认定。而对于善意取得法律关系中的原权利人来说,自始至终不法转让人的转让行为都是违背原权利人意思的,且原权利人从未表示过接受,也没有任何事实足以推定其为接受或追认,原权利人向不法转让人主张权利并在以后接受不法转让人的返还或赔偿或其它给付,完全是基于所有权而生之物上请求权,决非什么追认。因此我认为,原权利人有权要求取得高出其财产原有价值之利得,实为原所有人因对被转让财产享有收益权的结果,高出部分的所得可以视为原物的孳息,应与原物一并归所有人所有。当然,在这个返还过程中也要适当考虑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不法转让人在非法处分财产之前,曾以自己的劳动改变了原物的价值状况,提高了原物的价值,改进了其功能等。于此情形,我认为,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不法转让人的劳动,在要求其返还财产时,由原权利人与之协商确定财产的增值额,并就增值的部分约定一个恰当的分享比例。同样,善意第三人如果为照顾财产支付了必要的费用,那么在他返还原物时,便可依无因管理之责而向原权利人要求补偿;如果他为物的增值付出了劳动,也应分得相应比例的效益。有人认为,如果无权处分人无偿处分财产则应由其负全部赔偿责任。这种情况,我认为,在善意取得制度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这根本就不符合取得的法定要件,所以根本不在善意取得制度中讨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原权利人不仅有权要求不法转让人负全部责任,还完全可以依据物权之追及权,向没有支付对价而取得财产的第三人追回自己的财产。如果财产遭到毁损,则应由非法转让人与第三人负连带赔偿责任。
各国民法仍普遍地承认取得时效在维护交易安全、稳定秩序、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物尽其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详细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1、保护交易安全,稳定经济秩序
郑玉波先生曾将法的安全分为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前者着眼于利益的享有,所以也称为“享有的安全”或“所有的安全”,此种安全主要由物权法保障,后者主要着眼于利益的取得,所以也称为“交易安全”,合同法为主要维护交易安全的法律。 为什么说作为主要调整财产的占有关系,保障静态安全的物权法, 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制度的取得时效的功能是保护交易安全呢?其理由在于无权利人以所有的意思公然、和平、继续地占有他人的所有物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人们常信其与真实的权利关系相符,从而在该物上建立各种法律关系,否定取得时效制度势必造成社会经济与法律秩序的混乱,违背法律旨在维持人类共同生活的和平秩序这一目的。总而言之,取得时效制度就是通过保护静的安全达到维护动的安全目的的,即通过对占有人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承认从而达到维护与占有人发生交易或其他关系的第三人的利益,以达到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
另一方面,现代民法价值取向相比于近代民法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追求“安定性”到追求“妥当性”,由“形式主义”到“实质主义” 。在现代,传统民法的三大原则受到修正,消极国家向积极国家转变,民法本位也逐步呈现出了社会化倾向。现代民法上的取得时效制度就隐含传统民法所欠缺妥当性的国家干涉主义的价值观。在保护财产原始所有人利益与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上,取得时效制度选择了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也正是由于它选择了社会整体利益,稳定了社会经济秩序,所以,各国民法典无不加以采纳,即便在极力张扬“所有权神圣主义”的近代民法。
2、节约交易成本,减少资源浪费,促进物尽其用
按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明确界定的产权能保护人们投资和创业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模糊的产权制度是增加交易成本最基本的原因。取得时效制度通过赋予自主、和平、公然达一定期间的“占有人”以财产的所有权,从而消除原所有权与事实占有权相分离的状况,解决了模糊产权的问题。在很大意义上节约了当事人的交易成本,客观上也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并诱使闲置资源得以重新配置与利用。而这一功能也正好符合科斯所主张的“权利应该让于那些最能够最具有生产性使用并激励他们这样使用的动力的人。而且要发现和维护这种权利分配,就应该通过法律的清楚规定,通过使权利让渡的法律要求不太繁重,而让权利让渡成本比较低。”
另一方面,取得时效制度也能减少资源浪费,促进物尽其用。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过程中,始终都存在着一个无限人类需求与有限环境资源供应的矛盾。因而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的法律制度,其设计者在设计法律制度时都不可避免需要围绕解决这一矛盾进行,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就在于确立一个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内促使人们充分利用资源,尽量地减少浪费。取得时效制度通过赋予占有人以某种权利,从反面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该权利,从而有效地避免了资源的浪费,达到了促进物尽其用的目的。
五、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状况
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是否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对此,学者认识不一。我认为,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尚未确立善意取得制度,但若干的民事特别法,如我国《拍卖法》第58条及《票据法》第12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都设有或可推导出善意取得制度的相关规定。尽管我国司法实践承认一定情形下善意第三人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财产的所有权,但真正意义的善意取得制度则没有在我国民事基本法中得以明文规定,有鉴于此,我国应参照国外的立法体例,尽早确立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
下面我就我国善意取得立法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善意取得制度立法的指导思想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谋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应当更加注意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和谐;我国又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长期以来的文化积淀,造就了我国优良的传统道德规范。要建立有我国特色的善意取得制度,就应当既立足本国国情又借鉴世界先进立法思想和立法经验。具体而言,就是一面吸收世界各发达国家在善意取得立法上的成功经验,汲取有益的教训,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照顾的国情,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已被人民群众所广泛接受的优良道德习惯,不得违背中华民族的善良风俗。
(二)关于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体例
总观大陆法系国家善意取得制度立法,就体例上来看,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德国民法为代表,将善意取得纳入所有权取得范畴加以规定,另一种是以日本民法为代表,把善意取得规定在“占有”一章内,我国省国民党发源地则效仿瑞士民法,把善意取得规定在“所有权”一节,却指示依关于占有保护的规定取得所有权。根据上文对善意取得性质的,我以为,日本民法典的做法较为,故我国如要规定善意取得,宜将其列入整个物权法的立法规划中,作为物权法的中有章中的一节,作为占有制度中的一个小制度加以规定。
(三)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具体
其应包括:1、善意取得通则,主要说明善意取得的定义与构成要件;2、不适用善意取得的各种动产概括与例示,主要说明哪些动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3、盗赃物与遗失物的特则,分别盗赃物与遗失物的不同情况,明确盗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以及遗失物适用善意取得的条件;4、关于有价证券的善意取得的特殊规定,专门对不记名支票,本票,汇票以及其它有价证券和货币的善意取得作规定。这一部分内容也可放在票据法,证券法或其它民事特别法中规定,作为特别法上的善意取得。 资料:
《中国法制史》 马志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7月
《中国物权法原理》 孙宪忠 高级法学教程 2004年5月
《法导论》 孙笑侠
高等出版社
2004年8月
《中国物权法的理论探索》
孟勤国
社科文献
善意取得制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撤销权善意取得无权处分
引言
甲对乙负有10万元货款债务,已经超过履行期限半年没有清偿。当乙请求甲清偿时,甲称自己除了一件祖传玉器之外没有任何财产可用以偿债。当乙请求甲变卖其祖传玉器清偿债务时,甲称其祖传玉器已于前一天为帮朋友从银行贷款10万元已与丙银行签订了质押合同,并已将其交付给了该丙银行占有。于是,乙向法院提讼,以甲和丙银行为被告,请求撤销两被告之间签订的质押合同。一审法院认为乙的请求不符合我国《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因而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和民法学理论的通说,合同保全中的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如下:一、须有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二、该行为须于债权发生后有效成立且继续存在;三、须该行为有害于债权;四、在无偿行为场合,不要求受益人有损害债权的故意;在有偿行为场合,还须受益人有损害债权的故意,即其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行为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至于是否要求债务人有损害债权的主观故意,合同法未明确规定,虽理论上有学者认为应作与大陆法相同的解释①,即撤销权的成立须有债务人损害债权的故意,但笔者认为此说不妥:一则民法的原理不同于刑法,其“故意”要件的设立主要不是为了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而是为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因此不应再为受害人规定过多的举证责任;二则即便要求主观故意要件,也是采取法律推定的举证规则,即如果债务人明知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而仍然处分财产时,即可推定其具有恶意②。这一点与刑法的举证规则存在着质的区别;而在债务人举证证明自己没有损害债权的故意时,无非也是从证明自己仍有履行原债务的能力的角度来展开,这一点又完全和上述“须该行为有害于债权”这一构成要件相重复。因此笔者认为撤销权的行使无须要求债务人有损害债权的主观故意。
通过对相关撤销权适用条件的分析可知,不论银行对甲欠乙10万元到期债务这一事实知情与否,甲为银行设定质权的行为完全符合撤销权的法定构成要件,债权人乙完全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甲与银行之间的质押合同。然而,问题在于,如果跳出撤销权的固有模式来看,那么,如果银行是善意的,即其不知道甲的该质押行为在客观上构成了对乙的债权的侵害,在银行与甲之间的质押合同被撤销以后,银行的利益是否也应当得到保护?其是否构成质权的善意取得?如果本案中的质物未实际交付银行占有,则上述情况下银行的利益又将如何进行保护?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
质押合同被撤销后,基于善意的银行能否构成质权善意取得
问题的实质在于,当处分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因无权处分以外的原因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时,善意第三人是否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物权(本案中是取得质权)?
问题的关键有两个。其一,当处分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因无权处分以外的原因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时,处分人之前向第三人出质的行为是否构成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所要求的“无权处分”?应该说,虽然民法理论和民事立法一般认可合同的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这并不能当然得出处分人作为出质物的所有权人无权将该质物出质的结论。那么,在不符合“无权处分”的前提构成要件的情况下,作为善意第三人的银行是否就绝对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该质权呢?笔者以为,可以从其立法宗旨着手进行分析。善意取得制度的承认,表明法律在总体上采取了牺牲财产所有权的安全而保护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的立场。③从而,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前提不在于教条地论证是否存在无权处分,其之所以得到适用,根本目的是在于平衡财产静的安全与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之间的价值衡量。可见,只要存在善意第三人与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冲突,就应该有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可能。
其二,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是不是要求处分人与善意受让人之间的转让合同有效呢?对此,民法理论有较为充分的论证。史尚宽先生采肯定说,认为善意受让人在转让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时不能取得转让物所有权。他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在原因行为不存在的当事人之间不能适用,而只能适用于与原因行为无关的第三人。④王泽鉴先生则认为应将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意图彻底贯彻,善意受让人在转让合同存在无权处分以外的瑕疵时仍能取得受让物的所有权;⑤其转让合同不存在,只能说明取得此所有权构成不当得利,属于善意取得之后的效力问题,与善意取得制度的意旨并无违背。
质物未交付银行占有,银行是否构成质权的善意取得
法律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使善意第三人直接取得所有权,还是在于补正无权处分人的处分权?
依前一种理论,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直接结果是补正无权处分人的处分权瑕疵并使善意相对人直接取得所有权;至于善意第三人和相对人(无权处分人)之间合同关系的其他瑕疵,则并不影响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效力。善意取得制度的直接着眼点在“取得”,即其目的是为了对善意相对人进行直接和最终的保护,保护的手段就是使其直接取得物之所有权;第三人的“善意”只是作为其能够最终取得所有权的条件之一。在无权处分权人的处分权瑕疵得以补正之后,该善意第三人即可直接取得所有权。如果该善意第三人和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合同还存在不成立、无效、被撤销等其他瑕疵,由于善意第三人取得所有权在先,该合同瑕疵也只能通过不当得利请求权来予以补救。
依后一种理论,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直接结果并不是使善意相对人直接取得所有权,而是补正无权处分人的处分权,使善意第三人不致因其相对人无处分权而失去法律上的保护;至于善意第三人和相对人(无权处分人)之间合同关系的其他瑕疵,则并不在善意取得制度的调整范围之内。因此,该说认为在无权处分人和善意第三人间的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解除后,善意第三人并不能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所有权,从而物的原权利人仍可以行使其所有权的追及效力,而不是只能行使不当得利请求权。
结论
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对善意取得制度作出不同的规定和解释,完全是出于到底保护本权利人还是善意第三人的宗旨:
如果善意取得制度可以使善意第三人直接取得所有权,则法律保护的天平将倾向于善意第三人,对于本人来说,不能行使物上请求权,而只能向无权处分人行使侵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但考虑到本人向无权处分人交付占有本身即包含了承担其可能作出无权处分的风险,应当认为本人在这个问题的可保护利益要小于善意第三人,因为善意第三人是纯粹无过错的,而且他还代表了交易的安全性和社会的可信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直接取得所有权的善意取得制度设计模式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再来分析补正无权处分人的处分权的善意取得立法模式。合同当事人可以依据有效的债权合同向对方当事人请求交付标的物,若对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则应负违约责任。这样,在依据善意取得制度补正了无权处分人的处分权后(这时的“处分”,不是物权行为,而是债权行为),如果买卖合同也无其他瑕疵,则买卖合同有效成立,在善意第三人已取得标的物占有的情况下,其依法基于有效的合同即时取得所有权;如果需要办理物权的移转登记,则他尚未取得所有权,其占有是基于债权的占有,仍然不能对抗本权利人所有权的追及力。这样,第三人可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善意取得制度的设计模式是在严格区分法律行为的物权效力与债权效力的理论前提下对交易中的善意第三人和本人的利益平衡作出的不同选择。应当说,尽管这两种设计模式不存在法律逻辑上的优劣之分,但补正处分权的制度安排较之取得物权式的制度安排更能达成善意第三人和本人的利益平衡。(作者单位:九江学院政法学院)
注释
①马俊驹:《民法案例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49页。
②张广兴:《债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210页。
③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
善意取得制度范文第3篇
善意取得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形式。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文对善意取得的概念、价值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渊源、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及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进行了阐述。以期对我国的物权法、民法典的建立尽绵薄之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善意取得概述
(一)善意取得的含义。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另一种认为善意取得既可适用于动产亦可适用于不动产。(二)善意取得之价值基础善意取得制度,为近代以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法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三)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就实质来看,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种以牺牲财产的静的安全为代价而保护财产的动的安全的制度。(四)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渊源。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以来以日耳曼法的制度设计为基础,又吸纳了罗马法上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得以产生发展起来的。
二、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在我国将要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法体系中,应将善意取得制度规定如下构成要件:(一)受让人须为善意。善意取得中的“善意”系指行为人在为某种民事行为时不知存在某种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的一种心理状态。(二)受让人须通过有偿的法律行为而取得所有权。(三)受让人须实际占有由让与人转移占有的动产。(四)客体物须为(以交付为物权的公示方法的)动产。(五)让与人须为无处分权人。无处分权人是指没有处分财产的权利而处分财产的人。(六)让与人须为动产的占有人。
三、不动产善意取得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是否适用于不动产,各国立法规定不一,并且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亦存不同见解。主要有否定说和肯定说,否定说虽然都反对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其各自反对的理由并不相同;持肯定说的学者虽然都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其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依据存在分歧。
四、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此章节中主要包括了以下三点: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原所有权人与受让人之间。原所有权人与让与人之间。
当前我国正在制定民法典,善意取得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方式,应当规定在物权法中。善意取得制度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项交易规则,其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维护正常的商品交换,能有利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虽尚未确认善意取得制度,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承认善意购买者可以取得对其购买的、依法可以转让的财产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指出:“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一、善意取得概述
(一)善意取得的含义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另一种认为善意取得既可适用于动产亦可适用于不动产。从理论渊源上看,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但从价值基础和理论基础上看,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不动产亦无不可。动产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将其有权占有的他人的动产交付于买受人,如买受人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则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原动产所有权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原物。不动产善意取得,受让人信赖登记证书而与无权处分不动产的让与人交易,如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则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原不动产所有权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原物。
按照法律的一般规则,只有所有权或受人之托、代他人处分的人才有处分或买卖财产的权利,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之物,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其所为的法律行为须于事后取得其权利或经该他人之承认,始生效力,而且,所有权具有追及性,可直接向买受人追回原物。但善意取得制度的意义在于阻却所有权人的追及,允许善意的买受人取得受让物的所有权,保护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已经完成的交易,这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所有权人的利益。法律为何会作出这样的抉择呢?这就涉及到善意取得制度的价值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渊源。
(二)善意取得之价值基础
善意取得制度,为近代以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法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其涉及民法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与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之保护问题。保护静的安全即是对所有权给予绝对的保护,保护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即是对财产流转的保护。善意取得制度本质上是平衡所有权人利益和善意受让人利益的一项制度,一方面旨在一定程度维护所有权人的利益,保证所有权安全,保持社会秩序的平和稳定,另一方面又侧重维护善意受让人的利益,促进交易便捷和保护交易安全。当在保护真正的权利人与保护善意受让人之间发生冲突时,应当侧重于保护善意受让人。这样不仅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而且有利于鼓励交易;保护善意的受让人将使受让人形成一种对交易的合法性、对受让的标的物的不可追夺性的信赖与期待,这就对当事人从事交易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使其对交易产生安全感,并能大胆地从事交易。保护善意的受让人将有利于建立一种真正的信用经济,并使权利的让渡能够顺利的、有秩序的进行。在此种情况下,对真正权利人的利益的限制,亦含有把真正权利人选任托付自己财产的当事人考虑不周的责任归咎于他,他自己也应当承担不当选择的不利后果的意思。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要求每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都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细考察,无疑会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不利于信用经济的建立,也会从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日益频繁、交易过程纷繁复杂,且交易越来越需要迅速快捷,因此不可能要求交易当事人在从事交易之前,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调查了解标的物的权利及变动状态,了解交易的对方是否有权作出处分,否则不仅会使交易难以迅速达成而且也会防碍交易的正常进行。善意取得制度适应我国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应确立为民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三)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
就实质来看,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种以牺牲财产的静的安全为代价而保护财产的动的安全的制度。法律为何要牺牲财产的静的安全以保护财产的动的安全呢?这便涉及到善意取得存在的理论基础的问题。关于善意取得存在的理论基础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致有以下观点:
(1)取得时效说。时效制度,以时间及时间之经过为其构成要素,而善意取得制度则与时间及时间之经过没有联系,所以,时效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是两种各自独立的制度。
(2)权利外形说。占有人应推定其为法律上的所有者,故受让人有信赖之基础。
(3)法律赋权说。善意取得是由于法律赋予占有人处分他人所有权的权能。
(4)占有效力说。善意取得系由于受让人受让占有后,占有之效力使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法律上承认占有公信力的逻辑结果,即赞成权利外形说。
善意取得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方式,所有权属于物权,物权是一种对世权,物权对世人的对抗是以对方知情为前提的。因此,物权必须具有向世人公开的手段,这就是占有和登记。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为占有;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为登记。物权的变动以占有和登记为公示方法,当事人如果信赖这种公示而为一定的行为,即使占有和登记所表现的物权状态与真实的物权状态不相符合,也不能影响物权变动的效力。占有仅对动产具有公信力,即动产的占有人即被推定为所有权人。第三人正是基于占有来判断无处分权人是所有人,因此信任他应有处分权而为交易行为的。受让人信任的基础是占有的公信力。对于不动产,只有登记证书才能表征所有权,标的物的转移占有并不移转所有权,只有经登记取得证书后才发生所有权移转的效力,但是,不动产交易也会因登记错误、疏漏、未登记等原因发生无权处分问题,若不动产交易中第三人取得不动产时出于善意,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交易秩序的目的出发,应当允许第三人获得不动产的所有权。
(四)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渊源
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以来以日耳曼法的制度设计为基础,又吸纳了罗马法上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得以产生发展起来的。
在古代,调整无权转让关系的法律有两种不同的立法原则,即罗马法的“任何人不得将大于其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日耳曼法的基于“以手护手”观念,采纳的“所有人任意让他人占有其物的,只能请求该他人返还”的原则。罗马法的原则侧重对所有权人的保护,日耳曼法的原则侧重对受让人利益的保护。罗马法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即使受让人为善意,所有权人也可对其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但罗马法并非完全无视受让人的利益,而是规定善意受让人可主张时效取得。日耳曼法认为一旦权利人将自己的财产让与他人占有,只能向占有人请求返还占有物,如占有人将财产移转给第三人时,权利人不得向第三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只能向转让人请求赔偿损失。善意取得制度虽源于日耳曼法“以手护手”的原则,但二者在制度设计上仍存在差异。日耳曼法“以手护手”原则采取的是限制所有权追及力之结构,而且适用时根本无须区分受让人为善意还是恶意;善意取得制度采取的是使受让人取得所有权之结构,其目的在于积极地使受让人取得所有权,而非仅仅消极的限制原所有权人之恢复请求权。
善意取得制度之所以源于日耳曼法,是因为在日耳曼法上占有与所有权并未严格区分,占有其物者即有权利,而对物享有权利的也必须占有物,因而受让物的占有者,可能取得权利,而有权利但却未直接占有其物时,其权利的效力也因之减弱。当动产所有权人以自己的意思,将动产托付于他人而由他人直接占有时,所有权人权利的效力减弱,一旦直接占有人将动产让与第三人,所有人就无从对该第三人请求返还。善意取得制度之所以不能追溯到罗马法,是因为在罗马法上所有权概念出现较早,占有和所有权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所以无法演绎出以受让人误信物的占有人为有处分权人为适用前提的善意取得制度。
二、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在我国将要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法体系中,应将善意取得制度规定如下构成要件:
(一)受让人须为善意
善意取得中的“善意”系指行为人在为某种民事行为时不知存在某种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的一种心理状态。由于善意只是受让人取得财产时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状况很难为局外人得知,因此,确定受让人是否具有善意,应考虑当事人从事交易时的客观情况。如果根据受让财产的性质、有偿或无偿、价格的高低、让与人的状况以及受让人的经验等可以知道转让人无权转让,则不能认为受让人具有善意。受让人在让与人交付财产时必须是善意的,至于以后是否为善意,并不影响其取得所有权。如果受让人在让与人交付财产以前具有恶意,则可以推定其接受财产时为恶意。①
(二)受让人须通过有偿的法律行为而取得所有权
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而设定的,只有在让与人和受让人之间存在交易行为时,法律才有保护的必要;适用善意取得制度,除要求交易行为中让与人无处分权外,必须具备法律行为的其他一切生效要件,如该交易行为本身无效或可撤销,则不能发生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还应以受让人有偿取得动产为前提。若无偿转让动产,在许多情况下,本身就表明该动产的来源可能是不正当的,此时一个善意的受让人是不应受让这样的动产的;同时,受让人返还这样的动产并不会给其造成大的损失,受让人应返还该动产。
(三)受让人须实际占有由让与人转移占有的动产
所谓动产占有之转移,包括四种情形:现实交付,简易交付,占有改定,返还请求权之让与。现实交付,即直接占有的转移。简易交付,即受让人已经占有动产,则于物权变动的合意成立时,视为交付。占有改定,即动产物权的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特别约定,标的物仍然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这样,在物权让与的合意成立时,视为交付,受让人取得间接占有。返还请求权让与,即动产由第三人占有时,出让人将其对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受让人,以代替交付。在现实交付及简易交付场合,因受让人都已直接占有动产,其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动产权利,自无疑义。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依占有改定方式进行交易时,基于上述善意取得之价值基础的考虑,不宜支持占有改定方式下的受让人取得所有权。可见,只有当受让人实际占有该动产时,才适用善意取得。
(四)客体物须为(以交付为物权的公示方法的)动产
动产,是指能够移动而不损害其价值或用途的物。动产的公示以占有为原则,登记为例外。以登记为公示原则的动产,如航空器、船舶等,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
自近代以来,物被区分为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这通常是各国建立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占有委托物,指基于租赁、保管等契约关系,由承租人、保管人等实际占有的、属于出租人、委托人所有的物。简言之,它是基于真正权利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之物。占有脱离物,是非基于真正权利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之物,如盗品、遗失物等均属占有脱离物。占有脱离物原则上不发生善意取得,而占有委托物则相反,原则上得发生善意取得。这样规定同样是基于上述善意取得之价值基础的考虑。
(五)让与人须为无处分权人
无处分权人是指没有处分财产的权利而处分财产的人。若让与人为有处分权人,则其转让为有权行为,不欠缺法律依据,自然无法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是一对关系密切的制度,两者完全不可分割。无权处分是善意取得的前提,而善意取得则主要适用于无权处分行为。当真正的权利人拒绝追认时,如果有偿交易行为中的受让人是善意的,无权处分的合同仍然有效,受让人可以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六)让与人须为动产的占有人
善意取得中,因受让人为善意受让占有,故须有让与人占有可资信赖,始有善意之可言,让与人若非动产占有人,就没有占有的公信力。占有仅须让与人对动产有现实的管领力即可,而不以对动产的直接占有为必要。换言之,即使对动产为间接占有、辅助占有乃至瑕疵占有,也无不可。
三、不动产善意取得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是否适用于不动产,各国立法规定不一,并且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亦存不同见解。主要有否定说和肯定说,否定说虽然都反对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其各自反对的理由并不相同;持肯定说的学者虽然都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其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依据存在分歧。我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亦可适用于不动产,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主要发生于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共有房屋的部分共有人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受让人在善意时即可取得所有权。第二种情况是,不动产登记瑕疵,受让人信赖此发生的不动产所有权转移。
如上所述,善意取得制度是以日耳曼法的制度设计为基础,又吸纳了罗马法上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得以产生发展起来的。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注重权利的外观,该原则虽然并未蕴含交易安全的理念,但却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保护交易安全的客观需要,因而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善意取得适用于不动产是由于第三人信任不动产的表征手段——登记所致,登记与占有都具有表征权利的功能。由于我国目前的登记制度较为混乱和不规范,登记的程序和审查制度也尚待改进,我国不动产登记中的错漏在所难免,为保护不动产交易的安全,我国将来的物权立法中应当确立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
各国立法对善意取得制度是否适用于不动产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各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同。采形式审查主义的国家,善意取得制度一般不适用于不动产;采实质审查主义的国家,善意取得制度一般适用于不动产。这是因为采形式审查主义的国家,对于登记的申请,只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至于登记证上所载权利事项有无瑕疵,则不予过问,这样的公示不具有公信力。采实质审查主义的国家的登记具有公信力,依公示公信原则,只要无异议登记,即使登记所记载的权利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符,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的利益仍受法律保护。我国对不动产登记实行的是实质审查主义,所以,我国应建立完善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基本上与动产相同。不动产善意取得须受让人信赖登记证书而与让与人交易,事后真正的权利人主张该买卖行为无效,受让人可主张善意购买而取得所有权。不动产的买卖必须具有一般不动产买卖的形式要件,即必须缔结不动产买卖合同、交付标的物并进行过户登记。只有履行完登记手续的善意受让人才可以取得所有权,在这里登记的作用相当于动产的交付。
四、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善意取得制度涉及三方当事人,即原所有权人,让与人和受让人。在符合以上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即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下面将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产生的法律效果分述如下:
(一)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
基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受让人取得让与人转让的交易财产的所有权。让与人和受让人应履行所有权转移的权利和义务,受让人应支付价款,让与人应协助将交易财产的所有权移转于受让人。让与人不得再依自己无处分权或依所有权人追索或索赔,而请求受让人返还财产。②
(二)原所有权人与受让人之间
基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善意受让人取得让与人出让的财产的所有权,原所有权人不得向善意受让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三)原所有权人与让与人之间
原所有权人与让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原所有权人与让与人之间原来存在合同关系,如当事人之间存在着租赁、保管等合同关系的。原所有权人可主张让与人承担违约责任,也可向让与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还可以依侵害其所有权而主张侵权损害赔偿,此时请求权发生竞合,原所有权人可选择适用。
第二种情况原所有权人与让与人之间原来不存在合同关系,如让与人是基于盗窃、拾得遗失物而取得财产的。原所有权人可向让与人主张侵权责任的承担,也可向让与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此时请求权发生竞合,原所有权人可选择适用。
注释
①王利明王轶:《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载于《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
②王燕:《“善意取得”新探》载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高富平:《物权法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2、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3、魏振赢:《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余淑玲:《善意取得制度初探》,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6期
5、李建华傅穹:《论占有与善意取得》,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
6、王利明:《论无权处分》,载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7、王泽鉴:《民法物权通则所有权》,1993年9月版
善意取得制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善意取得 《物权法》 处分权
一、善意取得的概念以及存在的意义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事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在将其占有的他人动产交付于买受人后,若买受人于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即取得该动产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
善意取得制度,为近代以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法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民法物权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涉及到民法财产所有权的静态安全与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保护的优先与取舍,对于保护善意取得财产的第三人合法权益,维护交易活动的动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善意取得是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市场广泛的商品交换中,从事交换的当事人往往并不知道对方是否有权处分财产,因交易成本过高等因素也很难对市场出售的商品逐一调查。因而在市场或商店购物,如果买受人善意取得财产后,根据转让人的无权处分而使交易无效,并让买受人返还财产,则不仅要推翻已经形成的财产关系,而且使买受人担心买到的商品有可能随时退还,这样会造成买受人在交易时的不安全感,也不利于商品交换的稳定。可见,善意取得制度虽然限制了所有权的追及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它在保护交易安全,促进财货流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近 现代 民法上,由于该制度巨大功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普遍确认了这一制度。
二、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1.受让人取得财产时出于善意
如果取得财产时让与人为善意,受让人为恶意,就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所谓善意是相对于恶意而言的,是受让人在受让动产时主观心理状态。如何确定善意,学说上有“积极观念说”和“消极观念说”两种主张,由于积极观念说对受让人要求过于苛刻,因而赞成消极观念说的居多。受让人善意,是指受让人误信财产的让与人为财产的所有人。由于善意只是受让人取得财产时的一种心理状况,这种状况很难为局外人得知,因此,确定受让人是否具有善意,应考虑当事人从事交易时的客观情况。
2.取得的标的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善意取得仅适用于动产而不适用于不动产。因为动产物权以占有为公示方法,动产的占有人推定为动产的所有人,才会发生第三人信赖其占有效力而与之交易,并受让该动产,而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公示方法,权利归属十分明显,不必以善意取得而对交易安全加以特殊保护。但在
3.受让人必须通过交易行为取得物的占有
受让人取得财产主要是通过买卖、互易、债务清偿、等具有交换性质的行为实现的。如果通过继承、遗赠等行为取得的财产,不能产生善意取得的效力。因为继承人、受遗赠人只能从被继承人和遗赠人那里取得其个人的合法财产,而不能通过继承和受遗赠而取得继承人和遗赠人以外的他人的财产。如果允许对这些财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财产纠纷,妨碍继承和遗赠的正常进行。如果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从事的买卖等行为是无效的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也不能产生善意取得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应按法律关于民事行为无效和得撤销的规定,由双方或一方返还财产,恢复财产关系的原状
4.让与人必须为无权处分人
所谓无权处分,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的财产权利。处分财产只能有享有处分权的人行使,非处分权人处分他人的财产则构成对他人财产的侵害。非处分权人的处分包括如下情况:第一,不享有所有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如承租人、租用人转让承租和借用的财产。第二,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并对该财产予以处分,如小偷转让赃物。第三,虽享有所有权,但所有权受到限制,如所有人的财产被查封、扣押以后,所有人仍非法转让财产。第四,某个或某些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擅自处分共有财产。
5.让与人需为动产标的物的占有人和不动产的公示占有人。
三、我国目前善意取得制度有关规定
我国在《物权法》颁布之前并没有具体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只是在一些司法解释中可以找到该制度的相关依据,并且仅仅限于动产的善意取得。2007年10月颁布的《物权法》确立了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 《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行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3)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物权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善意取得适用于所有物权是一次重大的突破,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转轨时期,许多不动产登记制度尚未完善,如在房屋预售的过程中,存在“一房二卖”,甚至“一房多卖”的情况,导致许多购房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因此,将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不动产交易的领域,可最大限度的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地发展。该制度也成为我国《物权法》当中的一个亮点。
但是,在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时,以下两个问题应当引起注意:第一,我国物权法规定了异议登记制度。所谓异议登记,就是将事实上的权利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对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所提出的异议记入登记簿,异议登记的法律效力是,登记簿上所记载权利失去正确性推定的效力,第三人也不得主张依照登记的公信力而受到保护。由此可见,在异议登记的情况下没有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可能。第二,对于土地所有权和违章建筑不适用善意取得。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不存在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没有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必要。同时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违章建筑的建造违反了强行法的规定,因此不能成为交易的标的物,所以不存在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问题。
参考 文献 :
善意取得制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善意取得 《物权法》 处分权
一、善意取得的概念以及存在的意义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事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在将其占有的他人动产交付于买受人后,若买受人于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即取得该动产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
善意取得制度,为近代以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法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民法物权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涉及到民法财产所有权的静态安全与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保护的优先与取舍,对于保护善意取得财产的第三人合法权益,维护交易活动的动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善意取得是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市场广泛的商品交换中,从事交换的当事人往往并不知道对方是否有权处分财产,因交易成本过高等因素也很难对市场出售的商品逐一调查。因而在市场或商店购物,如果买受人善意取得财产后,根据转让人的无权处分而使交易无效,并让买受人返还财产,则不仅要推翻已经形成的财产关系,而且使买受人担心买到的商品有可能随时退还,这样会造成买受人在交易时的不安全感,也不利于商品交换的稳定。可见,善意取得制度虽然限制了所有权的追及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它在保护交易安全,促进财货流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近现代民法上,由于该制度巨大功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普遍确认了这一制度。
二、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1.受让人取得财产时出于善意
如果取得财产时让与人为善意,受让人为恶意,就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所谓善意是相对于恶意而言的,是受让人在受让动产时主观心理状态。如何确定善意,学说上有“积极观念说”和“消极观念说”两种主张,由于积极观念说对受让人要求过于苛刻,因而赞成消极观念说的居多。受让人善意,是指受让人误信财产的让与人为财产的所有人。由于善意只是受让人取得财产时的一种心理状况,这种状况很难为局外人得知,因此,确定受让人是否具有善意,应考虑当事人从事交易时的客观情况。
2.取得的标的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善意取得仅适用于动产而不适用于不动产。因为动产物权以占有为公示方法,动产的占有人推定为动产的所有人,才会发生第三人信赖其占有效力而与之交易,并受让该动产,而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公示方法,权利归属十分明显,不必以善意取得而对交易安全加以特殊保护。但在中国现阶段,仍处于市场经济制度转轨时期,物权登记公示制度不完善,所以为了适应该时期的发展更好地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也适应善意取得。但是也并非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一些例外的规定在我国相关的法律条文中都有具体的规定,在此不再赘述。
3.受让人必须通过交易行为取得物的占有
受让人取得财产主要是通过买卖、互易、债务清偿、等具有交换性质的行为实现的。如果通过继承、遗赠等行为取得的财产,不能产生善意取得的效力。因为继承人、受遗赠人只能从被继承人和遗赠人那里取得其个人的合法财产,而不能通过继承和受遗赠而取得继承人和遗赠人以外的他人的财产。如果允许对这些财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财产纠纷,妨碍继承和遗赠的正常进行。如果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从事的买卖等行为是无效的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也不能产生善意取得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应按法律关于民事行为无效和得撤销的规定,由双方或一方返还财产,恢复财产关系的原状
4.让与人必须为无权处分人
所谓无权处分,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的财产权利。处分财产只能有享有处分权的人行使,非处分权人处分他人的财产则构成对他人财产的侵害。非处分权人的处分包括如下情况:第一,不享有所有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如承租人、租用人转让承租和借用的财产。第二,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并对该财产予以处分,如小偷转让赃物。第三,虽享有所有权,但所有权受到限制,如所有人的财产被查封、扣押以后,所有人仍非法转让财产。第四,某个或某些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擅自处分共有财产。
5.让与人需为动产标的物的占有人和不动产的公示占有人。
三、我国目前善意取得制度有关规定
我国在《物权法》颁布之前并没有具体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只是在一些司法解释中可以找到该制度的相关依据,并且仅仅限于动产的善意取得。2007年10月颁布的《物权法》确立了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 《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行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3)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物权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善意取得适用于所有物权是一次重大的突破,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转轨时期,许多不动产登记制度尚未完善,如在房屋预售的过程中,存在“一房二卖”,甚至“一房多卖”的情况,导致许多购房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因此,将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不动产交易的领域,可最大限度的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地发展。该制度也成为我国《物权法》当中的一个亮点。
但是,在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时,以下两个问题应当引起注意:第一,我国物权法规定了异议登记制度。所谓异议登记,就是将事实上的权利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对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所提出的异议记入登记簿,异议登记的法律效力是,登记簿上所记载权利失去正确性推定的效力,第三人也不得主张依照登记的公信力而受到保护。由此可见,在异议登记的情况下没有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可能。第二,对于土地所有权和违章建筑不适用善意取得。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不存在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没有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必要。同时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违章建筑的建造违反了强行法的规定,因此不能成为交易的标的物,所以不存在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4).
善意取得制度范文第6篇
【摘 要】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它起源于日尔曼法中“以手护手”原则。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在广泛的商品交换中要求交易一方了解对方是否有对标的物的处分权实属困难,若因此而导致交易的无效,否定已形成的财产关系,就会使得一切交易蒙上不安全的阴影,也不利于维护商品交换秩序的稳定,所以善意取得制度已经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本文阐述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概念以及构成要件,并且针对目前我国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发表了一些的观点。 【论文关键词】善意取得 《物权法》 处分权 一、善意取得的概念以及存在的意义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事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在将其占有的他人动产交付于买受人后,若买受人于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即取得该动产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 善意取得制度,为近代以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法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民法物权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涉及到民法财产所有权的静态安全与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保护的优先与取舍,对于保护善意取得财产的第三人合法权益,维护交易活动的动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善意取得是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市场广泛的商品交换中,从事交换的当事人往往并不知道对方是否有权处分财产,因交易成本过高等因素也很难对市场出售的商品逐一调查。因而在市场或商店购物,如果买受人善意取得财产后,根据转让人的无权处分而使交易无效,并让买受人返还财产,则不仅要推翻已经形成的财产关系,而且使买受人担心买到的商品有可能随时退还,这样会造成买受人在交易时的不安全感,也不利于商品交换的稳定。可见,善意取得制度虽然限制了所有权的追及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它在保护交易安全,促进财货流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近现代民法上,由于该制度巨大功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普遍确认了这一制度。 二、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1.受让人取得财产时出于善意 如果取得财产时让与人为善意,受让人为恶意,就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所谓善意是相对于恶意而言的,是受让人在受让动产时主观心理状态。如何确定善意,学说上有“积极观念说”和“消极观念说”两种主张,由于积极观念说对受让人要求过于苛刻,因而赞成消极观念说的居多。受让人善意,是指受让人误信财产的让与人为财产的所有人。由于善意只是受让人取得财产时的一种心理状况,这种状况很难为局外人得知,因此,确定受让人是否具有善意,应考虑当事人从事交易时的客观情况。 2.取得的标的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善意取得仅适用于动产而不适用于不动产。因为动产物权以占有为公示方法,动产的占有人推定为动产的所有人,才会发生第三人信赖其占有效力而与之交易,并受让该动产,而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公示方法,权利归属十分明显,不必以善意取得而对交易安全加以特殊保护。但在中国现阶段,仍处于市场经济制度转轨时期,物权登记公示制度不完善,所以为了适应该时期的发展更好地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也适应善意取得。但是也并非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一些例外的规定在我国相关的法律条文中都有具体的规定,在此不再赘述。 3.受让人必须通过交易行为取得物的占有 受让人取得财产主要是通过买卖、互易、债务清偿、等具有交换性质的行为实现的。如果通过继承、遗赠等行为取得的财产,不能产生善意取得的效力。因为继承人、受遗赠人只能从被继承人和遗赠人那里取得其个人的合法财产,而不能通过继承和受遗赠而取得继承人和遗赠人以外的他人的财产。如果允许对这些财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财产纠纷,妨碍继承和遗赠的正常进行。如果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从事的买卖等行为是无效的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也不能产生善意取得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应按法律关于民事行为无效和得撤销的规定,由双方或一方返还财产,恢复财产关系的原状 4.让与人必须为无权处分人 所谓无权处分,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的财产权利。处分财产只能有享有处分权的人行使,非处分权人处分他人的财产则构成对他人财产的侵害。非处分权人的处分包括如下情况:第一,不享有所有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如承租人、租用人转让承租和借用的财产。第二,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 并对该财产予以处分,如小偷转让赃物。第三,虽享有所有权,但所有权受到限制,如所有人的财产被查封、扣押以后,所有人仍非法转让财产。第四,某个或某些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擅自处分共有财产。 5.让与人需为动产标的物的占有人和不动产的公示占有人。 三、我国目前善意取得制度有关规定 我国在《物权法》颁布之前并没有具体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只是在一些司法解释中可以找到该制度的相关依据,并且仅仅限于动产的善意取得。2007年10月颁布的《物权法》确立了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 《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行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3)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物权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善意取得适用于所有物权是一次重大的突破,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转轨时期,许多不动产登记制度尚未完善,如在房屋预售的过程中,存在“一房二卖”,甚至“一房多卖”的情况,导致许多购房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因此,将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不动产交易的领域,可最大限度的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地发展。该制度也成为我国《物权法》当中的一个亮点。 但是,在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时,以下两个问题应当引起注意:第一,我国物权法规定了异议登记制度。所谓异议登记,就是将事实上的权利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对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所提出的异议记入登记簿,异议登记的法律效力是,登记簿上所记载权利失去正确性推定的效力,第三人也不得主张依照登记的公信力而受到保护。由此可见,在异议登记的情况下没有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可能。第二,对于土地所有权和违章建筑不适用善意取得。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不存在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没有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必要。同时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违章建筑的建造违反了强行法的规定,因此不能成为交易的标的物,所以不存在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问题。
善意取得制度范文第7篇
法学六班 解鸿岩 20181014480
一、善意取得概念
善意取得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指无权处分人将他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若受让人取得时出于善意,则确定地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原所有权人不能追夺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放弃了近代民法以所有权神圣为核心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
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根据,向来有争议。即时时效说认为其依据在于适用即时时效或瞬间时效;权利外像说认为其依据在于对权利外像的保护;法律赋权说认为在善意取得权利的情况下,是法律赋予占有人以处分他人所有权的权能;占有保护说则认为根据公示主义,占有人应该推定其为法律上的所有人;法律特别规定说则认为善意取得系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我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存在依据即在于交易的安全与便捷。可见,近代民法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各国民事立法政策为保护市场交易安全、便捷而建立的制度。
近代民法,以所有权神圣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被认为是整个社会得以存续发展的重要基石。然而,善意取得制度竟然打破了所有权神圣的绝对观念,而肯定善意受让人的利益更值得保护,其确立是对所有权绝对尊重的一种扬弃,处处渗透着经济社会保护交易安全与便捷的客观现实,是促成近代各国民法最终确立善意取得制度的根本缘由。
《物权法》正是基于保护交易安全的考虑,在其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二、我国善息取得制度的发展
在07年的《物权法》中,明确了善意取得的规定。在此之前,虽然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善意取得制度,主要是在各部门的司法解释中,善意取得制度规定,罪犯赃物应当自行追缴,受让人的知道物必迫偿。如果受让人不知道被盗,罪犯将以原始价格赎回或补偿赃物。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要求赃物应适用善意,未被告知受的让人占有赃物的所有权,但是国家法律需要考虑到善意受让人自身的利益亏损,并规定为受让人获得相对应的赔偿。由此可以认为,我国的《物权法》正是摸索善意取得制度道路的开端。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赃物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在《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意见》之中,第89条有着明确的规定,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同财产,而其中第三人的行为乃为善意行为,并支付了价款,获得共有财产的结果是第三方获得财产,未经授权的处理人员需要对其他共有人负责任,而这一规定恰当地反映出了善意取得制度的特点。然而,我们仍是尚不清禁它是否是善意取得制度,这其中还存在不足。
在《票据法》之中,第12条规定,如果,受让人知道转让人通过非法途径获得了票据之后,仍去接受非法票据,这就不能算得上是善意取得票据。最后,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肯定结论:那就是,明确是善照行动而取得票据之人是可以从法律上得到《票据法》的保护,获得票据上的权利。
在《拍卖法》中的第58条法案认为,获得者和拍卖人需要一同承应有的责任,承认对方符合法律的善意取得制度。第11条对诈骗案件审理中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受让人若是属于善意地接受他人退还的欠款、贷款或是其他的财务上的费用,那么其财政就不是诈骗罪。另一方面,然后这些属性将无法恢复。依照法律规定,在买卖盗窃以及抢劫机动车的具体事例当中,我国有明确的法案规定了,那些明知是通过非法渠道获得的机动车的买方,该行为属于恶意买卖,在我国法律当中,此等买家是不受保护的,若是其购买者下知道汽车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情况下,买家的利益应受到法律的保障和保护。
于2001年颁布的《信托法》的12条法案认为,即使取消了信托的存在,受益人仍然可以从中得到信托的利益与资金。虽然上述的立法和司法的规定可以获得与善意取得制相同的法律效果,但缺乏系统以及明确的界定,该法的可以使用的范围其实际上而言仍是相当狭小的。它并不适用于民事法律案件。而立法者们为了解决我国在司法法律实际使用取得制度的混乱的现状,立法者们通过多年的刻苦的钻研以在及总结实践经验,最后在《物权法》之中增加了对善意取得度的规定 。
二、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引发善意取得实际发生的条件称为善意取得的要件纵览近现代各国民法规定并结合大陆法系民法理论研究成果,善意取得的要件如下:
1. 受让人在受让时须为善意
善意取得以受让人善意为成立条件,即受让人在转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至于让与人是否为善意则在所不问。受让人是否属于善意的举证责任,应当由主张受让人非善意的一方承担。《法国民法典》第2268条规定:“在任何情形下,占有均推定为善意,主张恶意者应负举证责任。”确定受让人是否善意,应以其受让动产之时的情况判定。动产交付后受让人是否善意,不影响善意取得的成立。但如交付前已知的,可直接认为非善意。
2. 受让人须以合理的价格有偿受让
善意取得制度旨在保护交易安全,只有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存在交易行为时,才存在善意取得问题。通过非交易行为而无偿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占有如赠与继承遗赠等则不能发生善意取得的效力。同样,受让人与让与人不得为同一民事主体。
3. 转让的不动产已经登记,转让的动产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只有通过不动产登记和动产的交付,才发生所有权的移转。如果双方仅达成了合意而未实际办理不动产标的物的过户登记,或者转移动产标的物的占有则双方仍只是一种债的关系,不发生善意取得。此处动产的交付,是否限于现实交付,理论上和立法上有不同的主张。一般认为,如果受让人是以占有改变或指示交付的方式取得无权处分人转让动产的一般不能发生善意取得的效果。而前述《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并没有明确善意取得的交付是现实交付还是观念交付,有待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4.标的物为法律不禁止或者不限制转让
法律禁止流通、限制流通的物,如毒品、枪支弹药、国家专有财产、文物等,均不适用善意取得。
5.转让合同本身应当合法有效
无权处分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转让合同,除欠缺处分外,该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法条件,不属于无效合同或者可撤销合同。但由于该合同转让人欠缺处分权,从而使其处于效力待定状态,若事后经权利人追认该转让行为,则该合同为有效合同,受让人基于该有效合同而取得所有权,不必适用善意取的;若事后权利人不予追认,则该转让合同无效,但受让人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该物的所有权。
四、我国《物权法》中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我国《物权法》从第一百零六条至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从中可以看到,善意取得既适用于动产,又可适用于不动产。当事人出于善意从无处分权人手中购买了房屋并登记过户,善意人取得房屋所有权。善意取得与可追认的无处分权人处分财产行为有别。善意取得制度中出让人与可追认的无处分权人处分财产行为中的出让人均是无处分权人,故善意取得是无处分权人处分财产行为的特别规定。善意取得中的受让人是善意第三人,善意取得行为自始有效,无须权利人追认。可追认的无处分权人处分财产行为中的受让人非善意第三人,其次,出让人无处分权仍受让财产,故该行为是可追认的行为。权利人追认的,让与行为自始有效;权利人不追认的,让与行为自始无效。
善意取得制度范文第8篇
[关键词]善意取得 物权 法律效力
一、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状况及其价值取向
善意取得,又称及时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人将其动产或不动产转让给受让人,如果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则受让人将依法取得对该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
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尚未确立善意取得制度,但《拍卖法》第58条、《票据法》第12条的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都设有或可推导出善意取得制度的相关规定。《物权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3)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这一规定正式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践依据是保护交易安全。交易安全又称动的安全,它与静的安全相对应。民法上素有“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的区分,“静的安全”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为宗旨,对原权利人现存的既得利益加以保护,使其免受他人的不法侵害,力图保持社会秩序的平和稳定;“动的安全”则以保护善意无过失的交易者的利益为使命,意在圆滑财产流通,从而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经济秩序。若从保护静的安全出发,所有权将得到绝对的保护。所有权人得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而受让人只能依靠相应法律去寻求救济。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再绝对贯彻所有权的绝对原则,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护动的安全,从而承认善意取得制度,有其必要,其理由在于:
1.一旦不保护交易安全,则任何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在购买财产或取得财产上设定的权利时,都需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尽确实的调查,以排除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财产及相应权利的可能。这无疑会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另外,民事主体将要为调查所支出的交易费用也将使其望而却步,这就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
2.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物品,大多物品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取其替代品。在这一背景下,与其保护静的安全,摧毁已存的法律关系的效力,以牺牲业已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代价,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如保护动的安全,使善意受让人取得物品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而由原权利人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民事责任的承担,从而补救其损失更为妥当。
3.保护动的安全,并非绝对有损原权利人的利益。在原权利人发觉其物已被无权处分人转让之前,或在其向善意受让人主张返还请求权之前,物品已灭失的,保护静的安全而不保护动的安全,对原权利人并无实益,而且一旦物品系因不可抗力灭失的,以保护静的安全为前提,物的风险仍由原权利人负担,此时与保护动的安全相比,反而对其不利。
4.保护动的安全,承认善意取得制度,兼有道德上的考虑。与善意受让人相比,原权利人能够对无权处分人施加远远大得多的影响,他完全有可能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对物的无权处分。善意受让人对他无法控制的风险承担责任,而与此同时,使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受可由其控制的风险的影响,无疑有悖于我们通常所信守的公平观念,更何况原权利人的控制成本常常要低于善意受让人的调查成本。
二、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1.标的物为动产或不动产
善意取得的标的物,以动产或不动产为限。动产物权以占有为其公示方法,交易中极易使人误信占有人为所有人或者有处分权的人,故善意取得的标的物应主要为动产。不动产以登记为物权的公示方式。我国《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不动产也可以发生善意取得。物权的存在既然以占有或登记为其表证,对于信赖此表证而同占人,登记人进行交易,纵使其表证与实质的权利不符,法律仍承认具有和真实物权相同的法律效果,善意受让人善意取得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自无疑义。
2.让与人必须为无权处分人
无权处分,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的财产权利的行为。即通过买卖、赠与、抵押等使所有权发生转让或者权能发生分离的情形。无权处分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不享有所有权或者不享有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2)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并对该财产予以处分;(3)所有权受到限制而处分财产;(4)虽有所有权但无处分权,却处分了财产;(5)人擅自处分被人的财产。如果让与人是有处分权的人,则不需要考虑善意取得的问题。
3.受让人必须是善意取得动产或不动产
受让人的善意亦即第三人的善意。如何判断受让人的善意,理论上有两种判断标准的学说,一种称之为“消极观念说”,认为第三人在取得该动产之时,根据客观情况和第三人的交易经验等考察,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出让人无权处分该财产。这一观点为我国立法及多数学者所主张;另一种称之为“积极观念说”,认为受让人必须具有将他人(出让人)视为所有人的观念。相比较而言,消极观念说对受让人善意的判断比积极观念说要简便易行得多,因为前者具有客观性,容易把握;而若以后者为依据,则势必要对人之主观心理加以考察,显然较为困难。因此,采取“消极观念说”作为判断受让人善意的标准较为科学。
4.受让人须依据法律行为有偿取得财产
善意取是制度旨有实现交易安全,而交易行为又几乎为法律行为,因此,事实行为并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因而,受让人只有通过法律行为,始得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此项法律行为必须满足法律行为本身有效的要件,即当事人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不违背法律规定等。另外,此法律行为具有交易行为性质和有偿,则转让人与受让人在法律上或者经济上同属于一人时,就无交易行为的性质,从而不发生善意取得。
5.受让人须已实际占有受让财产
占有是第三人取得权利的基础。在受让人已实际占有动产或不动产时,各国立法和学说一般都认为受让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财产权利。在以指示交付作为财产交付方式的场合下,让与人将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让与给受让人时,受让人便可取得财产权利。依占有改定方式交付财产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各国立法差异较大,德国民法对此持否定态度,而瑞士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则认为依占有改定而交付时亦可取得财产所有权。笔者认为占有改定不发生善意取得效力。理由在于:首先,善意取得制度是基于占有的公信力来维护交易安全的信赖基础。这种占有必须是直接的,易于识别判断的,而非观念上的,难以识别判断的占有。在占有改定情形下,善意受让人未取得物之直接占有,仅取得间接占有,难谓具有占有公信力;其次,善意取得制度的确立反映了物权制度从重“所有”到重“利用”的发展轨迹。物尽其用,财尽其效是善意取得制度的价值目标之一。而在占有改定场合下,这一价值目标自然无从实现;最后,依占有改定为交付方式的情形下,还会出现重复转让的情况,并据此而产生一物两权的混乱现象,何者权利优先实现,难以抉择。
三、关于善意取得的法律效力
最公平、最正义的善意取得制度应该是均衡这种“侧重效率与动态安全的保护,且兼顾静态安全”价值取得的有效法律元件。善意取得一旦成立,即在三方面产生法律效力:
1.善意取得对受让人的效力
善意取得制度对善意受让人的效力体现为善意受让人即时取得受让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这是善意取得最基本的效力。由于善意取得不是基于让与人的让与行为而取得权利,而是基于物权法律之直接产生,因此,善意取得之性质为原始取得。原有权利上的各种限制,原则上归于消灭,善意受让人取得完的所有权。其他人在该物上没定的权利,如添附等,也就不复存在。
2.善意取得对原权利人的效力
就原权利人而言,其在该财产上的一切权利归于消灭。不仅原权利人丧失了基于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而产生的物上请求权和债上请求权,即便是其他人设定在该物上的他物权,也一并归于消灭,只能依侵权行为而要求不法转让人赔偿损失。
《物权法》第108条规定:“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但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权利的除外。”据此,受让人善意取得动产所有权后,根据物一权的基本原理,该动产上的原所有权自动消灭。为保护交易安全,该动产之上所有权之外的其他物权也同时消灭。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无处分权人无权处分了原所有权人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使其权利归于消灭。因此原所有权人可以基于债权上的请求权要求无处分权人(转让人)承担合同责任、侵权责任或者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但不能向受让人和其他权利人追及。
3.善意取得对不法转让人的效力
作为不法转让人,他因侵害了原权利人之所有权或其它权利,其转移该财产所获之利益既无法律上之根据亦无合同作基础,实属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因此遭受损失者。如要其返还之不当得利仍不足以弥补原权利人之损失,则应由不法转让人负损害赔偿的责任。如果不法转让人以高于市场价格或财产实际价值的价格出让,高出的部分应一并返还给原权利人。
要建立和完善有我国特色的善意取得制度,就应当一方面吸收世界各发达国家在善意取得立法上的成功经验,汲取有益的教训,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照顾中国的国情,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已被人民群众所广泛接受的优良道德习惯,建立既立足本国国情又借鉴世界先进立法思想和立法经验的善意取得制度。
参考文献:
[1] 孙宪忠:中国物权法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8
[2] 孙笑侠:法理学导论,北京[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6
[3] 谢在全:民法物权法(上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26
善意取得制度范文第9篇
关键词:善意取得制度;物权;合同效力
【中图分类号】D923.2
物权法草案经过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又作了少量改动,但有关善意取得制度的第一百一十一条没有修改。关于善意取得制度,时下学界仍争论不休。代表性的争议有:1、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2、善意取得制度与公示公信原则关系;3、受让人的善意标准;4、权利补正与效力补正的关系。
善意取得制度旨在保护交易安全,鼓励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并尽力促成交易。这符合物权法草案第一条(为明确物的归属,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充分发挥物的效用……)的立法目的,并且,也和我国现行的《合同法》立法目的相通。
物权法草案设定的善意取得是有关物权变动的例外制度,它以所有权为原型,但不限于所有权,理论上还包括租赁使用权、抵押权和质权等几乎所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以所有权变动为例(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以所有权变动为例),善意取得制度中通常包括三方当事人,即原权利人、无处分权人和受让人。物权法草案第一百一十一条对原权利人和受让人依是否善意取得确定物权的归属,以原权利人和无处分权人之间是否不当得利或侵权对原权利人保护。无处分权人和受让人之间合同效力不是物权法规范的范畴,而是债法或合同法的范畴。虽然物权法草案规定了统一的善意取得制度,但仍显粗浅。如果要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还需要司法解释细化,并且通过法官个案适用提炼出有代表性的判例。
一、为何不动产也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立法者把不动产纳入善意取得制度,并且与动产适用相同的构成要件。而以梁慧星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反对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其理由是不动产的公示公信可以对善意受让人进行同样的保护,并且有学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和物权变动公信力原则在要件和效果上几乎相同,不过善意取得者从交易的过程出发,而后者从交易的结果入手进行考察,所以可以大致认为,善意取得是公信力原则的另一种表示方式。”[吴国喆:“善意取得制度的缺陷及其补正”,载《法学研究》第27卷第四期,第1页注释,2005年7月版。]但问题是,物权法草案所设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和物权的公信力原则并不等同。学界通常认为,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而不动产是否适用分歧较大。部分学者认为,不动产经登记后以公信力原则即可保护善意受让人,其没有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这种解释缺乏说服力。理由有三:
其一,不仅不动产适用公示公信原则,动产也同样适用。如果不动产公示公信原则可以使善意受让人受到保护,动产也可以以同样的原则使善意受让人受到保护。如此,善意取得制度根本无存在的必要。坚持仅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另一个理由是:动产以占有作为公示式方,不动产以登记作为公示方式。一般来说,登记须有登记的依据,要遵循登记程序,要接受登记机关的审查。登记因其规范性和公开性较占有这种公示方式更具有公信力。但这不应成为反对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理由。
其二,物权法草案的善意取得制度与公信力原则并不是同义的反复,两者对受让人的保护力度有所不同。物权法草案的善意取得制度在衡平原权利人与受让人的利益时更加向受让人倾斜,这种意图体现了鼓励交易、促成交易和保障交易的商业社会价值观。
物权法草案第一百一十一条共有三款:第一款以所有权为例规定善意取得的四个构成要件;第二款规定所有权人因所有权受到侵害时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追偿损失;第三款规定除所有权外其它物权准用前两款规定。
物权法草案善意取得制度的四个要件是:(一)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二)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三)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四)转让合同有效。一般来说,公信力原则包含三个要件:(一)存在公示的法律事实。物权变动的双方当事人须依法定方式公示其物权变动;(二)受让人与公示的物权人(前手,包括无处分权人)发生了交易,即发生了物权变动。如果彼此之间未发生物权变动则谈不上公信力的适用问题;(三)该受让人对其交易方的公示事实有着充分的信赖。[屈茂辉:“登记的生效时间与公信力”,载中国民商法律网/“判解研究”/“房屋买卖中的物权和债权的关系”。]考察公信力原则和善意取得制度,两者均要求“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即受让人是“善意”。但公信力原则与物权法草案设定的善意取得制度有着明显不同。以不动产为例,公示的方式是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即不动产登记。根据公信力原则的要件(一),交易的“不动产”在交易前须公示(记载于登记簿),而善意取得制度不以“不动产”在交易前须公示为构成要件。并且,不动产公示公信原则要求以完善的登记制度为前提,其主要适用于登记机关错误登记、不动产共有中物权登记在部分共有人名下、登记的基础关系无效而登记尚未涂销等情形。当前,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很不完善:登记机关不统一;登记程序不规范;登记效力不明确等等。今后,物权法颁布实施后,登记制度逐步走向规范,但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再则,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下,我国农村房屋没有实行登记制度,城市或城镇尚有大量私有房屋未进行登记,无论城乡还存在大量有违法建设嫌疑的房屋。综上所述,公信力原则因受到信赖登记簿(记载于登记簿的不动产和部分要求登记的动产)的制约,其对善意受让人保护的广度和深度不及善意取得制度。
其三,以动产和不动产来评判善意取得制度的取舍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我国的物权登记制度不是以动产和不动产来划线,物权法草案延续并完善了这种思路。从物权法草案来看,动产原则上是以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根据,一般不需要登记,但动产中的船舶、飞行器和机动车一般情况下需要登记。不动产原则上是以登记作为物权取得和变动的根据,但根据物权法草案第一百三十条和第一百六十八条,不动产物权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役权不要求登记,并且自合同生效时即设立。有学者认为“在登记对抗主义的立法例中,登记没有公信力。”[屈茂辉:“登记的生效时间与公信力”,载中国民商法律网/“判解研究”/“房屋买卖中的物权和债权的关系”。]这种解释在实践中说不清。根据物权法草案第二十八条,机动车等动产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机动车驾驶人占有机动车是否就可以推定他是所有权人呢?驾驶人身份与行驶证记载不一致时,还能说登记没有公信力吗?
二、“善意”受让人的善意标准如何界定
如前所述,物权法草案第一百一十一条的善意取得制度包含四个要件:
(一)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
(二)以合理的价格有偿转让;
(三)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四)转让合同有效。
以上四个要件没有提到“善意”二字,但该条第三款表述为“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可见“善意”的程度和边界要以这四个要件作为评判标准。四个要件中要件(一)才是实质要件,符合要件(一)才能认定是“善意”。要件(二)是要件(一)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要件(三)明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物权的时点要求。光有善意,不符合要件(三),也不能即时取得物权。和物权变动的一般规则相比较,要件(三)明显有着不同的特点。物权变动的一般规则是区分动产和不动产,动产要求交付,不动产要求登记。而上述要件(三)不区分动产和不动产,以交付为原则,以登记为例外。要件(四)“转让合同有效”严格来说不应当是善意取得制度的要件。合同的效力应当由合同法来界定,而不是物权法。这和《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解释有着极大的关系,由于学界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分歧,物权法草案在第一百一十一条明确“转让合同有效”才有了特殊意义。就此下文还将作详细论述。
如何理解要件(一)“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要理解这段话,要从其中的“或者”是表示并列关系还是表示递进关系入手。如果以二选一的并列关系理解,它的逻辑形式是“A或者B”,具体含义是:具备A时符合条件,具备B时也符合条件;不具备A但具备B时符合条件,同理,不具备B但具备A时也符合条件。回到要件(一)“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这句话,按二选一的并列关系理解为“在受让时知道但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符合条件,或者“在受让时不知道但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符合条件。推理的结果很荒唐,这是因为推理的前提不正确,即不能理解成二选一的并列关系。按递进关系理解,它的逻辑形式仍是“A或者B”,具体含义是:具备A时符合条件,在A是否具备不能确定时,具备B符合条件。回到要件(一)“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这句话,按递进关系理解为“在受让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符合条件,“如果是否知道无法界定,则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符合条件。可见要件(一)中的“或者”表达的应是递进关系,而非并列关系。即便按递进关系推敲,似还不够精确、不够严谨。因此,笔者以为要件(一)的表述方式尚有商榷之处。
依我国学界通说,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是指行为人在为某种民事行为时不知存在某种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善意是相对于恶意而言的,是行为人的内在心理活动状况。善意占有是指占有人认为自己有正当权利而为占有,而恶意占有则是指明知或应当知道而不知道自己无正当权利而为占有。物权法草案设定的善意取得制度没有就受让人应当无过失或者重大过失作出明确规定。考察要件(一)“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其实,此处的“不应当知道”就是关于受让人的过失是否影响善意取得成立的问题。“不应当知道”的反面是“应当知道”,如果应当知道而不知道不能认定是“善意”,行为人显然有过失。
依原权利人与无处分权人有无意思牵连,分为占有物和脱离物。所谓占有物,是指无处分权人是基于原权利人的意愿占有他人之物。如租赁、保管关系等。脱离物是指无处分权人占有他人之物不是源于原权利人的意愿。如无遗嘱的遗产、遗失物、赃物等。根据德国法模式,在善意取得适用的场合要求识别是占有物还是脱离物,脱离物排除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物权法草案设定的善意取得制度没有区分占有物和脱离物,没有排除脱离物的适用。可见,立法者是倾向于扩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
三、对《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再思考
根据物权法草案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适用善意取得时,“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要求“转让合同有效。”现时我国并无统一的民法典或债法,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应符合《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要求。《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当前,学界对这条有着不同的解读。具代表性的观点有:无效说[梁慧星:《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页;江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页。];附停止条件的法律行为说[钱明星、杨秋岭:“房屋的交付与物权变动”,载中国民商法律网/“判解研究”/“房屋买卖中的物权和债权的关系”。。];无权处分行为为无效行为的例外说[转引自钱明星、杨秋岭:“房屋的交付与物权变动”,载中国民商法律网/“判解研究”/“房屋买卖中的物权和债权的关系”。];有效说[吴国喆:“善意取得制度的缺陷及其补正”,载《法学研究》第27卷第四期,第7页,2005年7月版。]等等。似乎持无效说的人占多数,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持有效说。通过和《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比较,笔者发现物权法草案第一百一十一条强调“转让合同有效”,表明当权利人没有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使终没有取得处分权时,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转让合同并不必然无效,至少在善意取得适用的场合,合同有效。这是否意味着间接修改或者补充了《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呢?原权利人不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使终未取得处分权的场合,如果适用善意取得,转让合同有效,如果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没有理由不认定合同有效。至少在物权范围内,合同是否有效与原权利人是否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是否取得处分权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说,原权利人是否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是否取得处分权不是合同有效与否的必要条件。通过以上分析,物权法草案第一百一十一条“转让合同有效”的规定似乎已经事实上修改和补充了《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但是,《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修改和完善,应当通过修改合同法或者对合同法作出立法解释来完善,而这种直接在物权法上规定转让合同有效的方式,在逻辑上说不通。善意取得是物权变动的一项例外制度,因此前述讨论也仅限于物权范围。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被处分的是“财产”,“财产”包括物权法所指的“物”,但是否包括“债权”呢?处分他人“债权”与处分他人“物权”有无本质差别?如果处分的是债权,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这似乎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四、善意取得制度没有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权主体和物的占有常常发生分离;而需要登记的动产和不动产场合,还可能发生权利外观(表征)与真实权利状况的分离。在此状况下,为保障交易安全和明确物权(主要体现为所有权)的归属,善意取得制度应运而生。
但是,物权法草案设立善意取得制度并没有解决当事人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利益。善意取得制度的着眼点和着重点是以所有权为代表的物权归属。对于交易关系中的当事人来说,他们更在意的是利益,而取得物权只是利益的表现形式之一。如果交易中的“物”具有可替代性,关注利益的当事人一般能接受等价物,而不是执着于物的拥有。以不动产为例,有人主张“由于不动产往往价值巨大,不论谁最终取得房产,都使另一方蒙受财产上的巨大损失。因此,简单地在当事人之间进行权属判断显然过于粗糙。所以,在不动产善意取得中,探讨当事人之间的过错,以及基于这种过错确定双方各自应当承担的价值损失比例是比较合理的。”[刘颖,李霞:“诈骗条件下的不动产能适用善意取得吗”,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11月8日版。]由于善意取得制度只解决物的归属,受让人是否应当弥补原权利人的损失并未涉及,即法律并不排斥原权利人有通过受让人获得利益补偿的可能,法官根据公平原则和过错原则,运用自由裁量权在个案中衡平各方利益。所有权如此,其它物权也如此。依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物权的受让人,如果其尚有未曾支付的价金,原权利人可不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权利?如果可以主张权利,原权利人主张的是什么性质的权利?这似乎又是一个问题。
当我们审视善意取得制度时,应当认识不同类型物有着不同的交易形式和交易惯例,并且不同地域的交易环境也千差万别。以广州的房屋买卖为例,房屋交易的合意通常是通过房产中介公司来完成。以一宗发生在广州的盗卖房屋遗产案为例,笔者尝试分析关有各主体间的法律问题和法律关系。三年前,刘某与前妻协议离婚,依协议儿子由前妻抚养,刘某分得市区房屋一套,刘某离婚后没有再婚。三年后,刘某因病突然去世。按法定继承,刘某的房屋遗产由其父亲(母亲先于其去世)和其儿子继承。前妻为儿子办理遗产继承登记时,从房屋登记机关获息房屋遗产已被他人盗卖,产权已变更登记在陌生人陈某名下。房屋被盗卖后,盗卖人隐匿未能找到。由此引发一系列的法律纷争。通过调查,是他人假冒死者刘某之名盗卖了房屋,先是骗过公证机关办理了不真实的“委托公证书”,然后通过中介出售房屋。该交易的全过程包括:房产中介获得房源和有意向买家的信息,通过中介的撮合,买卖双方签下合约,办理公证,申请过户和变更登记,颁发新房产证书。参与的各方包括:“买卖”双方、中介、公证机关和登记机关。涉及的法律关系包括:“买卖”关系、居间关系、公证证明行为和登记机关的行政确认行政行为。在该案中,法定继承人可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公证机关和房屋登记机关撤销公证书和房产证书。而受让人可主张善意取得。当法定继承人或者受让人一方取得房屋产权后,另一方有权向中介公司、公证机关和房屋登记机关提出赔偿要求。盗卖者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如果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解决房屋的归属后,中介公司、公证机关和房屋登记机关应当如何承担法律责任以及如何来分担这种责任呢?根据现有法律,中介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可主张违约或侵权),公证机关[]和房屋登记机关可能承担的限于行政赔偿责任。行政赔偿责任以国家赔偿法为依据,它与民事责任相比,赔偿条件严格,赔偿范围、标准和幅度有限。这起案件法律关系众多,并且有数种可供选择的法律程序。依现行有效的法律维护自己权利的过程中,无论是原权利人还是受让人,可供选择的法律存在冲突和矛盾,而获取法律救济的途径和方式均面临许多的困境和障碍。
参考文献
[1]吴国喆:“善意取得制度的缺陷及其补正”,载《法学研究》第27卷第四期,第1页注释,2005年7月版
[2]屈茂辉:“登记的生效时间与公信力”,载中国民商法律网/“判解研究”/“房屋买卖中的物权和债权的关系”
[3]梁慧星:《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页;江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页
[4]钱明星、杨秋岭:“房屋的交付与物权变动”,载中国民商法律网/“判解研究”/“房屋买卖中的物权和债权的关系”
[5]转引自钱明星、杨秋岭:“房屋的交付与物权变动”,载中国民商法律网/“判解研究”/“房屋买卖中的物权和债权的关系”。
善意取得制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善意,取得,善意取得制度
一、善意取得之概说
(一)善意取得制度探源
从法学发展史观,任何法律制度的设立与架构都与社会资源的占有、利用和分配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有关。正如法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取决于社会经济水平和物质生活条件一样,法律制度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根源于经济基础,并为保护社会经济发展、规范社会和经济秩序服务。自立法价值的取向言,在此且不论公法,就私法言之,其价值取向是以保护多数平等主体而牺牲少数主体为原则,因此,当某一社会资源的占有与分配在社会成员的互动中由少数变为多数时,科学的立法总是适此而变。体现在善意取得制度的确立上,就从所谓“任何人不能以大于己之权利转让于他人”、“发现我物,取回之”[1]的古罗马法所有权绝对主义原则发展为“以手护手”的日耳曼制度。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起源于日耳曼法中的“以手护手”原则,并吸纳罗马法中取得时效的善意要件而发展起来的。[2]善意取得的具体涵义是指,财产的权利人在财产被他人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只能向侵犯其权利的相对人要求返还或赔偿,而不能向第三人要求返还,不知情的第三人对于财产的受让占有,其有转移所有权的效力。其实,善意取得也就是把原所有权追及效力的锁链切断,使得善意第三人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财产所有权。综上所述,善意取得制度是社会所有权观念变动的结果,是一种以牺牲财产“静的安全”为代价而保护财产“动的安全”的制度架构。适应于社会经济发展对交易秩序的稳定和财产流转快捷的价值趋向。
(二)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从来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大体而言,理论界存在即时时效说、权利外像说、法律赋权说、占有效力说和占有公信力说等几种学说。仔细分析诸种学说,无一都是以占有为表彰权利或本身即为物权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善意取得制度之理论基础。占有是一种事实还是一种权利,学理上有纷争,罗马法认为占有是一种事实,而日耳曼法认为占有是一种权利。目前,学界通说认为占有是一种事实,但法律赋予其公信力,使占有在本权之外披上能与之对抗的公示公信外衣,占有因之而常被世界许多国家的立法赋予其推定权利的效力。因此,即使占有人并非真实权利人,与占有人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并不受其权利瑕疵的影响,仍能够取得财产所有权。也即是善意第三人对占有公信所表征的权利的善意信赖斩断了原权利人的追及效力,此即为善意取得制度建立之原理。《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规定:“对于动产,占有具有与权利证明书相等的效力。”正因为占有因公信力而为权利的表征,受让人与让与人交易无须调查有无处分权。因动产以占有为公示方法,受让人善意予以信赖之故,是以占有公信力是善意取得制度不可或缺之基础。[3]
二、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
对于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学者们多从善意取得之对象即财产角度和财产主体方面论述[4],也即所谓能引起善意取得实际发生的要素或条件[5].此种界定并非很全面,局限于从其外部产生条件即产生善意取得的条件角度论述。笔者认为,从善意取得内在要素和外部构成角度分析,善意取得应包含善意与取得两要件。
(一)善意要件
所谓善意,是指行为人的内在心理活动状况。作为法律概念,善意(拉丁语Bona fides)起源于罗马法中的善意占有之诉(actio publicaca),是产生于共和国末期的一种以时效取得为基础的虚拟的要求返还所有物之诉。[6]善意作为人的主观活动状况,不显于外部,难于度测,但作为法律概念,必须具有可量度性和操作性,也即必须得有具体衡量标准。学理上在确定善意时有“积极观念说”和“消极观念说”。前者认为,行为人必须认为其所为的民事行为合法或行为的相对人依法享有权利;后者认为,只要行为人不知或不应知其行为缺乏法律上的根据或相对人没有权利,即为善意。[7]此二说似执着于一端,不利于把握住善意的实质,而且象“应知”和“不应知”等都是十分难于界定和操作的问题。笔者认为,要把握善意内涵并使之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应善意之主观、客观、时间、主体等诸标准衡之,并作综合认定。
1、主体标准
首先,善意取得之基础行为即交易行为是法律行为,因此行为人须具有行为能力,无相应行为能力者交易行为无效或效力未定,虽然善意取得具无因性[8],不以交易行为有效为必要,[9]但这主要是针对出让人为无权处分而言的。而法律常常规定无相应行为能力者只有在纯获利益时行为才有效。如果认为法定人可行使追认权而使无相应行为能力者行为有效,从而有适用善意取得之可能,显然不能符合善意取得制度设定之目的。因为善意取得为交易迅捷计,切断所有权人的追及力,简化法律关系,如果又延续一追认行为,不利于简捷、便利之制度设计理念;其次,行为人须是具善意的第三人。行为人为交易之目的是为获取所需,填补生产和生活缺漏,而不是用于毁损之目的,因为善意取得制度设计之理念内在地要求物尽其用,维持和增加社会财富。其次,行为人须尽必要注意义务。众所周知,善意取得制度是以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加速财产流转为目的,对出让人之权利瑕疵受让人本不必尽太多注意义务,但如果免却受让人一切注意义务,有悖常理,也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就注意义务的类阶而言,一般分为故意、重大过失、具体轻过失、抽象轻过失等序位。笔者认为,就受让人的善意认定而言,不能有太多注意义务但也不能不尽任何注意义务,在注意义务类阶上,应以重大过失为必要之注意义务,即行为人只有在不具有重大过失情况下,才能认定具有善意。
2、主观标准
主观标准即从行为人(第三人)的主观认知来衡量。也就是以行为人之生理、心理及智力状况为基础具体判断能否知道某种情形。在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之主观标准即是从行为人之生理、心理及智力状况方面具体判断其是否能够知道出让人的权利存在瑕疵。知情而为即具恶意,不知则为善意。当然,主观标准过分偏重医学、心理学,且行为人的智力有高下之别,因而可能导致同一法律关系却有截然不同之结果[10].
3、客观标准
客观标准即从社会一般大众之情形为基础抽象推断行为人在交易时能否知道出让人权利存在瑕疵。对交易中出让人权利之瑕疵,社会一般大众能够知道则行为人所持不知之理由不能成立,行为人不具善意,如果社会一般大众不能知道此情形则推定行为人不知,为交易行为时即具善意。社会一般大众标准的判断尽管比从行为人的主观态度判断更具合理性,但同样存在不易操作的缺陷。片面强调客观标准,难免以偏概全,有失公允。因而也有学者主张具体制度具体规定,但此举易造成法学概念模糊混淆,不利于法学发展。
4、时间标准
善意的时间标准即为在善意取得财产中行为人的善意分野和存续的时间。善意取得中行为人的善意必须得符合合理的时间,善意取得制度才有存续的必要。其实,早在罗马法时,善意的时间标准就有不同的主张。尤里安主张善意取得的效力,只要行为人从出让人处取得财产时具有善意即够(初始善意);而其他一些法学家则主张在发生效力的每一段时间都必须有善意的持续(持续善意),这一主张后为尤士丁尼所采。[11]笔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设立之目的在于稳定交易、促进物之迅捷流通,如果强调行为人之善意持续,行为人取得的财产将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设置初衷。因此,在善意取得上,应以行为人行为时的善意为标准。当然,此处的“行为时”是指财产交付时,并非法律规定的所有权转让行为的逻辑结构都已完成时,因之只要当事人一达成交易意见一致时具有善意即可适用善意取得。所以无论交易行为完成一部分时还是在所有权保留交易中达成交易后得知出让人为非所有人,都应认为具有善意,可以善意取得。
(二)取得要件
1、占有与出让人之处分
(1)占有
善意取得以占有为前提。此处之占有,一为出让人之占有,二为受让人之占有。就出让人之占有言,根据无权处分人占有标的物的依据,可分为委托物之占有和脱离物之占有。占有委托物是基于真正权利人的意思而占有之物,如基于租赁、保管等合同关系而占有他人之物,故原则上得适用善意取得;与之相反,占有脱离物是指非基于标的物真正权利人的意思而占有之物,如盗赃、遗失物等,故原则上不适用善意取得。其法理所在,即在于法律基于公平原则对受让者与原权利人之间进行利益平衡。
就受让人即善意取得第三人之占有言,受让人的占有须为直接占有。因为,善意取得的根据不仅仅单方面基于让与人占有的公信力而使受让人取得其权利,即“以让与人占有的虚像替代实像,俾资保护权利之取得者”[12],而且另一方面也是受让人的占有受到占有的效力保护所使然。准确地说,善意取得的成立既要求让与的相对方眼睛里有“客观”的外观事实值得信赖,也须于交易相对方之外的所有他人的眼睛里也有受让人占有的“客观”存在。否则,何以要求其他人尊重受让人善意取得的所有权,此时的所有权何以具有对世的效力。也正因为如此,德国联邦法院强调“善意取得的权利表征,不在于让与人的占有本身,而在于受让人取得占有的实现”[13].再者说来,善意取得的现代意义非在于实现原所有人不得对第三人请求返还的反射效果,而在于积极地使受让人取得所有权,终极地保护所有权。如果受让人是间接占有人,此时,人们几乎不可能从占有的表象来判断所有权的归属,如允许通过建立间接占有的方法取代实际交付,就会使财产已经发生转移的外部表现消失殆尽[14],善意取得制度的目的也难以达到。所以,占有改定等受让人间接占有方式无有善意取得之余地。
(2)出让人之处分
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是一对关系密切的制度,两者完全不可分割。出让人无权而为处分行为是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当真正的权利人拒绝追认时,如果受让人是善意的,无权处分的合同仍然视为有效,受让人可以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在此,须注意的是与表见制度的区别,善意取得与表见同属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但二者理论基础不同。前者基于占有之事实行为,后者基于之法律行为。而且,表见的法律效力一般是债的变动,而善意取得则是物权的变动。
(3)有偿交易
财产的转移占有,必须通过交易活动来实现,这种交易,是指买卖、互易、债务清偿、出资等有偿法律行为。赠与、继承等无偿法律行为一般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为,[15]首先,从商品流通的整体而言,绝大部分是等价或有偿的,无偿转让只是一种例外情况,在商品流通中所占比例极小,一个虽善意但无偿占有他人财产的人将财产返还,一般来说无碍商品交易的安全和财产的流转。另一方面,从种益角度说,由于第三人在受让时未给予相应的给付,如另将财产返还原所有人,也并不影响他原有的利益。如因保管、搬运等付出了了代价,可向无权转让人要求赔偿。再者,将未付出适当代价的财产据为己有而伤害他人利益,与民法上的公平原则不符,且与传统道德不合。在前苏联及德国民法上,无偿取得的善意第三人也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如1964年苏联民法典第152条规定:“如果财产是无偿地从没有出让该财产权利的人那里取得的,则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要求返还财产。”德国民法典第816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当然,如果无偿取得人再转让的话,对于再受让人来说则可适用善意取得而获得财产权。
2、取得之对象要件
国内学者常以动产、权利、不动产等具体财产作为善意取得的对象要件。[16]而笔者以为,具体财产对象常与社会变迁而互动。就如同采善意取得制度的瑞士和日本,对不动产,瑞士适用善意取得而日本则不适用。而且即使在同一国家,因社会观念变化和科技水平发展,对以前不适用者也可能予以适用,且新的可适用善意取得的物权、权利等财产会不断涌现。质言之,动产、不动产、权利等具体财产对象只是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条件而非构成要件。当然,并非善意取得对象要件就虚位而置。愚以为,法律是为确认和保障权利而制定,任何违法和违背社会秩序的行为都应该由法律给予否定性评价。善意取得之对象也应符合法律的秩序和价值要求。申言之,善意取得之对象要件即为下述二者。
(1)须不违背法律特别保护
根据国情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法律常常考量对一些系关国基的物件给予特殊保护。对于此类特殊保护之物件应不适用善意取得,系所当然。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类:一为国家禁止和限制流通物。此类物件受法律特别保护,不允许在社会上流通或广泛流通,第三人取得该物,无论善意与否,都将因主体不适格而不能取得;二为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财产。私行为不能防碍公行为,国家籍此对此类物件予以特别保护,一旦财产被采取强制措施,无论是权利人还是占有人都不得转让,转让则破坏了法律的强制效力,势必被法律否定,第三人则不能籍善意而取得该项财产。
(2)须不违背公序良俗
善意取得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其具有优越性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因而需要强调公平与道德原则,润滑其运作,以防被滥用。此类情形,也有两类:一为某些具有重大特殊人身性质或感情价值的财产。例如以身份相联系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奖章、手稿或与感情相联系的结婚戒指等,其价值不能单单就其价值量来决定。另有些财产,对他人也许价值不大,但在特定人看来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若仅就财产的物理性质决定其归属,势必不能合情合理地解决问题,达不到定纷止争的目的。[17]依笔者看来,这类含有特殊人身和感情意义的财产具有不可替代性,除非返还,否则无法弥补原权利人之损失,从另一方面看,第三人也没有充足的理由一定要拥有这些财产,他完全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况且我们也不应该牺牲两项权利(财产权和人身权)去满足一项权利(财产权)。所以,只要原权利人能够证明其人身或感情上的特殊性,即可不适用善意取得;[18]二为盗赃物和遗失物。这里要区分盗赃物与遗失物,盗赃物原则上不适用善意取得,其理由在于盗窃是侵犯良好治安秩序的行为,法律禁止盗赃物在社会上流通,且每个人都有对自己财产取得的合法性的注意义务,此种注意义务应高于善意取得之善意标准中注意义务。当然,有原则就有例外,基于经济关系的稳定如盗赃被多次转让和基于维护信用如货币及不记名有价证券等,可例外地适用善意取得。对于遗失物(包括走失的动物),许多国家法律规定在一定条件下,拾得人可取得所有权,[19]在此情形下无适用善意取得之必要。
我国立法并未确立善意取得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有承认。对于盗赃物和遗失物,我国司法实践没有作区分,只要是二者,不论转让几手,所有权人均可要求善意第三人返还。这种作法招致了理论界的强烈批评。对此,笔者认为,良好的治安秩序是社会经济有序发展的保证,保护原权利人之利益有助于减少盗窃,因为盗赃不能顺利转让则对盗者毫无意义;另外,我国是礼义之邦,崇尚拾金不昧的道德精神,遗失物返还原权利人不适用善意取得有助于良好社会风尚的建立。当然,此为原则也不可绝对化,社会现象繁纷复杂,在价值平衡和公平量度下,谨慎地适用善意取得,笔者认为也未尝不可。
三、善意取得之法律性质
(一)善意取得的无因性
善意取得有因与无因在学理上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通说认为善意取得为无因,但也有论者认为,物权无因性原则与善意取得有本质的区别[20].笔者赞成通说。理由为:从起源上看,善意取得制度要早于无因性原则,无因性原则是德国学者从物权行为中抽象而出,目的是为维护物权的公示公信力,维护“社会第三人”与公示物权所有人进行交易的安全性,体现物权的“对世性”。而善意取得制度同样是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的安全,也许二者在历史渊源上没有真正的必然联系,但其本质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从其构成要件观之,二者为种属,善意取得制度可以理解为无因性原则的一个类别,或者说是为剥夺“恶意”第三人的所有权,克服绝对化适用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的弊端,从物权安全保障角度设立的一个制度。故善意取得本身也具无因性。事实上,物权无因性原则过分偏重于对让受人的保护,不合公平原则,晚近,德国民法学界开始检讨无因性理论,认为无条件地适用“无因性”,使其绝对化,必然会得出有悖法理、情理的结论,进而提出“无因性之相对化”理论;[21]而善意取得正是这种“无因性之相对化”理论的表现形式之一。
(二)善意取得的原始性
多数学者认为,因为受让人取得该财产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因而属原始取得。也有少数学者主张,受让人善意取得虽依法律进行,但其终归是从他人手中取得财产权的,因而当属继受取得[22].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笔者认为善意取得是原始取得。如上文所述,善意取得是无因性取得,不以交易行为有效为条件,也即是不受原因行为影响。再者,善意取得是物权的变动而非债权的获得,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同样决定了善意取得的原始性。
四、善意取得的法律效力
善意取得涉及原权利人、无权出让人和善意受让人三者的权利义务,一旦成立,即在三方面产生法律效力:
1、就善意受让人来说,即时取得受让财产的所有权或其它物权,也就是说,从转移占有之时起,受让人成为财产的合法所有人和其他相应物权主体。善意第三人不负向原权利人返还原物的义务。
2、就原权利人而言,其在该财产上的一切权利归于消灭。不仅原权利人的所有权丧失了,而且基于所有权的其他人设定在该物上的他物权,也一并归于消灭,原权利人不能行使物上请求权要求返还原物,而只能依侵权行为要求不法转让人赔偿损失。
3、作为不法转让人,他因侵害了原权利人之所有权或其它权利,其转移该财产所获之利益既无法律上之根据亦无合同作基础,实属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因此遭受损失者。如要其返还之不当得利仍不足以弥补原权利人这损失,则应由不法转让人负损害赔偿的责任。如果不法转让人以高于市场价格或财产实际价值的价格出让,与财产价值相当的所得毫无疑问应当返还,至于高于财产价值的那部分所得应否返还,其法理依据何在?学者间对应予返还持一致意见但对法理依据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视为原权利人对无权处分人处分其财产的追认[23].另一种观点由反对此说,认为在此情形下准用关于无权追认的理论是不恰当的。因为无权的追认,应当有“被人”的追认之意思表示,在此基础上方可认定。而对于善意取得法律关系中的原权利人来说,自始至终不法转让人的转让行为都是违背原权利人意思的,且原权利人从未表示过接受,也没有任何事实足以推定其为接受或追认,原权利向不法转让人主张权利并在以后接受不法转让人的返还或赔偿或其它给付,完全是基于所有权而生之物上请求权,决非什么追认。因此主张,原权利人有权要求取得高出其财产原有价值之利得,实为原所有人因对被转让财产享有收益权之结果,高出部分的所得可以视为原物的孳息,应与原物一并归所有人所有。[24]笔者认为,高出部分所得理应返还原所有人,但其法理依据不在于原权利人对无权处分行为的追认,也不在于把高出部分视为原物的孳息,而在于任何人不能因违法行为而获利之法律基本原则。当然,在具体返还上,无权处分人因其智力或劳动的付出确使原权利人受有利益,衡诸公平,可准用无因管理由原权利人在受益范围内给予无权处分人为此支付的必要费用。
注释:
[1] 周枏著,《罗马法原论》,(上),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 谢在全著,《民法物权论》,(上),1989年版,第263页。
[3] 谢在全著,《民法物权论》,(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4] 王利明、王轶著:《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载《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
[5] 梁慧星、陈华彬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185页。
[6] (意)彼德罗·彭梵得著,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7] 梁慧星著,《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8] 注:后文对此将具体展开论述。
[9] 注:学者间对此问题颇有争论。王泽鉴先生认为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区别及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也应在善意取得制度上适用,故认为不以交易行为为必要,本文赞成此观点。
[10] 曾世雄著:《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81页。
[11] (意)彼德罗·彭梵得著,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12] 刘得宽著:《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13] 王泽鉴著:《民法物权》第二册《占有》,台1996年版,第131页。
[14] (德)罗伯特·霍恩等著:《德国民商法导论》(托尼·韦尔著,英译本,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93页。
[15] 注:以下参见余淑玲著:《善意取得制度初探》,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16] 王利明、王轶著,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
善意取得制度范文第11篇
关键词:遗失物;善意取得;基本利益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9.069
对于遗失物,结合学界的主要观点,其构成要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须为有主物。(2)须占有人丧失占有。即物已不在占有人之管领范围内,区别于一时丧失管领力。(3)须丧失非基于占有人的意思或他人行为。区别于因占有而为的抛弃、让与等行为丧失占有物,以及因他人侵占等行为丧失占有物,这些均不属于遗失物。(4)须无人占有。即遗失物在脱离原占有人与被他人拾得之间有时间间隔,这个期间无人占有。关于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是指动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的动产或登记在其名下的他人的不动产转让给第三人,若第三人在交易时出于善意即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原所有权人不得追夺的法律制度。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07条规定,所有权人有权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但并未规定二年经过后,所有权的归属。从文义上看,对于拾得人和受让人,原所有权人都有权“请求返还原物”;从《物权法》的体系来看,拾得人应送还权利人或送交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如不知道权利人,应招领公告,招领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应当可以得出,受让人无法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也就是其无法通过善意取得来取得物的所有权。
是否采用善意取得制度,关乎所有权与交易安全的价值衡量。支持遗失物能够适用善意取得,最重要的理由是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通说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是为了维护动态的交易安全。动态的交易安全是指法律保护交易当事人基于交易行为所取得的利益,认为在特定的场合下,牺牲真正的权利人的利益来保护善意无过失交易者的利益,以此维护活泼生动的交易活动秩序,促进民事流转。静态交易安全则是指法律保护权利人占有和所有的财产权益,禁止他人非法占有。动态的交易安全确实能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符合社会效益原则。若让民事主体总需要详细调查交易财产的来源,无疑会滞缓交易进程。因此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可以鼓励人们拾遗失物,更有利于发挥遗失物的效用。如果允许对遗失物进行善意取得,则会产生以下3种社会效果。
1 影响所有权人的利益
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效果是,遗失物若被善意第三人受让,善意人即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原所有人只能向拾得人或无权处分人请求赔偿。但是当遗失物经过多次流转后,要找到最初的无权处分人却非常困难。而且倘若前手交易人为恶意占有人,那么只要善意第三人受让则所有权发生移转。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拾得人将所得之物出手,可以再几经转手后便脱离干系。如此对原所有人的保护是更加不利的。即一旦遗失某物,不论遗失人过失与否,其很有可能无法恢复所有权。
2 间接影响交易秩序稳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常遗失物交易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尽管说若对第三人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话,交易主体更需要注意所购之物的权源是否正当,提防权利被追回之危险,不利于交易的便捷稳定,但这也可能为盗赃物的交易带来可乘之机。因为遗失物所占比例小,难以对整个交易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而且交易主体在交易时更谨慎的话,反而会对盗赃物、遗失物等无正当权源的物品的流转起限制作用,有利于减少交易的风险。再者,遗失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并非是放弃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如果利用其他制度而非牺牲遗失人之所有权的代价也可以促进交易安全的话,亦未尝不可。
3 影响传统社会道德的传承
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发挥遗失物的效用,但是却会迎来道德挑战。首先,因遗失物经过多次流转后导致拾得人或无权处分人难以知晓,无权处分行为也难以追责。其次,善意是推定的,只要符合善意取得要件所有权即取得。现今较为认同的说法是善意是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让与人无让与权。一般来说,主观状态较难推知,是否符合善意第三人的标准该如何鉴定?尤其是当遗失物对原所有人而言有着巨大的潜在价值或重大的精神价值时,无权处分人因转让该物所得的钱款往往无法弥补遗失人痛失原物的损失。遗失物一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不但堵死了原所有人回复所有状态的路径,不利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同时也鼓励了人们交易遗失物滋长贪小便宜的心理,与“任何人不得以大于自己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大相径庭。综上所述,遗失物善意取得制度会产生影响所有权人的利益、间接影响交易秩序稳定、影响传统社会道德的传承等不良社会效果,因此我国《物权法》不承认遗失物善意取得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我国物权法对遗失物的相关规定尚有不完备的地方。如何完善相关法规制度,需要在利益衡量中探讨更优制度。在不承认遗失物善意取得的前提下,为了保护拾得人与受让人的利益,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对我国的遗失物制度进行完善:
3.1 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
我国《物权法》将拾得人置于一个较高的道德标准,使其处于义务远大于权利的地位。如果赋予拾得人一定的报酬请求权,不仅符合平等互利的法律原则,鼓励人们拾遗,而且能更好的保护所有权和交易安全。当然,对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应该加以限制,如台湾民法第805条之1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请求前条第二项之报酬:一、在公众得出入之场所或供公众往来之交通设备内,由其管理人或受雇人拾得遗失物。二、拾得人违反通知、报告或交存义务或经查询仍隐匿其拾得之事实。”这些限制都是合理可取的。我国可根据国内的具体情况,设置合理的报酬范围,兼顾立法的简化与当事人的自由空间;同时对负有职责义务或恶意占有的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设置合理的限制。
3.2 改进对善意第三人之有偿回复制度
《物权法》第107条规定了对善意受让人的有偿回复制度,对于有偿回复发生的场所,我国物权法规定为两种即拍卖和向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我国行政机关虽然规定经营者需申请经营许可证,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经营者如小商贩没有经营许可证,但在市场交易中有一定的信誉,从这部分经营者中受让遗失物的善意第三人如果按照我国物权法规定是不能享有费用请求权的。这部分的善意受让人是否就不应该保护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尽管遗失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为了平衡利益,兼顾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对于有偿回复请求权的适用范围应适当扩大,即除了承认通过拍卖或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遗失物可有偿回复,只要在公共市场购得遗失物的善意受让人也可主张有偿回复。
3.3 规定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例外情况
当遗失物为金钱、不记名证券时,这类物品与普通物品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一是作为一般等价物,金钱间并没有差异,一旦遗失几乎不可能证明某张纸币是自己的,基于其特性应允许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以维持正常的经济秩序尤其是金融秩序。不记名证券是不记载所有人姓名,以简单的凭证证明所有权的证券,只要持证券所附的息票,就可以向机构领取股息或利息。其与金钱一样,便于携带且无特征,本身就是财产权利的载体,因此持有人就推定为该证券的所有人。同理,也应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总之,对于拾得遗失物,如果允许拾得人在一定条件下取得动产的所有权,则可以更好地发挥遗失物的效用并保护占有人的权利,但这对物的所有权人是极不公正的,因此我国并未采用此种制度,并不承认拾得人可以取得物的所有权。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拾得人将拾得物转让给善意第三人时,拾得物如何归属?笔者认为,对于遗失物不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为遗失物善意取得会产生影响所有权人的利益、间接影响交易秩序稳定、影响传统社会道德的传承等不良社会效果。但对于拾得人和受让人的利益也应当进行保护,因此可以通过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改进对善意第三人之有偿回复制度,甚至规定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例外情况的方式来保护拾得人和受让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江平.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2]江平.中国物权法教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3]李咏.论盗赃物、遗失物的善意取得[J].时代法学,2006,(6).
[4]史尚宽.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5]王泽鉴.民法物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善意取得制度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善意取得;无权处分;盗赃物
一、善意取得的制度沿革
罗马法时代, 奉行“无论何人不能以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及“发现己物, 我即收回”的观念,无论动产还是不动产的交易领域, 罗马法都绝对保护对物的真正所有权,即使买受人善意地取得无权处分人出卖的标的物, 也不能因此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物之原所有人基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效力, 可以向买受人请求返还。由此可见,罗马法奉行绝对主义的原则,没有善意取得制度。
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来源于日耳曼法。该法区别动产是不基于所有人的意思归他人占有还是基于所有人的意思归他人占有的场合,而规定了不同的法律后果:(1)在动产不基于所有人的意思归他人占有的场合,如被盗物、遗失物,所有人仍享有权利,动产无论转归何人占有,所有人都有权请求返还。(2)在动产基于所有人的意思交于他人时,如租赁物、寄托物,所有人仅有权对其契约的相对人即承租人、受托人请求返还原物、赔偿损失,对于善意第三人,不得为返还原物的请求。在这种情况下,善意第三人虽然取得物的占有权,但未取得物的所有权,所有人仍然享有所有权。在契约相对人从第三人处重新取得物的占有时,所有人仍有权从其相对人处重获物之占有权。这种基于所有人的意思把物交于他人占有对于第三人即不得请求返还原物的原则,后来在传统民法中称之为“占有公信力”原则。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交易安全日渐成为社会商品交换关注的主要问题, 相对于罗马法对所有权的绝对保护观念,日尔曼法的原则更能反映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从立法上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善意取得制度。
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就是继承了日耳曼法的做法,在第932-935条作了详细的规定:出让人出让不属于他所有之物,善意第三人取得其所有权(第932条)。《德国民法典》同日耳曼法不同的是:第一,仿效罗马法的取得实效,以第三人的善意为条件;第二,在日耳曼法第三人不过取得不受所有人追夺的占有,而在《德国民法典》上则由善意第三人取得所有权。《德国民法典》的这些规定, 从法律上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 并对其善意取得的构成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被当代各国视为善意取得制度之典范。
二、我国法律有关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
2007年3月16日, 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该法第106 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 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符合下列情形的, 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3)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 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 原所有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 参照前两款规定。”由此可以看出,《物权法》认为善意取得可以适用于不动产, 这是基于善意人对不动产产权证书上被登记的权利人这一事实的信赖, 也即对于物权公示的公信力的信赖, 在这一点上, 动产和不动产的公示所具有的公信力并无区别。
该法第107 条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该遗失物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 权利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 或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 但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买该遗失物的, 权利人请求返换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权利人向受让人支付所付费用后, 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追偿。”由此看出,遗失物的善意取得是受遗失人的主观认识以及受让人的取得方式的限制的。
该法第108 条规定::“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 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 但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权利的除外。”由此可以看出,除非善意人知情,否则他物权随善意取得的实现而消灭。
三、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完善
物权法的规定使得善意取得制度不仅适用于动产,还适用于不动产的物权变动,这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但物权法的规定又有急待完善的地方:
第一,对于动产中遗失物和遗忘物的善意取得问题,《物权法》第107 条规定为“权利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可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这样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原所有权人一直不知道物品已经遗失的情况下,是否会对原所有权人的所有权进行无期限的保护呢?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保护交易安全,《物权法》应增加一个关于除斥期间的规定,即自物品遗失某个期限后,所有人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的权利消灭。
第二,关于盗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问题,物权法并无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的宗旨就是以牺牲所有权人的利益为代价, 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维护交易安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盗赃物与遗失物相比较只是来源不同,作为动产,占有即为动产所有权的公示方式,善意第三人只能通过占有来推断谁是所有权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等价交易取得盗赃物的所有权,法律应当参照遗失物善意取得的有关规定认定善意第三人取得该盗赃物所有权。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 王泽鉴.民法物权(第二册)用益物权占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善意取得制度范文第13篇
内容提要: 《物权法》第106条确立的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规则,只能解释为主张善意取得的第三人负担证明责任。尽管善意要件的证明有一定难度,但通过间接证据的运用、经验则的援引以及对方当事人事实主张责任的加重,证明该要件是完全可能的。立法论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需要结合诸如进攻者角色、盖然性衡量、证明接近之类的实质性因素,以及公示方式与交易习惯、诉讼程序的实际运作、法律政治考量之类的外部因素进行。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善意取得的成立需要符合三个要件:受让人善意,交易价格合理,不动产登记或者动产交付。三要件中,后两个要件具体而明确,其法律适用相对简单。唯第一个要件,因涉及受让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其证明究竟遵循何种原则和标准,不仅在司法实务中乱象丛生,学说上亦不乏纷争。
(一)实务中的乱象
实务中的混乱状态,从以下几个案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1]
案例1:a将其所有的房子交给侄子d长期居住,而d将该房转卖给了h。a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与h二人之间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无效;h主张其对房产构成了善意取得。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判决书中写道:“被告h辩称自己作为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该房屋归被告d所有,因双方签订协议时,没有向其交付任何有关该房屋的手续,而h又无证据证实该房屋系d所有,因此,h以善意购买该房屋的辩解,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2]
案例2:y与t原为夫妻。离婚后,y向h借款,并以t名下的轿车与h签订了质押担保。后y逾期未返还借款,h请求法院确认其对小轿车的占有构成善意取得动产质权。一审驳回了h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生效后,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抗诉理由之一是原审判决由原告h负担其为善意的举证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再审法院接受了这条意见,却仍维持了原判。再审判决中写到:“本案车辆质押合同的效力仍需衡量h占有该车辆时是否出于善意,即h不知道y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则构成善意取得。在判断h是否为善意,理论上虽应采取推定的方法,应由t对h占有该车辆时的恶意进行举证,但是,本案中的有效证据显示,y向h交付轿车时,机动车登记证书明确载明车辆所有权人是t,即使h不知道y与t离婚之事实,h也仅能推断该车辆系y与t的共同共有财产,在未经t同意的情形下,y不得单独对该车辆作出处分。根据在案证据已可证实h未尽一定程度的注意义务……” [3]
案例3:j与z原系夫妻关系。z在其与j的离婚诉讼期间,将其本人名下的一套房产卖给了w。j诉至法院,称该房产系其与z的夫妻共同财产,要求法院判令z与w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被告则主张其对该房产的占有构成善意取得。在一审过程中,原告j提交了其所属单位的电话本3份,以证明被告w知道原告和被告z是夫妻关系,并可能知道原告和被告正处于离婚诉讼期间。一审法院认为j的证据不足以证明w买房时系恶意,驳回了j的诉讼请求。j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判决书中写道:“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j上诉称被上诉人w购买房屋时并非属于善意取得,对该主张,因其未能举出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4]
反映在上述判决中的有关善意要件之证明的混沌不明之处,大致可以归入两个问题:一是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二是善意要件在具体案件中如何证明。就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第一份判决看上去认为第三人应当就其善意负证明责任;第二份判决明确指出,就第三人的善意,理论上应采推定的方法,由原权利人证明其恶意;第三个案件相对复杂,但从判决书的论述逻辑来看,法官似乎认为共同财产所有人应当就第三人接受财产转让时的非善意负证明责任。[5]就善意要件的具体证明,三份判决也都作出了详略不等的说明。
(二)学说上的分歧
就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者间存在明显分歧。尽管多数民法学者认为,就善意要件的认定应当采取推定的方法,即推定受让人为善意,而由主张其为非善意的原权利人就受让人的恶意或者重大过失负举证责任; [6]晚近发表的两篇专论却持不同观点。[7]在对现行法进行法解释学阐释时,两篇专论一致认为,善意要件应由主张善意取得的受让人(第三人)负担证明责任。不过,就导致这种证明责任分配方法的条文设计是否合理,二文之一却提出了激烈的批评。[8]在该文看来,我国目前的制度设计使得第三人不得不证明实际上很难证明的“消极事实”,这将严重限制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甚至让这一制度的规范目的落空。在逻辑上,这种批评以善意证明的难度否定第三人负担善意证明责任的制度安排,我们看到,这种逻辑在其他民法学者那里也有体现。[9]这提醒我们:在讨论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时,实际上无法回避该要件究竟如何证明的问题。
本文拟就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澄清呈现于上述判决、学说上的混乱和纷争。引言之后,第二部分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分析《物权法》第106条中蕴含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第三部分讨论善意要件的证明可能性及其实现策略;在结束司法论的考察之后,第四部分从立法论的角度分析未来该问题立法需要考量的内外因素;结论部分归纳本文主要论点,并就本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稍作阐发。
二、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法解释学的分析
所谓证明责任,即争议事实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的败诉责任。通说认为,证明责任规范在性质上属于实体法,应当主要从实体法规范中寻求和发现。[10]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与善意要件直接相关的则是该条第一款后句。这样,我国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主要就转化为该条规范的解释问题。
(一)语义解释
立法者一般不会在实体法中直接规定证明责任分配,但通过分析实体法规范的文义和结构,从中发现证明责任规范却是可能的。依其表述方式和规范结构,罗森贝克将实体法规范分为权利形成规范、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妨碍规范和权利受制规范,其中,权利形成规范是从正面规定权利成立的规范,后三种规范则是从反面规定权利消灭或者受阻的规范。由于每方当事人都要主张和证明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规范,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就对权利形成规范负担主张和证明责任,否认权利存在或主张权利消灭、受阻的当事人则对后三种法律规范负担主张和证明责任。[11]这就是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规范说。[12]考虑到规范说直接诉诸实体法规范表达方式的特点,人们有理由把这种学说看作实体法语义解释的一种。[13]尽管规范说已经遭到不少批评,但主流观点大多认可其基本框架,所谓修正只反映在一些细节; [14]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德国、日本,还是我国台湾,规范说都仍是法官司法实务中通行的学说。[15]究其原因,是因为由这种学说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清晰、稳定而统一,易受职业法律人的青睐。[16]因此,这里仍从规范说开始我们对《物权法》第106条的证明责任意义上的法律解释。
考虑到在诉讼中,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一般需要援引权利形成规范作为攻击手段,主张该权利不存在的当事人则要援引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妨碍规范和权利受制规范作为防御手段,这两类规范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基本规范”与“相对规范”来界定。[17]由此出发,关于《物权法》第106条第一句的解读方式就有两种:一种是,将前半句关于追回权的规定看作基本规范,而将后半句看作其相对规范;另一种是将后半句本身看作基本规范。在前一种解读方式中,《物权法》第106条后半句关于善意取得三要件的规定属于(追回权的)权利妨碍规范;在后一种解读方式中,该规定则属于(善意取得的)权利形成规范。但无论采用哪一种解读方式,关于该条证明责任分配方法的结论都是相同的,[18]即主张善意占有的当事人应当就该条列举的所有三个法律要件负证明责任——其中自然也包括善意要件的证明。我们看到,其他学者对《物权法》第106条的解释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9]
(二)体系解释
针对规范说的一个批评是,仅从法律条文的文义和构造中寻求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不合理的。[20]一方面,立法者在设计实体法规范时可能并没有考虑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另一方面,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常常也不是通过单个条文来表达的。仅仅从一个法律条文出发,机械地运用规范说,可能会得出与立法者意图相悖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法。现代法律解释理论认为,法条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一定的“意义脉络”当中。[21]这要求法律适用者在对一个法条进行解释时,除了关注这个法条本身的文法和语义,还要考虑它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与其他法条的关系。[22]在法律的意义脉络和逻辑关系中理解一个法条,这就是所谓体系解释。具体到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规则,上一小节的语义解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的起点,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考察:体系解释是否会带给我们不同的解释结果?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在《物权法》第106条的意义脉络中,善意取得是作为无权处分法律效果的例外情形规定的。[23]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这种体系安排背后的逻辑是:如果我们认为主张无权处分者应当证明其所有权及无权处分,那么作为与这种法律效果对抗的砝码,善意取得的主张人自然应当就其是否符合善意取得的三个要件进行证明。
其次,根据相同概念相同解释的法律解释规则,[24]关于《物权法》第106条中的“善意”概念的解释,应当尽量与民法中的其他法律制度保持一致。我们看到,在《合同法》的表见制度中,同样存在“善意”的概念。[25]就概念内涵,两种情形下的“善意”并没有太大区别;[26]就规范目的,物权法对于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与合同法对于善意相对人的保护亦无本质不同。[27]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权。” [28]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效力,如果没有相反理由,就《物权法》第106条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也应作相同的理解。
(三)目的论解释
法律规范的语义确立了法律解释的起点和边界;在此边界内,体系解释让法律规范的语义更加清晰和丰满,因此不妨看作是一种延伸了的语义解释。而无论语义解释还是体系解释,目的都在于探寻立法者的规范意图。在对规范说进行反思、批判的过程中,已有学者提出应在证明责任的分配基准中引入利益衡量或者实体法旨趣之类实质性考量的观点。[29]姑且不论这类观点是否成立,仅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如果基于规范说得到的证明责任分配结论与《物权法》第106条的规范意图明显冲突,那么这种结论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就《物权法》第106条的立法意图,学者的观点存在分歧。一位学者认为,《物权法》第106条通过将善意要件作为法律成立要件规定的方式将该要件的证明责任加诸第三人,体现了一种优先保护所有权的立法意图。[30]在另两位学者看来,如此规定只会限制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导致《物权法》第106条规范目的——即保护交易安全——落空的严重后果。二位学者更明确指出,不能想当然的以为,物权法作此规定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所有权;这只不过是法条设计不当的结果而已。[31]
在笔者看来,第一种观点更有说服力。首先,将保护交易安全界定为善意取得制度的目的虽然没有错,却不能把保护交易安全看作这一制度的唯一目的。正如拉伦茨所言,“一项法律规则常不只要实现一个目的,毋宁常以不同的程度追求多数的目的。”[32]尽管善意取得制度的确立表明法律在总体上采取了牺牲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而保护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的立场,但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无论何时、何地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因为这一点,多数国家选择了兼顾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与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的“中间法立场”,而非原则上不承认善意取得或者对善意取得的范围基本不加限制的“极端法立场”。我国《物权法》亦不例外。[33]?从这个角度,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规范目的并非单纯保护交易安全这一种利益,而毋宁是在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保护这两种利益当中寻求平衡。[34]
其次,在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相比的意义上,说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偏重保护所有权并不牵强。如前所述,在我国《物权法》中,善意取得是被放在无权处分的法律效果——原所有权人的追回权——之后,作为其例外而规定的。这种立法体例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并不多见,与德国法相关规定更形成了鲜明对比。[35]《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1款规定:“即使物不属于让与人,取得人也因依照第条所为的让与而成为所有人,但取得人在依照该条的规定将会取得所有权时非为善意的除外。”而根据《德国民法典》第929条第1句,“为转让动产的所有权,所有人必须将该物交付给取得人,并且所有人和取得人必须达成关于所有权应移转的合意”。[36]学者指出,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彰显了物权行为有因性的立法原则,《德国民法典》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则以第929条确立的独立的、无因的物权行为逻辑起点。[37]也就是说,第929条确立了“满付与合意两个要件即带来所有权转移之法律后果”的规范,第932条第1款则将这一规范的适用范围从有权处分拓展到了无权处分。与这种明显旨在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例相比,我国《物权法》第106条无疑更倾向于保护所有权。
其实,这种倾向在我国《物权法》中多有体现。比如,我国《物权法》没有规定取得时效制度,对占有制度的规定也相当粗陋。考虑到取得时效以及占有保护均构成对原所有权的限制,现行法对这两类制度的消极态度,可以说进一步反映了立法者对于所有权保护的偏爱。
以上分析表明,《物权法》第106条在规范意图上的确偏重保护所有权,而将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施加给主张善意的第三人,正是这种规范意图的体现。退一步讲,即便我们承认“保护交易安全”是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主要规范目的,第三人负担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的立法例也并不会使这一规范目的落空。从原则上不承认善意取得,[38]到承认善意取得并且将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施加给原所有权人,我国《物权法》第106条的设计位于中间。这种立法例与那种将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施加给原所有权人的立法例相比,差别仅仅在于第三人善意与否真伪不明的那一部分案件;对于那些能够证明其善意的第三人而言,交易安全利益仍然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四)比较法解释
比较法不能作为解释现行法的直接依据,但可以为我们理解现行法提供间接参考。实际上,在对一种法律制度尚未形成稳定的法解释学共识之前,引入比较法资源经常是法律解释者不得不为的选择。我们看到,民法学者以推定解释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无疑受到了日本和我国台湾民法学著作的影响; [39]而徐涤宇、胡东海对现行法的批评,则是因为德国法提供了不同的立法例。[40]比较法上的这些反例,是否可以成为本文解释结论——特别是基于规范说的语义解释结论——的依据?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完全否定的。
首先,日本法、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不构成对上文分析的反驳。一个不言自明的逻辑是:作为一种确定证明责任分配基本原则的理论学说,规范说仅适用于法律没有就证明责任分配作出规定的场合。[41]《日本民法典》第192条规定,“通过交易行为平稳且公然开始占有动产的人,在善意且无过失时,即时取得可在该动产上行使的权利。” [42]表面上看,善意在这里似乎是权利成立规范的要件事实。但问题是,就善意的成立,《日本民法典》第186条第1款已经规定:“占有人,可推定为以所有的意思、善意、平稳且公然地占有之人。” [43]《日本民法典》第186条实际是一条假推定之名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44]立法者通过这个规范,将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直接分配给了就占有人的善意提出异议的人。由于第186条的存在,规范说被排除在了第192条的解释之外。差不多相同的规定也出现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条。[45]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台湾民法学者的论述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总是被从反面、以恶意证明的方式赋予原权利人。[46]
其次,德国法同样不构成对上文分析的反驳。就《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1款,拉伦茨认为,“在有人对取得人的所有权提出疑问时,取得人只需要证明根据第929条所有的让与行为,而毋需也证明他在取得所有权之时是善意的。对取得人的所有权提出疑问的人,才必须对取得人的非善意提出证明。” [47]按照罗森贝克的理论,通过“……除外”这样的表达方式,立法者赋予第932条第1款以权利妨碍规范的性质。[48]主张该规范以妨碍基于第932条前半句主张善意取得者,需要就该规范负担证明责任,即证明取得人为非善意。[49]与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将善意要件作为取得人的权利成立要件规定相比,德国法第932条代表了另一种立法例。但这两种立法例都可以被纳入同一种解释工具,即规范说。
最后,上述立法例都可以在其本国善意取得制度的规范目的中得到解释。关于善意取得的规范目的,上一节已有简单涉及。这里以德国法为例,提供进一步的论据。在德国民法典第一立法委员会拟定的草案当中,善意的证明责任其实是被交给取得人的,因为当时的起草者认为,占有的公信力无法与不动产登记相提并论。但在第二次立法委员会那里,交易安全利益压倒了所有权保护利益。[50]结果,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意图在证明责任环节也获得了优先考虑,立法者将善意要件的规范形式由之前的权利形成规范改成了现在的法律妨碍规范。[51]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在立法上,将善意要件作为善意取得的权利成立要件和将其作为权利妨碍要件来规定都是可能的;第二,选择哪一种立法模式,起决定作用的是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就立法技术的运用而言,两种立法模式并无不同,即都是通过规范表述方式的选择,达到在当事人之间妥当配置证明责任的目的。
综上所述,尽管日本法、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和德国法关于善意要件证明责任分配的立法与我国《物权法》不同,但这只是各国(地区)善意取得制度不同立法意图的反映。一旦引入立法意图的因素,比较法上的不同立法例就变得可以理解,也不再有优劣之分。上述立法例不仅没有证伪,反而从方法上进一步证成了前文关于《物权法》第106条的解释结论。
(五)普适的德国法
徐涤宇、胡东海二位先生的《证明责任视野下善意取得之善意要件的制度设计——〈物权法〉第条之批评》一文(以下简称徐文),从证明责任角度对《物权法》第106条提出了激烈批评。徐文从《德国民法典》第932条出发,认为该条确立的善意要件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在比较法上具有普适性;反观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则由于立法者缺乏通过实体法分配证明责任的意识,有规范目的落空之虞;这一缺陷已经无法通过解释论弥补,而必须借助“超越法律的续造”来补救。[52]就该文部分观点及论据,前文已有零星反驳,此处不赘。唯“德国法的普适性”一点,因在徐文中具有方法论的基石意义,仍需进一步澄清。
首先可以指出的是:即便最粗糙的比较法考察,也不能得出《德国民法典》第932条具有“普适性”的结论。在大陆法系,日本法、我国台湾地区法、瑞士法的法条结构与德国法均不相同;在英美法系,美国法更是提供了完全相反的判例。[53]不需要更多的考察,对于“德国法具有普适性”的判断,有限的几个反例就已经足够了。更重要的是,即便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采用了德国法的立法例,因此在概率的意义上姑且承认德国法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性”,但这一判断对我们评估中国法也不具有直接的意义。立法者面对的社会情景不同,需要达到的立法目的不同,为此可以选择的立法技术也不同。评价一个国家的某个立法妥当与否,只能看这一立法在立法目的的设置上是否顺应了这个国家社会、经济的需要,以及立法者是否通过立法技术的运用,妥帖地实现了这一立法目的。从这个角度,仅仅因为德国法的“普适性”而批评中国《物权法》第106条设计不当,这本身就是武断的和不公正的。
在笔者看来,徐文的关键问题在于:发现了德国法与中国法的区别,却没有深入分析导致这种区别的原因,而是将其简单归咎于立法者的疏忽;接受了德国法学者关于《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的分析,却没有看到,这种分析只是对德国法的法解释学阐释——而这种阐释恰恰不具有“普适性”。[54]法解释学的终极目的是探寻本国现行法的真义,为做到这一点,只能从本国法规范的语义出发,参考本国法的体系和逻辑,探寻本国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德国学者如此,中国学者也应当如此。从这个意义上,德国法的规定,以及对这些规定的评注都不能成为解释、批评中国的直接依据。而本文迄今为止的分析表明在忠实反映立法者规范意图这一点上,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做得并不比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差;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未发现启动“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的充分理由。[55]
三、善意要件的证明之道
依前所述,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物权法》第106条第一款只能解释为第三人负担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不无争议的是,善意要件是否能够证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又应通过哪些方法来证明?这类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圆满回答,第一节的分析也许难免遭遇“概念法学”的非议。
(一)无法证明的善意
一个经常看到、但却很少得到充分论证的观点是,作为一种否定性事实,[56]善意要件很难从正面被证明。比如,叶金强认为:“由于第三人不知真实物权状况为一消极事实,要求第三人证明其不知,在逻辑上难于成立,而且占有具有推定力,第三人可以将占有人视为真正权利人,所以,在无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真实物权信息的情况下,即应推定第三人为善意。可见,原权利人如果要否定善意取得的构成,需要举证证明第三人知道事实真相。” [57]陈华彬认为:“因无过失为常态,有过失为变态,且无过失为消极事实,依民事诉讼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占有人应无须就此常态与消极事实负举证的责任。” [58]徐涤宇、胡东海认为:“受让人若要成功证明自己的善意,却并非易事。此所谓善意是指不知让与人无处分权而言。因而,‘善意’是一种否定性事实或消极性事实。此类事实,虽非证明责任理论中的消极事实说认为的‘消极事实不能证明’,却也是很难证明的,加之‘善意’是一种主观内在状态,其证明难度更大。” [59]甚至郑金玉也认为,由第三人自证其善意,将会给司法实践带来难题。[60]在笔者看来,这类观点的价值主要不在法解释学,而在法政策学。在法解释学层面,如果上文的分析成立,那么,即使真如论者所言——善意要件很难被证明,解释者也只能认为,立法者本来就是要通过证明难度的增加而将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限制在很小的范围。[61]但在法政策学层面,如果这种论点成立,立法者在设计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规则时就不应对其视而不见。但是,善意要件真的无法证明吗?或者至少,善意的证明难度要远远大于恶意的证明吗?无论从理论还是实务的角度考察,对这些设问的回答看上去都是否定的。
首先,作为这一论点理论基础的否定事实说,早已被证明为是不妥当的。否定事实说认为,只有肯定的事实能够证明,否定的事实是不可能证明的。这一学说早已被德国法学家抛弃。德国研究证明责任的所有权威学者——从最早的罗森贝克[62],到晚近的莱波尔德[63]、穆泽拉克[64]、普维庭[65],都一再指出,否定事实说原则上是错误的。肯定事实与否定事实的区分,从来不是决定证明责任分配的关键因素,甚至不是重要因素。即使是立法者经常会在立法上避免否定事实的证明,也不能改变这一结论。[66]在英美法系,该理论自十九世纪末就被学者抛弃。[67]尽管有判例从“否定性事实不易证明”的角度分析证明责任的分配,但正如学者指出的,在这些案件中,决定证明责任分配的关键因素其实是公共政策考量。在普通法中,同时大量存在要求当事人证明否定性事实的例子;就这类事实的证明,并不存在一个原则性的标准。[68]在我国,学者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69]在笔者看来,否定事实说之所以会被抛弃,主要是因为否定事实与肯定事实的划分非常模糊。[70]部分地因为这一点,否定事实是否难以证明,就成为一个不能一概而论的问题。一个事实要件究竟是从否定的方面更容易证明,还是从肯定的方面更容易证明,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71]
其次,具体到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正面证明善意未必比从反面证明恶意更难。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是指第三人的“不知情”,即不知道并且不应该知道处分人对于财产没有处分权;所谓“恶意”,则是指第三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处分人对于财产没有处分权。陈华彬先生认为:“占有人是否以善意加以占有,因属其个人内心之事,难以举证证明,故在善意占有抑或恶意占有的事实不明时,推定为善意占有。” [72]?这一论断的前半句并无不妥;但问题在于,“恶意”同样是“个人内心之事”,没什么证据表明证明“恶意”比证明“善意”容易。实际上,无论善意证明还是恶意证明,都必须运用一些特殊的证明策略才能完成。[73]既然如此,善意证明的难度如何就能成为善意要件证明责任分配的依据呢? [74]
最后,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告诉我们,证明“善意”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说以上分析只是理论上的“假说”,那么中国法官的实践则为这种“假说”提供了大量证据。在《物权法》颁行后的审判活动中,中国法院频繁作出认定善意要件成立的判决。只需稍举数例: [75]
1、“白存忠持有宅基地使用证书,该使用证书上非原告名字,马正省征询了村委意见,签订协议时包括小队长在内的多名中间人参加,故马正省购买白存忠的房屋时没有恶意,是善意的。” [76]
2、“第三人李某运作为房屋的卖方持有原告韩某的房产证、身份证复印件、房屋钥匙,与被告王某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该房屋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被告王某购买了该房屋,并支付了合理对价。房屋买卖协议签订后,被告王某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已数年,原告韩某一直未提出异议。第三人李某运虽无权处分该房屋,但被告王某有理由相信第三人李某运有权处分。被告王某购买该房屋是善意取得。” [77]?
3、“被告候某、万某间系夫妻关系,被告候某十多年来对其房产不闻不问,其漠视自己所有权的行为,显然有悖生活常理。被告朱某有理由相信被告候某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房已出售他人,被告万某也具有出售房屋的权,被告万某实施的出售房屋的行为,系被告候某、万某的共同意思表示。因此,被告朱某善意有偿取得房产,其合法权益应予保护。” [78]
4、“因涉案财产原所有权人群翊公司在设定所有权保留时未依法进行登记,亦未通过其他方式向合同外第三人进行公示,合同外第三人雅新线路板公司不可能知晓设备出让人系无权处分,其受让财产应属善意。” [79]
5、“在本案中,藏东菊将五间房作价8000元抵偿给了王国忠,是藏东菊的真实意思表示,王国忠接受该五间房屋予以折抵藏东菊的欠款是善意的,且藏东菊已经将该五间房屋交付给了王国忠,王国忠即取得了该五间房屋的所有权。” [80]?
6、“本案中,被告袁铁旦取得争议房屋的权利前,出卖人在此长期居住,原告却没有在此居住,被告袁铁旦和出卖人经协商达成协议,袁铁旦支付了合理对价,出卖方交付了房屋的相关手续,在被告袁铁旦居住后,又自建了房屋,厂方没有提出异议,原告徐其岭事前事后经过该房,明知后也未提出异议,被告袁铁旦有理由相信出卖人对该房屋有处分权。” [81]
7、 “本案被上诉人张开欣于2005年12月4日经中介公司居间介绍,凭当时的房产现有资料(经济实用房的申购人、购房合同签订人均为薛兴国)直接与薛兴国本人签订‘房产买卖协议书’及‘补充条款’。交易时购房合同及购房发票原件交付张开欣保管,房产也交付张开欣入住,张开欣主观上显然是善意的。” [82]
8、“原告张晓娜购买该房屋时,是经中介公司中介购买,购买时诉争房屋登记的原产权人为袁铁路且登记上未显示有异议登记,故作为受让人的原告在购买该房屋时是善意的。” [83]
尽管上述判决就善意证明的阐述详略不等,将它们放在一起,却足以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善意要件的证明难度并没有给中国法官带来太多困惑。尽管笔者没有就善意取得的司法判决做一个系统的统计分析,尽管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大量认定“善意”不成立的案件,但笔者相信,上述判决对于打消那种“因为善意要件证明责任设置不当而导致《物权法》第106条规范意图落空”的担忧,已经足够了。
(二)善意要件的证明策略
作为一种涉及人的主观认知状态和心理状态的事实要件,善意的证明与一般客观事实的证明的确有所不同。这本是不言自明的。笔者相信,不会有哪个法官会用认定一般客观事实的策略和方法来对善意要件进行调查和认定。但这里仍打算对善意要件的证明策略稍作探讨。因为,这种讨论不仅可以为上述结论提供进一步的支持,而且对类似证明难题的解决也具有方法上的参考意义。
1、间接证据的运用。如前所述,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是指“第三人不知道并且不应当知道处分人对财产无处分权”。也就是说,主张善意取得的第三人不仅需要证明其“不知情”,而且需要证明其“不应当知情”——即“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情”。[84]其中,前者涉及第三人在交易时的主观认知状态;后者则是法律对第三人不知情的原因的评价,在实践中经常可以转化为第三人是尽到必要注意义务的问题。[85]?
在证据法理论上,知识、意图、意愿这类存在于人类精神领域的事实被界定为“内在事实”,而与存在于外部世界、能够被人类通过五官感知的“外在事实”区别开来。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对于后者,直接证明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对于前者,多数时候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来证明。[86]与善意要件相关的“知情与否”就属于内在事实。对该事实,严格意义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一种,即第三人本人的声明。而考虑到第三人在诉讼中所处的地位,这种声明对法官事实认定的意义非常有限。第三人为证明其“不知情”,还要就此声明进行更具体的事实主张和证据提出。比如,第三人可以提供证人证言,证明他曾经在特定场合谈到过他要与出卖人进行交易,并且从言辞中可以得知他并不知道该出卖人对财产没有处分权。更常见的情形是,第三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出卖人在交易中展示的权利表征让他有理由相信其对财产有处分权。比如,对于不动产,出卖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中确实显示了其本人姓名;对于动产,出卖人对财产的占有在具体情景中看上去是持续、稳定的。第三人为证明这些事实提供的证据,在性质上都属于间接证据。对这类证据,法院首先应当审查其关联性,即审查间接证据与证明对象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对那些经过审查,被认为对证明主题的确有效力的间接证据,法院应当从整体上进行综合判断。也就是说,要将这些证据作为一个整体,看它们是否足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即第三人的不知情。[87]
为了证明“无重大过失”,第三人应当就交易的主体、时间、地点、内容和过程提供信息,以证明他在当时的情景中,已尽到了一般人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88]在逻辑上,“无重大过失”的证明发生在“不知情”的证明之后,并以前者为基础。但在实践中,对这两个证明对象的证明经常是不分彼此、交织进行的。比如,当第三人就交易场景以及他在交易中的表现提供证据时,这些证据一方面是证明其“无重大过失”的直接证据,另一方面,又不妨看作证明其“不知情”的间接证据。
上述思路对中国的法官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 [89]其中体现的证明逻辑,与上文的阐述并无实质区别。
2、经验则的援引[90]。所谓经验则,简单的说,就是“从经验中归纳得到的关于事物的知识或法则”。[91] “在经验则这个概念下,人们可以想到的除了通过观察具体事件得到的一般生活经验,还有交易生活、商业、贸易,甚至艺术、科学和技术中的一般性规则、原则和知识。” [92]在善意要件的认定过程中,经验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对于善意的证明经常只能通过各种间接证据来完成。比如,在关于二手车的争议中,第三人提供证据证明:他是在法定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上与出卖人完成交易的;他之前并不认识出卖人;他就该二手车支付了合理的对价。这些证据本身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直接证明第三人是善意的,但将它们放在一起,却可以初步证明这一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官在这里运用了一个经验则——即:在上述情形下,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出卖人对财产有处分权。在上文引用的第4个判决书中,法官也援引了一个经验则:对于没有登记并且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向社会公示的所有权保留,合同外的第三人不可能知道。可见,在间接证据与证明结论——第三人的善意——之间,经验则实际充当了一种桥梁或者纽带的角色。
应该注意,不同类型的经验则,其盖然性并不相同。有些经验则只具有较弱的盖然性,只能作为法官对案件事实进行综合判断时的参考;而另一些经验则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构成了“典型生活过程”,以至于可以直接发生表见证明的效果。[93]另外还要看到,经验则是对证据与争议事实之间关系的一种盖然性说明,就这种说明,对方当事人总是可以通过反例来。比如在上述第四个案件中,原权利人就可以提出第三人实际上知道处分人没有处分权的事实,来反驳“对于没有登记并且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向社会公示的所有权保留,合同外的第三人不可能知道”的经验则。
3、对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义务的加重。[94]在善意要件的证明过程中,第三人并不需要就其主张的所有间接事实进行举证;对于对方没有反驳的间接事实,法官毋宁是直接确认为真。[95]而权利人对第三人主张的间接事实,也不能是简单地否认了事。考虑到善意要件本身的特征,如果简单地否认声明就足以第三人的事实主张,那么法官几乎很少能对争议事实形成心证。善意要件证明的特征要求权利人在否认第三人主张的间接事实时,必须提出足以该间接事实的相反事实。举例言之,如果第三人主张其不认识处分人,这时权利人就不能简单地反驳说,“第三人其实认识处分人”。他必须就第三人与处分人之间的关系提出更加具体的事实。比如他可以指出,第三人与处分人曾在某一特定时期同学。又例如,在对上文判决4中提到的经验则进行反驳时,权利人就不能仅仅说,“即使没有公示,第三人也有可能知道其所有权保留的事实”。这一陈述尽管在理论上完全成立,但作为对本案证明的反驳却是不够的。为了动摇法官的内心确信,他必须提出能够表明第三人知道处分人无处分权的具体事实。一旦权利人提出了足以反驳第三人事实主张的具体事实,接下来就应由第三人就这些事实的不存在进行举证了。第三人的证据只要能够达到上述反驳事实的程度,就算完成了证明。[96]
就证明难题的解决,还能想到一些别的策略,比如法官的事实推定、证明标准的降低,等等。一来为篇幅所限,二来考虑到这些策略的适用范围与前述三种策略多有重合,其概念内涵亦不乏争议,这里不拟展开讨论。之前的阐述已经表明,尽管善意的证明有一定难度,但现代民事诉讼早已发展出一系列解决这类证明难题的策略。只要法官妥善运用了这些策略,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就第三人善意与否获得心证的。需要特别警惕这样一种简单化的思维:一旦将证明责任施加给了一方当事人,这一方当事人就将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出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对方当事人则可以高枕无忧。不仅法官不会认同这种思维,从学理的角度,以这种方式理解证明责任显然也是浅薄的和片面的。实际上,对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法官而言,[97]证明责任规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环节:一是在事实调查开始时,由哪一方当事人首先针对争议事实提出证据;二是在事实调查程序终结而法官无法对争议事实形成心证时,判决哪一方当事人败诉。而在这两点之间的漫长诉讼过程中,法官不仅可以,而且应当运用多种手段,从双方当事人那里尽可能多地获取相关信息,以便对争议事实形成心证。对于法官的审理活动而言,作为真伪不明之时的裁判规则的证明责任规范固然重要,但为了避免适用证明责任规范而发展出来的诸种证明策略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四、立法论上需要考量的若干因素
此前的论述已表明了笔者对《物权法》第106条的基本评价,那就是:从司法证明的角度,这一条文是可以解释的,也是可以适用的。但这只是一个解释论上的中立判断,它并不意味着笔者“喜欢”这个条文,更不意味着笔者否认这一条文有被修改的可能。这种可能性是否,以及何时出现,取决于立法者的法律政策考量。当然,立法者的法律政策考量也应当有章可循。就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立法,以下两类因素是立法者必须关注的。
(一)影响证明责任立法的实质性因素
按照德国学者的观点,法官对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运用只能从实体法出发,而不能在此过程中掺入实质性考量。因为那样的话,法官实际上篡夺了立法者的权力,法律的安定性将荡然无存。[98]但是,对于立法者而言,进行这类实质性考量却是可能的,有时候甚至是必要的。按照普维庭的归纳,这类实质性原则主要有:抽象的盖然性衡量、证明接近、社会保护思想、宪法上地位、进攻者角色、危险增加、消极性证明,等等。[99]不过,对于善意要件的证明,真正需要思考的只有进攻者角色、盖然性衡量和证明接近。
1、进攻者角色。进攻者角色原理的基本要求是,要求改变现状的当事人应当就其主张的事实负担证明责任。在普维庭看来,这一原理在各实质性依据中具有中心地位,因为它与保护占有、权利安定性、社会秩序保护、对现存事实状况的保护和禁止私力救济等基本法律价值密切相关。[100]实际上,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理论通说的规范说与进攻者角色原理基本上契合;或者换句话说,进攻者角色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规范说的实质性依据。[101]表面上看,在善意取得制度中,进攻者角色理论有利于支持让原权利人负担证明责任的观点。不过,这一论辩的价值非常有限。就善意取得所涉及的财产,在不同时期实际存在两个不同的占有:一个是原权利人基于所有权的占有,一个是第三人基于无权处分的占有。固然,基于第三人的视角,我们可以说原所有权人处于进攻者角色;但基于所有权人的视角,又不妨说第三人处于进攻者角色。进攻者角色原理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视角。起决定性意义的只能是立法者的价值判断,或者说,是立法者对所有权保护和占有保护这两种利益进行衡量的结果。
2、盖然性衡量。盖然性衡量理论要求立法者在配置证明责任时,衡量真伪不明时事实“为真”与“为伪”的概率,并据此制定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比如,就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立法者就应当衡量,在现实生活中,究竟第三人为善意的概率更大,还是其为恶意的概率更大。如果第三人为善意的概率更大,那么在真伪不明时判原权利人败诉看上去更具合理性;相应地,在立法上,将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原权利人就是较为妥当的选择。由于引入了概率概念,这一理论比较具有科学性的外观,因此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但是,这一理论对于立法者的参考价值却很有限。主要问题在于对于一个要件事实真伪不明之时“为真”或者“为伪”的概率,实际上很难衡量。以善意要件的证明为例,这一衡量首先涉及人们对于当前社会诚信状况的判断。如果一个社会的诚信状况较好,人们也许可以说,由原权利人证明第三人恶意是较好的选择;反之,则由第三人证明其善意更优。但是,这种判断很大程度上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究竟哪些案件会被认定为“真伪不明”,最终取决于法官的判断;而法官的判断又受到其证据调查能力、裁判习惯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将所有这些因素纳入盖然性衡量的范畴,看上去已经超出了这一理论所能容纳的范围。因此我们看到,就德国民法典第932条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德国学者通常认为,其实质性依据并非盖然性衡量,而是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即对占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102]??
3、证明接近。按照证明接近原理,立法者在设计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时,应当尽量让距离证据较近的一方当事人提出该证据。基于有利于查清案件真实和节省司法资源的考量,证明接近原理有其合理性,并且在现代产品责任法、医疗责任法等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体现。不过,作为一种主要着眼于克服证明困难的实质性依据,证明接近理论的意义不宜夸大。为了克服证明困难,现代证据法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和理论,比如间接证明、表见证明、对方当事人的事实提出责任,等等。由于这些策略的存在,许多时候,即便某些证据不在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一方,也不影响其对相关要件的有效证明。在证明困难的情况下选择这类策略,而不是根据证明接近原理重新设计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因为这些策略大体都可以归入“证据评价”的范畴,其运用并不会改变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人们实在有太多理由坚持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比如,前文刚刚提到的进攻者角色原理。进攻者原则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即使证据不在我这一方,但如果我希望改变一种法律关系的现状,通常情况下我就要负担证明责任,因为我不能让他人无端地忍受讼累。因此,尽管证明接近原理表面上有利于支持现行法——即有利于支持让第三人负担证明责任的立法例,但我却不愿强调这一论据。
(二)影响立法者利益衡量的外部因素
以上分析几乎都指向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最终决定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证明责任配置方式的只能是立法者的利益衡量。换句话说,就是在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保护这两种利益里面,立法者更偏重于保护哪一种利益。事实上,这也是笔者在之前的法解释学分析中反复强调的观点。但立法者生活在一定时空之中,其价值判断从来不能超脱于其所处的历史与社会之外。与上一节阐述的实质性因素相对,这种来自历史和社会的变量构成了影响善意要件证明责任配置的外部因素。这里不可能全面考察这些因素,只挑出三个方面略加阐述。
1、公示方式与交易习惯。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根基在于物权变动公示的公信力,一般而言,物权的公示方法即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有学者指出,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的公信力存在重大差别:对于不动产,只要受让人信赖了登记,就是善意的,除非其明知登记错误,否则无需考虑交易环境等因素而对于动产,由于占有的公信力较低,受让人就不能仅仅凭借占有的事实当然地相信处分人具有处分权,因而在判断受让人是否具有信赖利益时,还必须考虑其他一系列因素,比如价格的高低、交易的具体环境、交易的场所等。[103]也就是说,基于不同的物权公示方法,关于受让人善意的证明要求也会有所不同。为了弥合这种差别,立法论上似乎可以考虑:对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要件,由原权利人从反面证明受让人为恶意;对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要件,则由受让人从正面证明其善意。[104]
但上述建议很大程度只是理论演绎的结果,它在实践中的合理性,还要结合当前中国民间的交易习惯进行具体分析。比如,我们看到,在我国农村地区,不进行不动产登记的房屋买卖大量存在。基于这样一种现状,立法者如果只是简单强调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结果就有可能导致(在具体情境下)有失公平的案件处理结果。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在考量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方式时,对民间交易习惯的调查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诉讼程序的实际运作。如前所述,实体法关于一个事实要件证明责任分配方式的不同选择,反映了立法者对对立利益进行衡量的不同结果。但是,即便是同一种证明责任的立法例,其在各个国家的实际效果也未必相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证明责任分配方式只决定了真伪不明之时败诉风险负担的大致框架,而在这个框架之内,这种风险究竟以多高的频率出现,很大程度却取决于一个国家诉讼制度的运作情况。比如说,在一个当事人提出证据的手段匮乏,法官化解各种证明难题的能力不足的诉讼环境中,证明责任负担对当事人而言就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而在这两个因素都相对乐观的情况下,证明责任负担带来的压力则会小很多。另外,影响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际效果的还有法官的裁判习惯。比如,法官究竟是倾向于作出证明责任判决,还是倾向于回避作出证明责任判决?在后一种情况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实际意义相对较小,因为它被适用的频率本来就很小;而在前一种情况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影响则较大。考虑到善意本身就是一个主观性较强、证明起来有一定难度的事实要件,立法者在考量其证明责任分配方式时,对上述因素不能不察。
3、法律政治的考量。法律不止是对既有社会生活状态的确认和保障,在许多时候,它还承担着引导公众的行为方式,塑造某种立法者期望的社会生活状态的功能。因此,在一定时期,法律有可能成为立法者推进社会变革的手段和工具。如前所述,现行法对所有权给予更多保护,而对交易变动施加了较多限制。就此制度安排,不妨认为,其背后隐藏着一种“目前社会上的交易行为不尽谨慎”的预设。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前提性预设被修正甚至抛弃都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目前这种制度安排对于经济生活的实际影响是:财产所有人可以以较为随意的方式行使所有权的权能,而受让人则需要在交易中多加谨慎。假如将此看作一种法律政治的考量,这种考量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同样有可能朝着有利于受让人、有利于交易便利的方向变迁。立法者在对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进行配置时,应当对此有着清醒的自觉。
五、结论
经由第二到第四部分的论述,就引言提出的问题,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1、《物权法》第106条确立的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规则,只能解释为主张善意取得的第三人负担证明责任。
2、通过间接证据的运用、经验则的援引以及对方当事人事实主张责任的加重,善意要件是可以被证明的。
3、立法论上关于善意要件证明责任分配的讨论,需要结合诸如进攻者角色、盖然性衡量、证明接近之类的实质性因素,以及公示方式与交易习惯、诉讼程序的实际运作、法律政治考量之类的外部因素进行。
此外,本文附带批评了徐涤宇、胡东海二位先生关于善意要件证明责任分配的分析。在笔者看来,尽管徐文的材料、观点均不无偏颇,其最致命的缺陷却在方法。将一个外国法上的命题“普适化”,拿来解释和批评中国法,这种研究方法在中国法学界相当流行。关于这种方法的谬误,前文已有揭示;至于此种谬误的避免,则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在分析中国法时,坚守作为解释者的中立立场。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行法在周密与精致程度上与德国、日本,甚至我国台湾地区法制相比,仍有明显差距;这种差距,又因为上述国家和地区相对丰富的法解释学研究成果而被进一步放大。但是,一种外国法律制度在逻辑周延性、体系自洽性上的优势,并不能成为我们放弃现行法的理由。正因为我们的现行法相对粗糙,才更需要法律人去悉心呵护。只有法律人怀着一种“护法者”的敬畏之情,以最大的耐心去为现行法探寻可能的解释和适用空间,这法律才能在我们的手中获得生机。
其次,在批评中国法时,更多关注中国法的运作实践,而不是仅仅关注中国法与外国法的文本差异。文本比较只能说明有限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法律文本相对简单、粗陋的背景下,拿其他国家成熟的法律制度和理论来衡量它,很容易就得出关于我国法的负面评价。但这种评价并不公正,也没有太大意义。一方面,文本比较揭示的“问题”在实践中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另一方面,法律文本的粗陋可以通过解释者的努力弥补,而这正是法学家的职责所在。
注释:
[1] 为节省篇幅,案情介绍以反映案件主要争议为限,判决书引用则限于与善意要件的证明直接相关的部分。三份判决均来自“北大法宝”,有兴趣的读者自可下载阅读全文。
[2] 判决书全文,见《(2009)郑民初字第963号判决书》。
[3] 判决书全文,见《(2010)浙杭商提字第1号判决书》。
[4] 判决书全文,见《(2010)郑民二终字第537号判决书》。
[5] 在实务中,法官很少使用“真伪不明”的字眼,对于肯定之外的事实判断,一般只是笼统表述为“证据不足,予以驳回”。从理论上,这意味着法官可能就该事实形成了为“否”的内心确信,也可能是该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另一方面,中国现行法上的“举证责任”,与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上的“证明责任”或者“举证责任”概念并不完全相同。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就上述判决究竟采纳了哪一种证明责任分配方案,实际上很难准确判断。这里的归纳是笔者细读三份判决文本之后得出的结论,其中,法官的表达方式和论理逻辑尤其受到了重点关注。笔者深知,这种归纳不完全精确,但为了研究的开展,眼下也只能满足于这种只具有大致可靠性的判断了。
[6] 比如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267页;叶金强:《论善意取得构成中的善意且无重大过失》,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5期;陈华彬:《民法物权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页;程啸:《论不动产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释义》,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尽管上述论著中的某些发表在《物权法》颁布之前,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论著的作者在《物权法》颁行后改变了观点。
[7] 参见徐涤宇、胡东海:《证明责任视野下善意取得之善意要件的制度设计——〈物权法〉第106条之批评》,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4期;郑金玉:《善意取得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研究》,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6期。
[8] 参见上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
[9] 参见前引[6],叶金强文;前引[6],陈华彬书,第550页。
[10] leo rosenberg,die beweislast auf der grundlage des bürgerlichen gesztzbuchs und der zivilprozessordnung,5.aufl.münchen:c.h.beck, 1965,s 82;hans prütting,gegenwartsprobleme der beweislast,münchen:c.h.beck 1983,s 20.;adrian keane,the modern law of evidence,butterworths,1996,p 69;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页(该章为李浩教授撰写)。
[11] 上引[10],leo rosenberg书,第100页以下;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理论与制度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0页。
[12] 通说有时又被称为法律要件分类说,比如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笔者认为,尽管法律要件说与规范说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但代表性论述的内容基本一致。因此,这里不对这两个概念作刻意的区分。
[13] 关于规范说直接诉诸法律文义和规范构造的特点,参见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83-284页。
[14] 比如,在德国,学者基本上都已放弃罗森贝克理论中的“权利受制规范”这一规范类别,vgl gottfried baumgärtel/lhans-willi laumen/hanns prütting,handbuch der beweislast:grundlagen,aufl 2.carl hezmanns verlag,2009,s 146 f.在日本,有学者主张在证
明责任分配标准中引入“实体法旨趣”之类的实质性考量,比如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98-399页。关于日本学者批评观点的更多介绍,参见前引[11],高桥宏志书,第441-448页;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295页;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174页。
[15] 关于规范说(或者法律要件说)的通说地位,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页;前引[14],张卫平书,第305页;前引[12],李浩书,第128-129页;毕玉谦:《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185页。另外,上述中国学者都赞成在中国以规范说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
[16] 参见前引[12],李浩书,第128页;前引???,王亚新书,第174页;前引???,毕玉谦书,第244-245页。
[17] 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100页。
[18] 一个规范究竟是基本规范还是相对规范,主要取决于当事人在具体诉讼中援引该规范的时间和场合,而对证明责任分配并无影响。关于基本规范与相对规范之间关系的相对性,又见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102页。
[19] 参见前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前引[7],郑金玉文。
[20]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83-284页;前引[14],新堂幸司书,第398-399页。
[21] 参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4-207页。
[22] 卡尔•恩吉斯:《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23] 梁慧星指出,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与《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制度构成了特别法与一般法的逻辑关系。参见梁慧星:《中国民事立法评说》,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
[24] 关于这一解释规则,见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5-76页。
[25] 《合同法》第49条并没有出现“善意相对人”的字眼,这一条只是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该行为有效。”但无论在学理还是在实务中,这里的相对人通常都被称为“善意相对人”。
[26] 即都以第三人不知道并且不应当知道特定事实为内容。
[27] 即都在于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
[28] 《最高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
[29] 参见前引[11],高桥宏志书,第244-248页。
[30] 参见前引[7],郑金玉文。
[31] 参加前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
[32] 前引[21],卡尔•拉伦茨书,第209页。
[33] 参见前引[6],陈华彬书,第282-283页。
[34]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平衡这两种利益的功能,又见谢在全:《民法物权》(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
[35] 《德国民法典》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932-934条,以第932条最为基础,第932条又援引了第929条。相关法条的逻辑关系,见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页。
[36] 《德国民法典》(第三版),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34、335页。
[37] 参见前引[7],郑金玉文。
[38] 比如挪威、丹麦等国。参见前引[6],陈华彬书,第281-282页。
[39] 从论者的知识背景和参引文献中不难发现这一点。
[40] 参见前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
[41] 参见前引[12],李浩书,第138页;前引[15],陈刚书,第256页。
[42] 渠涛编译:《最新日本民法:日本民法典》(2006年新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43] 同上书,第44页。
[44] 推定之名的证明责任规范,见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204页以下。
[45] 见《“中华民国”民法典》第944条。这一条排除了规范说对于该法第948条的适用。类似的规定还出现在《瑞士民法典》引言部分的第3条。按照该条规定,“当本法认为法律效果系属于当事人的善意时,应推定该善意存在。”这条规定同样排除了规范说对于《瑞士民法典》第933条的适用。
[46] 参见前引[34],谢在全书,第221页;王泽鉴书,第486页。
[47] 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又见vgl.jürgen oechsler,in:münchenerkommentar zum bgb,5.aufl.c.h.beck,münchen 2009,s 1069;othmar jauernig(hrsg.),bgb-kommentar,5.aufl.c.h. beck,münchen 2009,s 1293;前引[14],gottfried baumgärtel等书,第223页;palandt/bassenge,bgb,69 aufl.,c.h.beck,münchen2010,s 1504.
[48] 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126-127页,脚注5。
[49] 德国有民法学者认为,善意是善意取得的权利形成事实,只因其认定采推定的方法,因此须由反对方负担证明非善意的证明责任。比如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下册),申卫星、王洪亮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页;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吴
越、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推定。因为,就善意的成立,法律并未规定基础事实;关于恶意的证明是主证,而不是反证,见前引[47],othmar jauernig书,第1293页。
[50] 前引[47],jürgen oechsler书,第1069页。
[51] hans-joachim musielak,die grundlage der beweislast im zivilprozess,walter de gruyter,1975,s 379;前引[48],othmar jauernig书,第1293页。
[52] 参见前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
[53] see,e.g.,oscar gruss&son v.first state bank,582 f.2d 424,432(7th cir.1978);natural resources,inc.v.wineberg,349 f.2d685,688 n.8(9th cir.1965);albee tomato,inc.v.a.b.shalom produce corp.,155 f.3d 612(2d cir.1998).早期的一个述评, see evidence-burden of proving bona fide purchas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4,no.1(dec.,1936),pp.146-148.所有这些判决和述评都一再指出,在美国法上,多数判例认为主张善意取得的受让人应就其善意负证明责任。
[54] 在笔者看来,徐文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作者预先接受了《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法以及德国学者关于该条文立法技术的论述;因为对这种“前见”缺乏必要的自觉,当二位作者开始观察我国《物权法》第106条时,实际上已经无法做到作为一名解释者所应有的客观、中立。
[55] 关于“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参见前引[21],卡尔•拉伦茨书,第286页以下。
[56] 有时又被表述为消极事实。考虑到这主要是译名选择的不同所致,本文对这两个概念不作区分。
[57] 参见前引[6],叶金强文。
[58] 参见前引[6],陈华彬书,第550页。
[59] 参见前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
[60] 参见前引[7],郑金玉文。
[61] 罗森贝克指出:“证明困难并非证明不可能……如果认为对否定加以证明是没有必要的,那就意味着必须修改实体法。”否定事实是否需要证明,“仅仅取决于法律是否将该否定规定为法律效力的前提。如果法律将它规定为法律效力的前提条件,那么,主张此等法律效力的人,同样必须就该否定承担证明责任。”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332、333页。
[62] 同上书,第330页以下。
[63] dieter leipold,beweislastregeln und gesetzliche vermutung,berlin:dunker&humblot 1966,s 47.
[64] 前引[51],hans-joachim musielak书,第371、376页。
[65]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59页。
[66] 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333页;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59页。
[67] 黄国昌:《阶段的举证责任论——统合实体法政策下之裁判规范与诉讼法观点下之行为规范》,载氏著:《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68] see rupert cross/colin tapper,cross on evidence,buttersorths,1990,p124.
[69] 参见前引[12],李浩书,第128页;前引[14],张卫平书,第281-282页;折衷的观点,见前引[15],毕玉谦书,第41-50页。
[70] 前引[14],张卫平书,第281-282页。
[71] 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见姜世明:《举证责任与证明度》,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56页。
[72] 前引[6],陈华彬书,第550页。
[73] 下一节集中讨论这些证明策略。
[74] 笔者认为,日本法和台湾法中有关占有的善意推定在性质上属于占有推定的内容,导致这种立法的是法律政策的考量(即对占有公信力的确认和保护),与善意的证明难度并无直接关系。
[75] 出于篇幅考虑,仅引用判决书中认定善意要件成立的部分。完整的案情和判决,请参考判决书原文。所有判决均来自“北大法宝”。
[76] 《(2010)焦民二终字第196号判决书》。
[77] 该判决在二审中被改判,但改判的理由是不动产没有登记,而不是第三人非善意。参见《(2009)商民终字第120号判决书》。
[78] 《(2008)崇民一(民)初字第3149号判决书》。
[79] 《(2007)苏中民三初字第0094号判决书》。
[80] 《(2009)新中民四终字第504号判决书》
[81] 《(2009)川民初字第0972号判决书》。
[82] 《(2007)厦民终字第2115号判决书》。
[83] 《(2009)驿民初字第2324号判决书》。
[84] 关于善意的内容,民法学界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从现行法出发,将善意解释为包含不知情和非因重大过失不知情较为妥当
[85] 前引[34],王泽鉴书,第486-487页。
[86] 前引[14],gottfried baumgärtel等书,第309页.
[87] 关于间接证据的整体性审查,参见前引[14],gottfried baumgrtel等书,第320页
[88] vgl gottfried baumgärtel/lhans-willi laumen/hanns prütting,handbuch der beweislast:bgb sachenrecht(§§854-1296).aufl 3. carl hezmanns verlag,2010,s 224.
[8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
[90] 这里之所以使用“经验则”,而不是更流行的“经验法则”一词,是因为,这一概念显然来自德语的erfahrungssätze一词,而这个由erfahrung(经验)和sätze(句子)构成的德文单词,并不包含“法则”一词的含义。另外,如果我们把erfahrungssätze译为“经验法则”,在翻译与denkgesetz(思维法则)、naturgesetz(自然法则)并列的erfahrungsgesetz一词时就会遇到困难,因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验法则”。
[91] 前引[11],高桥宏志书,第29页。
[92] stein/jonas/leipold,kommentar zur zpo,22.aufl.tübingen 2008,s 640.
[93] 不同类型的经验则,见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106页以下。
[94] 德国学者将此称为“证明相对方事实主张具体化义务的加重(gesteigertel substantiierungspflicht des beweisgegners)”,见前引???,gottfried baumgärtel等书,第358页以下。
[95] 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下),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30页。
[96] 参见前引[14],gottfried baumgärtel等书,第360页。
[97] 这里之所以限定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是因为英美法系的证明责任概念在构成上与大陆法系存在明显差别,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大陆
法系的相关理论。关于这一点,可参见黄国昌:《阶段的举证责任论——统合实体法政策下之裁判规范与诉讼法观点下之行为规范》,载黄国昌:《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134页。
[98]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56页。
[99]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57页以下。
[100]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63-264页。
[101]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59页。
[102]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04页;前引[14],gottfried baumgärtel等书,第223页。
善意取得制度范文第14篇
内容提要: 《物权法》第106条确立的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规则,只能解释为主张善意取得的第三人负担证明责任。尽管善意要件的证明有一定难度,但通过间接证据的运用、经验则的援引以及对方当事人事实主张责任的加重,证明该要件是完全可能的。立法论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需要结合诸如进攻者角色、盖然性衡量、证明接近之类的实质性因素,以及公示方式与交易习惯、诉讼程序的实际运作、法律政治考量之类的外部因素进行。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善意取得的成立需要符合三个要件:受让人善意,交易价格合理,不动产登记或者动产交付。三要件中,后两个要件具体而明确,其法律适用相对简单。唯第一个要件,因涉及受让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其证明究竟遵循何种原则和标准,不仅在司法实务中乱象丛生,学说上亦不乏纷争。
(一)实务中的乱象
实务中的混乱状态,从以下几个案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1]
案例1:a将其所有的房子交给侄子d长期居住,而d将该房转卖给了h。a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与h二人之间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无效;h主张其对房产构成了善意取得。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判决书中写道:“被告h辩称自己作为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该房屋归被告d所有,因双方签订协议时,没有向其交付任何有关该房屋的手续,而h又无证据证实该房屋系d所有,因此,h以善意购买该房屋的辩解,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www.lw881.com” [2]
案例2:y与t原为夫妻。离婚后,y向h借款,并以t名下的轿车与h签订了质押担保。后y逾期未返还借款,h请求法院确认其对小轿车的占有构成善意取得动产质权。一审驳回了h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生效后,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抗诉理由之一是原审判决由原告h负担其为善意的举证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再审法院接受了这条意见,却仍维持了原判。再审判决中写到:“本案车辆质押合同的效力仍需衡量h占有该车辆时是否出于善意,即h不知道y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则构成善意取得。在判断h是否为善意,理论上虽应采取推定的方法,应由t对h占有该车辆时的恶意进行举证,但是,本案中的有效证据显示,y向h交付轿车时,机动车登记证书明确载明车辆所有权人是t,即使h不知道y与t离婚之事实,h也仅能推断该车辆系y与t的共同共有财产,在未经t同意的情形下,y不得单独对该车辆作出处分。根据在案证据已可证实h未尽一定程度的注意义务……” [3]
案例3:j与z原系夫妻关系。z在其与j的离婚诉讼期间,将其本人名下的一套房产卖给了w。j诉至法院,称该房产系其与z的夫妻共同财产,要求法院判令z与w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被告则主张其对该房产的占有构成善意取得。在一审过程中,原告j提交了其所属单位的电话本3份,以证明被告w知道原告和被告z是夫妻关系,并可能知道原告和被告正处于离婚诉讼期间。一审法院认为j的证据不足以证明w买房时系恶意,驳回了j的诉讼请求。j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判决书中写道:“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j上诉称被上诉人w购买房屋时并非属于善意取得,对该主张,因其未能举出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4]
反映在上述判决中的有关善意要件之证明的混沌不明之处,大致可以归入两个问题:一是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二是善意要件在具体案件中如何证明。就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第一份判决看上去认为第三人应当就其善意负证明责任;第二份判决明确指出,就第三人的善意,理论上应采推定的方法,由原权利人证明其恶意;第三个案件相对复杂,但从判决书的论述逻辑来看,法官似乎认为共同财产所有人应当就第三人接受财产转让时的非善意负证明责任。[5]就善意要件的具体证明,三份判决也都作出了详略不等的说明。
(二)学说上的分歧
就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者间存在明显分歧。尽管多数民法学者认为,就善意要件的认定应当采取推定的方法,即推定受让人为善意,而由主张其为非善意的原权利人就受让人的恶意或者重大过失负举证责任; [6]晚近发表的两篇专论却持不同观点。[7]在对现行法进行法解释学阐释时,两篇专论一致认为,善意要件应由主张善意取得的受让人(第三人)负担证明责任。不过,就导致这种证明责任分配方法的条文设计是否合理,二文之一却提出了激烈的批评。[8]在该文看来,我国目前的制度设计使得第三人不得不证明实际上很难证明的“消极事实”,这将严重限制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甚至让这一制度的规范目的落空。在逻辑上,这种批评以善意证明的难度否定第三人负担善意证明责任的制度安排,我们看到,这种逻辑在其他民法学者那里也有体现。[9]这提醒我们:在讨论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时,实际上无法回避该要件究竟如何证明的问题。
本文拟就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澄清呈现于上述判决、学说上的混乱和纷争。引言之后,第二部分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分析《物权法》第106条中蕴含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第三部分讨论善意要件的证明可能性及其实现策略;在结束司法论的考察之后,第四部分从立法论的角度分析未来该问题立法需要考量的内外因素;结论部分归纳本文主要论点,并就本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稍作阐发。
二、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法解释学的分析
所谓证明责任,即争议事实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的败诉责任。通说认为,证明责任规范在性质上属于实体法,应当主要从实体法规范中寻求和发现。[10]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与善意要件直接相关的则是该条第一款后句。这样,我国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主要就转化为该条规范的解释问题。
(一)语义解释
立法者一般不会在实体法中直接规定证明责任分配,但通过分析实体法规范的文义和结构,从中发现证明责任规范却是可能的。依其表述方式和规范结构,罗森贝克将实体法规范分为权利形成规范、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妨碍规范和权利受制规范,其中,权利形成规范是从正面规定权利成立的规范,后三种规范则是从反面规定权利消灭或者受阻的规范。由于每方当事人都要主张和证明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规范,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就对权利形成规范负担主张和证明责任,否认权利存在或主张权利消灭、受阻的当事人则对后三种法律规范负担主张和证明责任。[11]这就是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规范说。[12]考虑到规范说直接诉诸实体法规范表达方式的特点,人们有理由把这种学说看作实体法语义解释的一种。[13]尽管规范说已经遭到不少批评,但主流观点大多认可其基本框架,所谓修正只反映在一些细节; [14]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德国、日本,还是我国台湾,规范说都仍是法官司法实务中通行的学说。[15]究其原因,是因为由这种学说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清晰、稳定而统一,易受职业法律人的青睐。[16]因此,这里仍从规范说开始我们对《物权法》第106条的证明责任意义上的法律解释。
考虑到在诉讼中,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一般需要援引权利形成规范作为攻击手段,主张该权利不存在的当事人则要援引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妨碍规范和权利受制规范作为防御手段,这两类规范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基本规范”与“相对规范”来界定。[17]由此出发,关于《物权法》第106条第一句的解读方式就有两种:一种是,将前半句关于追回权的规定看作基本规范,而将后半句看作其相对规范;另一种是将后半句本身看作基本规范。在前一种解读方式中,《物权法》第106条后半句关于善意取得三要件的规定属于(追回权的)权利妨碍规范;在后一种解读方式中,该规定则属于(善意取得的)权利形成规范。但无论采用哪一种解读方式,关于该条证明责任分配方法的结论都是相同的,[18]即主张善意占有的当事人应当就该条列举的所有三个法律要件负证明责任——其中自然也包括善意要件的证明。我们看到,其他学者对《物权法》第106条的解释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9]
(二)体系解释
针对规范说的一个批评是,仅从法律条文的文义和构造中寻求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不合理的。[20]一方面,立法者在设计实体法规范时可能并没有考虑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另一方面,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常常也不是通过单个条文来表达的。仅仅从一个法律条文出发,机械地运用规范说,可能会得出与立法者意图相悖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法。现代法律解释理论认为,法条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一定的“意义脉络”当中。[21]这要求法律适用者在对一个法条进行解释时,除了关注这个法条本身的文法和语义,还要考虑它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与其他法条的关系。[22]在法律的意义脉络和逻辑关系中理解一个法条,这就是所谓体系解释。具体到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规则,上一小节的语义解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的起点,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考察:体系解释是否会带给我们不同的解释结果?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在《物权法》第106条的意义脉络中,善意取得是作为无权处分法律效果的例外情形规定的。[23]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这种体系安排背后的逻辑是:如果我们认为主张无权处分者应当证明其所有权及无权处分,那么作为与这种法律效果对抗的砝码,善意取得的主张人自然应当就其是否符合善意取得的三个要件进行证明。
其次,根据相同概念相同解释的法律解释规则,[24]关于《物权法》第106条中的“善意”概念的解释,应当尽量与民法中的其他法律制度保持一致。我们看到,在《合同法》的表见制度中,同样存在“善意”的概念。[25]就概念内涵,两种情形下的“善意”并没有太大区别;[26]就规范目的,物权法对于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与合同法对于善意相对人的保护亦无本质不同。[27]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权。” [28]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效力,如果没有相反理由,就《物权法》第106条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也应作相同的理解。
(三)目的论解释
法律规范的语义确立了法律解释的起点和边界;在此边界内,体系解释让法律规范的语义更加清晰和丰满,因此不妨看作是一种延伸了的语义解释。而无论语义解释还是体系解释,目的都在于探寻立法者的规范意图。在对规范说进行反思、批判的过程中,已有学者提出应在证明责任的分配基准中引入利益衡量或者实体法旨趣之类实质性考量的观点。[29]姑且不论这类观点是否成立,仅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如果基于规范说得到的证明责任分配结论与《物权法》第106条的规范意图明显冲突,那么这种结论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就《物权法》第106条的立法意图,学者的观点存在分歧。一位学者认为,《物权法》第106条通过将善意要件作为法律成立要件规定的方式将该要件的证明责任加诸第三人,体现了一种优先保护所有权的立法意图。[30]在另两位学者看来,如此规定只会限制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导致《物权法》第106条规范目的——即保护交易安全——落空的严重后果。二位学者更明确指出,不能想当然的以为,物权法作此规定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所有权;这只不过是法条设计不当的结果而已。[31]
在笔者看来,第一种观点更有说服力。首先,将保护交易安全界定为善意取得制度的目的虽然没有错,却不能把保护交易安全看作这一制度的唯一目的。正如拉伦茨所言,“一项法律规则常不只要实现一个目的,毋宁常以不同的程度追求多数的目的。”[32]尽管善意取得制度的确立表明法律在总体上采取了牺牲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而保护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的立场,但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无论何时、何地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因为这一点,多数国家选择了兼顾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与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的“中间法立场”,而非原则上不承认善意取得或者对善意取得的范围基本不加限制的“极端法立场”。我国《物权法》亦不例外。[33]从这个角度,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规范目的并非单纯保护交易安全这一种利益,而毋宁是在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保护这两种利益当中寻求平衡。[34]
其次,在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相比的意义上,说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偏重保护所有权并不牵强。如前所述,在我国《物权法》中,善意取得是被放在无权处分的法律效果——原所有权人的追回权——之后,作为其例外而规定的。这种立法体例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并不多见,与德国法相关规定更形成了鲜明对比。[35]《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1款规定:“即使物不属于让与人,取得人也因依照第条所为的让与而成为所有人,但取得人在依照该条的规定将会取得所有权时非为善意的除外。”而根据《德国民法典》第929条第1句,“为转让动产的所有权,所有人必须将该物交付给取得人,并且所有人和取得人必须达成关于所有权应移转的合意”。[36]学者指出,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彰显了物权行为有因性的立法原则,《德国民法典》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则以第929条确立的独立的、无因的物权行为逻辑起点。[37]也就是说,第929条确立了“满足交付与合意两个要件即带来所有权转移之法律后果”的规范,第932条第1款则将这一规范的适用范围从有权处分拓展到了无权处分。与这种明显旨在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例相比,我国《物权法》第106条无疑更倾向于保护所有权。
其实,这种倾向在我国《物权法》中多有体现。比如,我国《物权法》没有规定取得时效制度,对占有制度的规定也相当粗陋。考虑到取得时效以及占有保护均构成对原所有权的限制,现行法对这两类制度的消极态度,可以说进一步反映了立法者对于所有权保护的偏爱。
以上分析表明,《物权法》第106条在规范意图上的确偏重保护所有权,而将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施加给主张善意的第三人,正是这种规范意图的体现。退一步讲,即便我们承认“保护交易安全”是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主要规范目的,第三人负担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的立法例也并不会使这一规范目的落空。从原则上不承认善意取得,[38]到承认善意取得并且将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施加给原所有权人,我国《物权法》第106条的设计位于中间。这种立法例与那种将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施加给原所有权人的立法例相比,差别仅仅在于第三人善意与否真伪不明的那一部分案件;对于那些能够证明其善意的第三人而言,交易安全利益仍然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四)比较法解释
比较法不能作为解释现行法的直接依据,但可以为我们理解现行法提供间接参考。实际上,在对一种法律制度尚未形成稳定的法解释学共识之前,引入比较法资源经常是法律解释者不得不为的选择。我们看到,民法学者以推定解释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无疑受到了日本和我国台湾民法学著作的影响; [39]而徐涤宇、胡东海对现行法的批评,则是因为德国法提供了不同的立法例。[40]比较法上的这些反例,是否可以成为推翻本文解释结论——特别是基于规范说的语义解释结论——的依据?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完全否定的。
首先,日本法、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不构成对上文分析的反驳。一个不言自明的逻辑是:作为一种确定证明责任分配基本原则的理论学说,规范说仅适用于法律没有就证明责任分配作出规定的场合。[41]《日本民法典》第192条规定,“通过交易行为平稳且公然开始占有动产的人,在善意且无过失时,即时取得可在该动产上行使的权利。” [42]表面上看,善意在这里似乎是权利成立规范的要件事实。但问题是,就善意的成立,《日本民法典》第186条第1款已经规定:“占有人,可推定为以所有的意思、善意、平稳且公然地占有之人。” [43]《日本民法典》第186条实际是一条假推定之名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44]立法者通过这个规范,将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直接分配给了就占有人的善意提出异议的人。由于第186条的存在,规范说被排除在了第192条的解释之外。差不多相同的规定也出现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条。[45]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台湾民法学者的论述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总是被从反面、以恶意证明的方式赋予原权利人。[46]
其次,德国法同样不构成对上文分析的反驳。就《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1款,拉伦茨认为,“在有人对取得人的所有权提出疑问时,取得人只需要证明根据第929条所有的让与行为,而毋需也证明他在取得所有权之时是善意的。对取得人的所有权提出疑问的人,才必须对取得人的非善意提出证明。” [47]按照罗森贝克的理论,通过“……除外”这样的表达方式,立法者赋予第932条第1款以权利妨碍规范的性质。[48]主张该规范以妨碍基于第932条前半句主张善意取得者,需要就该规范负担证明责任,即证明取得人为非善意。[49]与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将善意要件作为取得人的权利成立要件规定相比,德国法第932条代表了另一种立法例。但这两种立法例都可以被纳入同一种解释工具,即规范说。
最后,上述立法例都可以在其本国善意取得制度的规范目的中得到解释。关于善意取得的规范目的,上一节已有简单涉及。这里以德国法为例,提供进一步的论据。在德国民法典第一立法委员会拟定的草案当中,善意的证明责任其实是被交给取得人的,因为当时的起草者认为,占有的公信力无法与不动产登记相提并论。但在第二次立法委员会那里,交易安全利益压倒了所有权保护利益。[50]结果,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意图在证明责任环节也获得了优先考虑,立法者将善意要件的规范形式由之前的权利形成规范改成了现在的法律妨碍规范。[51]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在立法上,将善意要件作为善意取得的权利成立要件和将其作为权利妨碍要件来规定都是可能的;第二,选择哪一种立法模式,起决定作用的是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就立法技术的运用而言,两种立法模式并无不同,即都是通过规范表述方式的选择,达到在当事人之间妥当配置证明责任的目的。
综上所述,尽管日本法、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和德国法关于善意要件证明责任分配的立法与我国《物权法》不同,但这只是各国(地区)善意取得制度不同立法意图的反映。一旦引入立法意图的因素,比较法上的不同立法例就变得可以理解,也不再有优劣之分。上述立法例不仅没有证伪,反而从方法上进一步证成了前文关于《物权法》第106条的解释结论。
(五)普适的德国法
徐涤宇、胡东海二位先生的《证明责任视野下善意取得之善意要件的制度设计——〈物权法〉第条之批评》一文(以下简称徐文),从证明责任角度对《物权法》第106条提出了激烈批评。徐文从《德国民法典》第932条出发,认为该条确立的善意要件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在比较法上具有普适性;反观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则由于立法者缺乏通过实体法分配证明责任的意识,有规范目的落空之虞;这一缺陷已经无法通过解释论弥补,而必须借助“超越法律的续造”来补救。[52]就该文部分观点及论据,前文已有零星反驳,此处不赘。唯“德国法的普适性”一点,因在徐文中具有方法论的基石意义,仍需进一步澄清。
首先可以指出的是:即便最粗糙的比较法考察,也不能得出《德国民法典》第932条具有“普适性”的结论。在大陆法系,日本法、我国台湾地区法、瑞士法的法条结构与德国法均不相同;在英美法系,美国法更是提供了完全相反的判例。[53]不需要更多的考察,对于“德国法具有普适性”的判断,有限的几个反例就已经足够了。更重要的是,即便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采用了德国法的立法例,因此在概率的意义上姑且承认德国法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性”,但这一判断对我们评估中国法也不具有直接的意义。立法者面对的社会情景不同,需要达到的立法目的不同,为此可以选择的立法技术也不同。评价一个国家的某个立法妥当与否,只能看这一立法在立法目的的设置上是否顺应了这个国家社会、经济的需要,以及立法者是否通过立法技术的运用,妥帖地实现了这一立法目的。从这个角度,仅仅因为德国法的“普适性”而批评中国《物权法》第106条设计不当,这本身就是武断的和不公正的。
在笔者看来,徐文的关键问题在于:发现了德国法与中国法的区别,却没有深入分析导致这种区别的原因,而是将其简单归咎于立法者的疏忽;接受了德国法学者关于《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的分析,却没有看到,这种分析只是对德国法的法解释学阐释——而这种阐释恰恰不具有“普适性”。[54]法解释学的终极目的是探寻本国现行法的真义,为做到这一点,只能从本国法规范的语义出发,参考本国法的体系和逻辑,探寻本国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德国学者如此,中国学者也应当如此。从这个意义上,德国法的规定,以及对这些规定的评注都不能成为解释、批评中国的直接依据。而本文迄今为止的分析表明在忠实反映立法者规范意图这一点上,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做得并不比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差;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未发现启动“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的充分理由。[55]
三、善意要件的证明之道
依前所述,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物权法》第106条第一款只能解释为第三人负担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不无争议的是,善意要件是否能够证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又应通过哪些方法来证明?这类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圆满回答,第一节的分析也许难免遭遇“概念法学”的非议。
(一)无法证明的善意
一个经常看到、但却很少得到充分论证的观点是,作为一种否定性事实,[56]善意要件很难从正面被证明。比如,叶金强认为:“由于第三人不知真实物权状况为一消极事实,要求第三人证明其不知,在逻辑上难于成立,而且占有具有推定力,第三人可以将占有人视为真正权利人,所以,在无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真实物权信息的情况下,即应推定第三人为善意。可见,原权利人如果要否定善意取得的构成,需要举证证明第三人知道事实真相。” [57]陈华彬认为:“因无过失为常态,有过失为变态,且无过失为消极事实,依民事诉讼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占有人应无须就此常态与消极事实负举证的责任。” [58]徐涤宇、胡东海认为:“受让人若要成功证明自己的善意,却并非易事。此所谓善意是指不知让与人无处分权而言。因而,‘善意’是一种否定性事实或消极性事实。此类事实,虽非证明责任理论中的消极事实说认为的‘消极事实不能证明’,却也是很难证明的,加之‘善意’是一种主观内在状态,其证明难度更大。” [59]甚至郑金玉也认为,由第三人自证其善意,将会给司法实践带来难题。[60]在笔者看来,这类观点的价值主要不在法解释学,而在法政策学。在法解释学层面,如果上文的分析成立,那么,即使真如论者所言——善意要件很难被证明,解释者也只能认为,立法者本来就是要通过证明难度的增加而将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限制在很小的范围。[61]但在法政策学层面,如果这种论点成立,立法者在设计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规则时就不应对其视而不见。但是,善意要件真的无法证明吗?或者至少,善意的证明难度要远远大于恶意的证明吗?无论从理论还是实务的角度考察,对这些设问的回答看上去都是否定的。
首先,作为这一论点理论基础的否定事实说,早已被证明为是不妥当的。否定事实说认为,只有肯定的事实能够证明,否定的事实是不可能证明的。这一学说早已被德国法学家抛弃。德国研究证明责任的所有权威学者——从最早的罗森贝克[62],到晚近的莱波尔德[63]、穆泽拉克[64]、普维庭[65],都一再指出,否定事实说原则上是错误的。肯定事实与否定事实的区分,从来不是决定证明责任分配的关键因素,甚至不是重要因素。即使是立法者经常会在立法上避免否定事实的证明,也不能改变这一结论。[66]在英美法系,该理论自十九世纪末就被学者抛弃。[67]尽管有判例从“否定性事实不易证明”的角度分析证明责任的分配,但正如学者指出的,在这些案件中,决定证明责任分配的关键因素其实是公共政策考量。在普通法中,同时大量存在要求当事人证明否定性事实的例子;就这类事实的证明,并不存在一个原则性的标准。[68]在我国,学者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69]在笔者看来,否定事实说之所以会被抛弃,主要是因为否定事实与肯定事实的划分非常模糊。[70]部分地因为这一点,否定事实是否难以证明,就成为一个不能一概而论的问题。一个事实要件究竟是从否定的方面更容易证明,还是从肯定的方面更容易证明,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71]
其次,具体到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正面证明善意未必比从反面证明恶意更难。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是指第三人的“不知情”,即不知道并且不应该知道处分人对于财产没有处分权;所谓“恶意”,则是指第三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处分人对于财产没有处分权。陈华彬先生认为:“占有人是否以善意加以占有,因属其个人内心之事,难以举证证明,故在善意占有抑或恶意占有的事实不明时,推定为善意占有。” [72]这一论断的前半句并无不妥;但问题在于,“恶意”同样是“个人内心之事”,没什么证据表明证明“恶意”比证明“善意”容易。实际上,无论善意证明还是恶意证明,都必须运用一些特殊的证明策略才能完成。[73]既然如此,善意证明的难度如何就能成为善意要件证明责任分配的依据呢? [74]
最后,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告诉我们,证明“善意”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说以上分析只是理论上的“假说”,那么中国法官的实践则为这种“假说”提供了大量证据。在《物权法》颁行后的审判活动中,中国法院频繁作出认定善意要件成立的判决。只需稍举数例: [75]
1、“白存忠持有宅基地使用证书,该使用证书上非原告名字,马正省征询了村委意见,签订协议时包括小队长在内的多名中间人参加,故马正省购买白存忠的房屋时没有恶意,是善意的。” [76]
2、“第三人李某运作为房屋的卖方持有原告韩某的房产证、身份证复印件、房屋钥匙,与被告王某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该房屋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被告王某购买了该房屋,并支付了合理对价。房屋买卖协议签订后,被告王某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已数年,原告韩某一直未提出异议。第三人李某运虽无权处分该房屋,但被告王某有理由相信第三人李某运有权处分。被告王某购买该房屋是善意取得。” [77]
3、“被告候某、万某间系夫妻关系,被告候某十多年来对其房产不闻不问,其漠视自己所有权的行为,显然有悖生活常理。被告朱某有理由相信被告候某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房已出售他人,被告万某也具有出售房屋的权,被告万某实施的出售房屋的行为,系被告候某、万某的共同意思表示。因此,被告朱某善意有偿取得房产,其合法权益应予保护。” [78]
4、“因涉案财产原所有权人群翊公司在设定所有权保留时未依法进行登记,亦未通过其他方式向合同外第三人进行公示,合同外第三人雅新线路板公司不可能知晓设备出让人系无权处分,其受让财产应属善意。” [79]
5、“在本案中,藏东菊将五间房作价8000元抵偿给了王国忠,是藏东菊的真实意思表示,王国忠接受该五间房屋予以折抵藏东菊的欠款是善意的,且藏东菊已经将该五间房屋交付给了王国忠,王国忠即取得了该五间房屋的所有权。” [80]
6、“本案中,被告袁铁旦取得争议房屋的权利前,出卖人在此长期居住,原告却没有在此居住,被告袁铁旦和出卖人经协商达成协议,袁铁旦支付了合理对价,出卖方交付了房屋的相关手续,在被告袁铁旦居住后,又自建了房屋,厂方没有提出异议,原告徐其岭事前事后经过该房,明知后也未提出异议,被告袁铁旦有理由相信出卖人对该房屋有处分权。” [81]
7、 “本案被上诉人张开欣于2005年12月4日经中介公司居间介绍,凭当时的房产现有资料(经济实用房的申购人、购房合同签订人均为薛兴国)直接与薛兴国本人签订‘房产买卖协议书’及‘补充条款’。交易时购房合同及购房发票原件交付张开欣保管,房产也交付张开欣入住,张开欣主观上显然是善意的。” [82]
8、“原告张晓娜购买该房屋时,是经中介公司中介购买,购买时诉争房屋登记的原产权人为袁铁路且登记上未显示有异议登记,故作为受让人的原告在购买该房屋时是善意的。” [83]
尽管上述判决就善意证明的阐述详略不等,将它们放在一起,却足以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善意要件的证明难度并没有给中国法官带来太多困惑。尽管笔者没有就善意取得的司法判决做一个系统的统计分析,尽管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大量认定“善意”不成立的案件,但笔者相信,上述判决对于打消那种“因为善意要件证明责任设置不当而导致《物权法》第106条规范意图落空”的担忧,已经足够了。
(二)善意要件的证明策略
作为一种涉及人的主观认知状态和心理状态的事实要件,善意的证明与一般客观事实的证明的确有所不同。这本是不言自明的。笔者相信,不会有哪个法官会用认定一般客观事实的策略和方法来对善意要件进行调查和认定。但这里仍打算对善意要件的证明策略稍作探讨。因为,这种讨论不仅可以为上述结论提供进一步的支持,而且对类似证明难题的解决也具有方法上的参考意义。
1、间接证据的运用。如前所述,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是指“第三人不知道并且不应当知道处分人对财产无处分权”。也就是说,主张善意取得的第三人不仅需要证明其“不知情”,而且需要证明其“不应当知情”——即“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情”。[84]其中,前者涉及第三人在交易时的主观认知状态;后者则是法律对第三人不知情的原因的评价,在实践中经常可以转化为第三人是尽到必要注意义务的问题。[85]
在证据法理论上,知识、意图、意愿这类存在于人类精神领域的事实被界定为“内在事实”,而与存在于外部世界、能够被人类通过五官感知的“外在事实”区别开来。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对于后者,直接证明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对于前者,多数时候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来证明。[86]与善意要件相关的“知情与否”就属于内在事实。对该事实,严格意义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一种,即第三人本人的声明。而考虑到第三人在诉讼中所处的地位,这种声明对法官事实认定的意义非常有限。第三人为证明其“不知情”,还要就此声明进行更具体的事实主张和证据提出。比如,第三人可以提供证人证言,证明他曾经在特定场合谈到过他要与出卖人进行交易,并且从言辞中可以得知他并不知道该出卖人对财产没有处分权。更常见的情形是,第三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出卖人在交易中展示的权利表征让他有理由相信其对财产有处分权。比如,对于不动产,出卖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中确实显示了其本人姓名;对于动产,出卖人对财产的占有在具体情景中看上去是持续、稳定的。第三人为证明这些事实提供的证据,在性质上都属于间接证据。对这类证据,法院首先应当审查其关联性,即审查间接证据与证明对象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对那些经过审查,被认为对证明主题的确有效力的间接证据,法院应当从整体上进行综合判断。也就是说,要将这些证据作为一个整体,看它们是否足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即第三人的不知情。[87]
为了证明“无重大过失”,第三人应当就交易的主体、时间、地点、内容和过程提供信息,以证明他在当时的情景中,已尽到了一般人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88]在逻辑上,“无重大过失”的证明发生在“不知情”的证明之后,并以前者为基础。但在实践中,对这两个证明对象的证明经常是不分彼此、交织进行的。比如,当第三人就交易场景以及他在交易中的表现提供证据时,这些证据一方面是证明其“无重大过失”的直接证据,另一方面,又不妨看作证明其“不知情”的间接证据。
上述思路对中国的法官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 [89]其中体现的证明逻辑,与上文的阐述并无实质区别。
2、经验则的援引[90]。所谓经验则,简单的说,就是“从经验中归纳得到的关于事物的知识或法则”。[91] “在经验则这个概念下,人们可以想到的除了通过观察具体事件得到的一般生活经验,还有交易生活、商业、贸易,甚至艺术、科学和技术中的一般性规则、原则和知识。” [92]在善意要件的认定过程中,经验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对于善意的证明经常只能通过各种间接证据来完成。比如,在关于二手车的争议中,第三人提供证据证明:他是在法定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上与出卖人完成交易的;他之前并不认识出卖人;他就该二手车支付了合理的对价。这些证据本身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直接证明第三人是善意的,但将它们放在一起,却可以初步证明这一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官在这里运用了一个经验则——即:在上述情形下,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出卖人对财产有处分权。在上文引用的第4个判决书中,法官也援引了一个经验则:对于没有登记并且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向社会公示的所有权保留,合同外的第三人不可能知道。可见,在间接证据与证明结论——第三人的善意——之间,经验则实际充当了一种桥梁或者纽带的角色。
应该注意,不同类型的经验则,其盖然性并不相同。有些经验则只具有较弱的盖然性,只能作为法官对案件事实进行综合判断时的参考;而另一些经验则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构成了“典型生活过程”,以至于可以直接发生表见证明的效果。[93]另外还要看到,经验则是对证据与争议事实之间关系的一种盖然性说明,就这种说明,对方当事人总是可以通过反例来推翻。比如在上述第四个案件中,原权利人就可以提出第三人实际上知道处分人没有处分权的事实,来反驳“对于没有登记并且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向社会公示的所有权保留,合同外的第三人不可能知道”的经验则。
3、对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义务的加重。[94]在善意要件的证明过程中,第三人并不需要就其主张的所有间接事实进行举证;对于对方没有反驳的间接事实,法官毋宁是直接确认为真。[95]而权利人对第三人主张的间接事实,也不能是简单地否认了事。考虑到善意要件本身的特征,如果简单地否认声明就足以推翻第三人的事实主张,那么法官几乎很少能对争议事实形成心证。善意要件证明的特征要求权利人在否认第三人主张的间接事实时,必须提出足以推翻该间接事实的相反事实。举例言之,如果第三人主张其不认识处分人,这时权利人就不能简单地反驳说,“第三人其实认识处分人”。他必须就第三人与处分人之间的关系提出更加具体的事实。比如他可以指出,第三人与处分人曾在某一特定时期同学。又例如,在对上文判决4中提到的经验则进行反驳时,权利人就不能仅仅说,“即使没有公示,第三人也有可能知道其所有权保留的事实”。这一陈述尽管在理论上完全成立,但作为对本案证明的反驳却是不够的。为了动摇法官的内心确信,他必须提出能够表明第三人知道处分人无处分权的具体事实。一旦权利人提出了足以反驳第三人事实主张的具体事实,接下来就应由第三人就这些事实的不存在进行举证了。第三人的证据只要能够达到推翻上述反驳事实的程度,就算完成了证明。[96]
就证明难题的解决,还能想到一些别的策略,比如法官的事实推定、证明标准的降低,等等。一来为篇幅所限,二来考虑到这些策略的适用范围与前述三种策略多有重合,其概念内涵亦不乏争议,这里不拟展开讨论。之前的阐述已经表明,尽管善意的证明有一定难度,但现代民事诉讼早已发展出一系列解决这类证明难题的策略。只要法官妥善运用了这些策略,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就第三人善意与否获得心证的。需要特别警惕这样一种简单化的思维:一旦将证明责任施加给了一方当事人,这一方当事人就将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出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对方当事人则可以高枕无忧。不仅法官不会认同这种思维,从学理的角度,以这种方式理解证明责任显然也是浅薄的和片面的。实际上,对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法官而言,[97]证明责任规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环节:一是在事实调查开始时,由哪一方当事人首先针对争议事实提出证据;二是在事实调查程序终结而法官无法对争议事实形成心证时,判决哪一方当事人败诉。而在这两点之间的漫长诉讼过程中,法官不仅可以,而且应当运用多种手段,从双方当事人那里尽可能多地获取相关信息,以便对争议事实形成心证。对于法官的审理活动而言,作为真伪不明之时的裁判规则的证明责任规范固然重要,但为了避免适用证明责任规范而发展出来的诸种证明策略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四、立法论上需要考量的若干因素
此前的论述已表明了笔者对《物权法》第106条的基本评价,那就是:从司法证明的角度,这一条文是可以解释的,也是可以适用的。但这只是一个解释论上的中立判断,它并不意味着笔者“喜欢”这个条文,更不意味着笔者否认这一条文有被修改的可能。这种可能性是否,以及何时出现,取决于立法者的法律政策考量。当然,立法者的法律政策考量也应当有章可循。就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立法,以下两类因素是立法者必须关注的。
(一)影响证明责任立法的实质性因素
按照德国学者的观点,法官对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运用只能从实体法出发,而不能在此过程中掺入实质性考量。因为那样的话,法官实际上篡夺了立法者的权力,法律的安定性将荡然无存。[98]但是,对于立法者而言,进行这类实质性考量却是可能的,有时候甚至是必要的。按照普维庭的归纳,这类实质性原则主要有:抽象的盖然性衡量、证明接近、社会保护思想、宪法上地位、进攻者角色、危险增加、消极性证明,等等。[99]不过,对于善意要件的证明,真正需要思考的只有进攻者角色、盖然性衡量和证明接近。
1、进攻者角色。进攻者角色原理的基本要求是,要求改变现状的当事人应当就其主张的事实负担证明责任。在普维庭看来,这一原理在各实质性依据中具有中心地位,因为它与保护占有、权利安定性、社会秩序保护、对现存事实状况的保护和禁止私力救济等基本法律价值密切相关。[100]实际上,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理论通说的规范说与进攻者角色原理基本上契合;或者换句话说,进攻者角色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规范说的实质性依据。[101]表面上看,在善意取得制度中,进攻者角色理论有利于支持让原权利人负担证明责任的观点。不过,这一论辩的价值非常有限。就善意取得所涉及的财产,在不同时期实际存在两个不同的占有:一个是原权利人基于所有权的占有,一个是第三人基于无权处分的占有。固然,基于第三人的视角,我们可以说原所有权人处于进攻者角色;但基于所有权人的视角,又不妨说第三人处于进攻者角色。进攻者角色原理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视角。起决定性意义的只能是立法者的价值判断,或者说,是立法者对所有权保护和占有保护这两种利益进行衡量的结果。
2、盖然性衡量。盖然性衡量理论要求立法者在配置证明责任时,衡量真伪不明时事实“为真”与“为伪”的概率,并据此制定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比如,就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立法者就应当衡量,在现实生活中,究竟第三人为善意的概率更大,还是其为恶意的概率更大。如果第三人为善意的概率更大,那么在真伪不明时判原权利人败诉看上去更具合理性;相应地,在立法上,将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原权利人就是较为妥当的选择。由于引入了概率概念,这一理论比较具有科学性的外观,因此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但是,这一理论对于立法者的参考价值却很有限。主要问题在于对于一个要件事实真伪不明之时“为真”或者“为伪”的概率,实际上很难衡量。以善意要件的证明为例,这一衡量首先涉及人们对于当前社会诚信状况的判断。如果一个社会的诚信状况较好,人们也许可以说,由原权利人证明第三人恶意是较好的选择;反之,则由第三人证明其善意更优。但是,这种判断很大程度上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究竟哪些案件会被认定为“真伪不明”,最终取决于法官的判断;而法官的判断又受到其证据调查能力、裁判习惯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将所有这些因素纳入盖然性衡量的范畴,看上去已经超出了这一理论所能容纳的范围。因此我们看到,就德国民法典第932条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德国学者通常认为,其实质性依据并非盖然性衡量,而是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即对占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102]
3、证明接近。按照证明接近原理,立法者在设计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时,应当尽量让距离证据较近的一方当事人提出该证据。基于有利于查清案件真实和节省司法资源的考量,证明接近原理有其合理性,并且在现代产品责任法、医疗责任法等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体现。不过,作为一种主要着眼于克服证明困难的实质性依据,证明接近理论的意义不宜夸大。为了克服证明困难,现代证据法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和理论,比如间接证明、表见证明、对方当事人的事实提出责任,等等。由于这些策略的存在,许多时候,即便某些证据不在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一方,也不影响其对相关要件的有效证明。在证明困难的情况下选择这类策略,而不是根据证明接近原理重新设计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因为这些策略大体都可以归入“证据评价”的范畴,其运用并不会改变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人们实在有太多理由坚持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比如,前文刚刚提到的进攻者角色原理。进攻者原则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即使证据不在我这一方,但如果我希望改变一种法律关系的现状,通常情况下我就要负担证明责任,因为我不能让他人无端地忍受讼累。因此,尽管证明接近原理表面上有利于支持现行法——即有利于支持让第三人负担证明责任的立法例,但我却不愿强调这一论据。
(二)影响立法者利益衡量的外部因素
以上分析几乎都指向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最终决定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证明责任配置方式的只能是立法者的利益衡量。换句话说,就是在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保护这两种利益里面,立法者更偏重于保护哪一种利益。事实上,这也是笔者在之前的法解释学分析中反复强调的观点。但立法者生活在一定时空之中,其价值判断从来不能超脱于其所处的历史与社会之外。与上一节阐述的实质性因素相对,这种来自历史和社会的变量构成了影响善意要件证明责任配置的外部因素。这里不可能全面考察这些因素,只挑出三个方面略加阐述。
1、公示方式与交易习惯。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根基在于物权变动公示的公信力,一般而言,物权的公示方法即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有学者指出,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的公信力存在重大差别:对于不动产,只要受让人信赖了登记,就是善意的,除非其明知登记错误,否则无需考虑交易环境等因素而对于动产,由于占有的公信力较低,受让人就不能仅仅凭借占有的事实当然地相信处分人具有处分权,因而在判断受让人是否具有信赖利益时,还必须考虑其他一系列因素,比如价格的高低、交易的具体环境、交易的场所等。[103]也就是说,基于不同的物权公示方法,关于受让人善意的证明要求也会有所不同。为了弥合这种差别,立法论上似乎可以考虑:对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要件,由原权利人从反面证明受让人为恶意;对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要件,则由受让人从正面证明其善意。[104]
但上述建议很大程度只是理论演绎的结果,它在实践中的合理性,还要结合当前中国民间的交易习惯进行具体分析。比如,我们看到,在我国农村地区,不进行不动产登记的房屋买卖大量存在。基于这样一种现状,立法者如果只是简单强调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结果就有可能导致(在具体情境下)有失公平的案件处理结果。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在考量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方式时,对民间交易习惯的调查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诉讼程序的实际运作。如前所述,实体法关于一个事实要件证明责任分配方式的不同选择,反映了立法者对对立利益进行衡量的不同结果。但是,即便是同一种证明责任的立法例,其在各个国家的实际效果也未必相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证明责任分配方式只决定了真伪不明之时败诉风险负担的大致框架,而在这个框架之内,这种风险究竟以多高的频率出现,很大程度却取决于一个国家诉讼制度的运作情况。比如说,在一个当事人提出证据的手段匮乏,法官化解各种证明难题的能力不足的诉讼环境中,证明责任负担对当事人而言就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而在这两个因素都相对乐观的情况下,证明责任负担带来的压力则会小很多。另外,影响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际效果的还有法官的裁判习惯。比如,法官究竟是倾向于作出证明责任判决,还是倾向于回避作出证明责任判决?在后一种情况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实际意义相对较小,因为它被适用的频率本来就很小;而在前一种情况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影响则较大。考虑到善意本身就是一个主观性较强、证明起来有一定难度的事实要件,立法者在考量其证明责任分配方式时,对上述因素不能不察。
3、法律政治的考量。法律不止是对既有社会生活状态的确认和保障,在许多时候,它还承担着引导公众的行为方式,塑造某种立法者期望的社会生活状态的功能。因此,在一定时期,法律有可能成为立法者推进社会变革的手段和工具。如前所述,现行法对所有权给予更多保护,而对交易变动施加了较多限制。就此制度安排,不妨认为,其背后隐藏着一种“目前社会上的交易行为不尽谨慎”的预设。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前提性预设被修正甚至抛弃都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目前这种制度安排对于经济生活的实际影响是:财产所有人可以以较为随意的方式行使所有权的权能,而受让人则需要在交易中多加谨慎。假如将此看作一种法律政治的考量,这种考量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同样有可能朝着有利于受让人、有利于交易便利的方向变迁。立法者在对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进行配置时,应当对此有着清醒的自觉。
五、结论
经由第二到第四部分的论述,就引言提出的问题,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1、《物权法》第106条确立的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规则,只能解释为主张善意取得的第三人负担证明责任。
2、通过间接证据的运用、经验则的援引以及对方当事人事实主张责任的加重,善意要件是可以被证明的。
3、立法论上关于善意要件证明责任分配的讨论,需要结合诸如进攻者角色、盖然性衡量、证明接近之类的实质性因素,以及公示方式与交易习惯、诉讼程序的实际运作、法律政治考量之类的外部因素进行。
此外,本文附带批评了徐涤宇、胡东海二位先生关于善意要件证明责任分配的分析。在笔者看来,尽管徐文的材料、观点均不无偏颇,其最致命的缺陷却在方法。将一个外国法上的命题“普适化”,拿来解释和批评中国法,这种研究方法在中国法学界相当流行。关于这种方法的谬误,前文已有揭示;至于此种谬误的避免,则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在分析中国法时,坚守作为解释者的中立立场。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行法在周密与精致程度上与德国、日本,甚至我国台湾地区法制相比,仍有明显差距;这种差距,又因为上述国家和地区相对丰富的法解释学研究成果而被进一步放大。但是,一种外国法律制度在逻辑周延性、体系自洽性上的优势,并不能成为我们放弃现行法的理由。正因为我们的现行法相对粗糙,才更需要法律人去悉心呵护。只有法律人怀着一种“护法者”的敬畏之情,以最大的耐心去为现行法探寻可能的解释和适用空间,这法律才能在我们的手中获得生机。
其次,在批评中国法时,更多关注中国法的运作实践,而不是仅仅关注中国法与外国法的文本差异。文本比较只能说明有限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法律文本相对简单、粗陋的背景下,拿其他国家成熟的法律制度和理论来衡量它,很容易就得出关于我国法的负面评价。但这种评价并不公正,也没有太大意义。一方面,文本比较揭示的“问题”在实践中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另一方面,法律文本的粗陋可以通过解释者的努力弥补,而这正是法学家的职责所在。
注释:
[1] 为节省篇幅,案情介绍以反映案件主要争议为限,判决书引用则限于与善意要件的证明直接相关的部分。三份判决均来自“北大法宝”,有兴趣的读者自可下载阅读全文。
[2] 判决书全文,见《(2009)郑民初字第963号判决书》。
[3] 判决书全文,见《(2010)浙杭商提字第1号判决书》。
[4] 判决书全文,见《(2010)郑民二终字第537号判决书》。
[5] 在实务中,法官很少使用“真伪不明”的字眼,对于肯定之外的事实判断,一般只是笼统表述为“证据不足,予以驳回”。从理论上,这意味着法官可能就该事实形成了为“否”的内心确信,也可能是该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另一方面,中国现行法上的“举证责任”,与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上的“证明责任”或者“举证责任”概念并不完全相同。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就上述判决究竟采纳了哪一种证明责任分配方案,实际上很难准确判断。这里的归纳是笔者细读三份判决文本之后得出的结论,其中,法官的表达方式和论理逻辑尤其受到了重点关注。笔者深知,这种归纳不完全精确,但为了研究的开展,眼下也只能满足于这种只具有大致可靠性的判断了。
[6] 比如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267页;叶金强:《论善意取得构成中的善意且无重大过失》,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5期;陈华彬:《民法物权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页;程啸:《论不动产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释义》,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尽管上述论著中的某些发表在《物权法》颁布之前,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论著的作者在《物权法》颁行后改变了观点。
[7] 参见徐涤宇、胡东海:《证明责任视野下善意取得之善意要件的制度设计——〈物权法〉第106条之批评》,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4期;郑金玉:《善意取得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研究》,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6期。
[8] 参见上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
[9] 参见前引[6],叶金强文;前引[6],陈华彬书,第550页。
[10] leo rosenberg,die beweislast auf der grundlage des bürgerlichen gesztzbuchs und der zivilprozessordnung,5.aufl.münchen:c.h.beck, 1965,s 82;hans prütting,gegenwartsprobleme der beweislast,münchen:c.h.beck 1983,s 20.;adrian keane,the modern law of evidence,butterworths,1996,p 69;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页(该章为李浩教授撰写)。
[11] 上引[10],leo rosenberg书,第100页以下;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理论与制度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0页。
[12] 通说有时又被称为法律要件分类说,比如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笔者认为,尽管法律要件说与规范说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但代表性论述的内容基本一致。因此,这里不对这两个概念作刻意的区分。
[13] 关于规范说直接诉诸法律文义和规范构造的特点,参见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83-284页。
[14] 比如,在德国,学者基本上都已放弃罗森贝克理论中的“权利受制规范”这一规范类别,vgl gottfried baumgärtel/lhans-willi laumen/hanns prütting,handbuch der beweislast:grundlagen,aufl 2.carl hezmanns verlag,2009,s 146 f.在日本,有学者主张在证
明责任分配标准中引入“实体法旨趣”之类的实质性考量,比如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98-399页。关于日本学者批评观点的更多介绍,参见前引[11],高桥宏志书,第441-448页;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295页;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174页。
[15] 关于规范说(或者法律要件说)的通说地位,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页;前引[14],张卫平书,第305页;前引[12],李浩书,第128-129页;毕玉谦:《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185页。另外,上述中国学者都赞成在中国以规范说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
[16] 参见前引[12],李浩书,第128页;前引瑏瑤,王亚新书,第174页;前引瑏瑥,毕玉谦书,第244-245页。
[17] 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100页。
[18] 一个规范究竟是基本规范还是相对规范,主要取决于当事人在具体诉讼中援引该规范的时间和场合,而对证明责任分配并无影响。关于基本规范与相对规范之间关系的相对性,又见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102页。
[19] 参见前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前引[7],郑金玉文。
[20]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83-284页;前引[14],新堂幸司书,第398-399页。
[21] 参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4-207页。
[22] 卡尔•恩吉斯:《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23] 梁慧星指出,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与《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制度构成了特别法与一般法的逻辑关系。参见梁慧星:《中国民事立法评说》,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
[24] 关于这一解释规则,见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5-76页。
[25] 《合同法》第49条并没有出现“善意相对人”的字眼,这一条只是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该行为有效。”但无论在学理还是在实务中,这里的相对人通常都被称为“善意相对人”。
[26] 即都以第三人不知道并且不应当知道特定事实为内容。
[27] 即都在于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
[28] 《最高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
[29] 参见前引[11],高桥宏志书,第244-248页。
[30] 参见前引[7],郑金玉文。
[31] 参加前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
[32] 前引[21],卡尔•拉伦茨书,第209页。
[33] 参见前引[6],陈华彬书,第282-283页。
[34]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平衡这两种利益的功能,又见谢在全:《民法物权》(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
[35] 《德国民法典》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932-934条,以第932条最为基础,第932条又援引了第929条。相关法条的逻辑关系,见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页。
[36] 《德国民法典》(第三版),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34、335页。
[37] 参见前引[7],郑金玉文。
[38] 比如挪威、丹麦等国。参见前引[6],陈华彬书,第281-282页。
[39] 从论者的知识背景和参引文献中不难发现这一点。
[40] 参见前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
[41] 参见前引[12],李浩书,第138页;前引[15],陈刚书,第256页。
[42] 渠涛编译:《最新日本民法:日本民法典》(2006年新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43] 同上书,第44页。
[44] 推定之名的证明责任规范,见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204页以下。
[45] 见《“中华民国”民法典》第944条。这一条排除了规范说对于该法第948条的适用。类似的规定还出现在《瑞士民法典》引言部分的第3条。按照该条规定,“当本法认为法律效果系属于当事人的善意时,应推定该善意存在。”这条规定同样排除了规范说对于《瑞士民法典》第933条的适用。
[46] 参见前引[34],谢在全书,第221页;王泽鉴书,第486页。
[47] 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又见vgl.jürgen oechsler,in:münchenerkommentar zum bgb,5.aufl.c.h.beck,münchen 2009,s 1069;othmar jauernig(hrsg.),bgb-kommentar,5.aufl.c.h. beck,münchen 2009,s 1293;前引[14],gottfried baumgärtel等书,第223页;palandt/bassenge,bgb,69 aufl.,c.h.beck,münchen2010,s 1504.
[48] 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126-127页,脚注5。
[49] 德国有民法学者认为,善意是善意取得的权利形成事实,只因其认定采推定的方法,因此须由反对方负担证明非善意的证明责任。比如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下册),申卫星、王洪亮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页;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吴
越、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推定。因为,就善意的成立,法律并未规定基础事实;关于恶意的证明是主证,而不是反证,见前引[47],othmar jauernig书,第1293页。
[50] 前引[47],jürgen oechsler书,第1069页。
[51] hans-joachim musielak,die grundlage der beweislast im zivilprozess,walter de gruyter,1975,s 379;前引[48],othmar jauernig书,第1293页。
[52] 参见前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
[53] see,e.g.,oscar gruss&son v.first state bank,582 f.2d 424,432(7th cir.1978);natural resources,inc.v.wineberg,349 f.2d685,688 n.8(9th cir.1965);albee tomato,inc.v.a.b.shalom produce corp.,155 f.3d 612(2d cir.1998).早期的一个述评, see evidence-burden of proving bona fide purchas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4,no.1(dec.,1936),pp.146-148.所有这些判决和述评都一再指出,在美国法上,多数判例认为主张善意取得的受让人应就其善意负证明责任。
[54] 在笔者看来,徐文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作者预先接受了《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法以及德国学者关于该条文立法技术的论述;因为对这种“前见”缺乏必要的自觉,当二位作者开始观察我国《物权法》第106条时,实际上已经无法做到作为一名解释者所应有的客观、中立。
[55] 关于“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参见前引[21],卡尔•拉伦茨书,第286页以下。
[56] 有时又被表述为消极事实。考虑到这主要是译名选择的不同所致,本文对这两个概念不作区分。
[57] 参见前引[6],叶金强文。
[58] 参见前引[6],陈华彬书,第550页。
[59] 参见前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
[60] 参见前引[7],郑金玉文。
[61] 罗森贝克指出:“证明困难并非证明不可能……如果认为对否定加以证明是没有必要的,那就意味着必须修改实体法。”否定事实是否需要证明,“仅仅取决于法律是否将该否定规定为法律效力的前提。如果法律将它规定为法律效力的前提条件,那么,主张此等法律效力的人,同样必须就该否定承担证明责任。”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332、333页。
[62] 同上书,第330页以下。
[63] dieter leipold,beweislastregeln und gesetzliche vermutung,berlin:dunker&humblot 1966,s 47.
[64] 前引[51],hans-joachim musielak书,第371、376页。
[65]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59页。
[66] 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333页;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59页。
[67] 黄国昌:《阶段的举证责任论——统合实体法政策下之裁判规范与诉讼法观点下之行为规范》,载氏著:《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68] see rupert cross/colin tapper,cross on evidence,buttersorths,1990,p124.
[69] 参见前引[12],李浩书,第128页;前引[14],张卫平书,第281-282页;折衷的观点,见前引[15],毕玉谦书,第41-50页。
[70] 前引[14],张卫平书,第281-282页。
[71] 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见姜世明:《举证责任与证明度》,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56页。
[72] 前引[6],陈华彬书,第550页。
[73] 下一节集中讨论这些证明策略。
[74] 笔者认为,日本法和台湾法中有关占有的善意推定在性质上属于占有推定的内容,导致这种立法的是法律政策的考量(即对占有公信力的确认和保护),与善意的证明难度并无直接关系。
[75] 出于篇幅考虑,仅引用判决书中认定善意要件成立的部分。完整的案情和判决,请参考判决书原文。所有判决均来自“北大法宝”。
[76] 《(2010)焦民二终字第196号判决书》。
[77] 该判决在二审中被改判,但改判的理由是不动产没有登记,而不是第三人非善意。参见《(2009)商民终字第120号判决书》。
[78] 《(2008)崇民一(民)初字第3149号判决书》。
[79] 《(2007)苏中民三初字第0094号判决书》。
[80] 《(2009)新中民四终字第504号判决书》
[81] 《(2009)川民初字第0972号判决书》。
[82] 《(2007)厦民终字第2115号判决书》。
[83] 《(2009)驿民初字第2324号判决书》。
[84] 关于善意的内容,民法学界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从现行法出发,将善意解释为包含不知情和非因重大过失不知情较为妥当
[85] 前引[34],王泽鉴书,第486-487页。
[86] 前引[14],gottfried baumgärtel等书,第309页.
[87] 关于间接证据的整体性审查,参见前引[14],gottfried baumgrtel等书,第320页
[88] vgl gottfried baumgärtel/lhans-willi laumen/hanns prütting,handbuch der beweislast:bgb sachenrecht(§§854-1296).aufl 3. carl hezmanns verlag,2010,s 224.
[8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
[90] 这里之所以使用“经验则”,而不是更流行的“经验法则”一词,是因为,这一概念显然来自德语的erfahrungssätze一词,而这个由erfahrung(经验)和sätze(句子)构成的德文单词,并不包含“法则”一词的含义。另外,如果我们把erfahrungssätze译为“经验法则”,在翻译与denkgesetz(思维法则)、naturgesetz(自然法则)并列的erfahrungsgesetz一词时就会遇到困难,因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验法则”。
[91] 前引[11],高桥宏志书,第29页。
[92] stein/jonas/leipold,kommentar zur zpo,22.aufl.tübingen 2008,s 640.
[93] 不同类型的经验则,见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106页以下。
[94] 德国学者将此称为“证明相对方事实主张具体化义务的加重(gesteigertel substantiierungspflicht des beweisgegners)”,见前引瑏瑤,gottfried baumgärtel等书,第358页以下。
[95] 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下),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30页。
[96] 参见前引[14],gottfried baumgärtel等书,第360页。
[97] 这里之所以限定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是因为英美法系的证明责任概念在构成上与大陆法系存在明显差别,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大陆
法系的相关理论。关于这一点,可参见黄国昌:《阶段的举证责任论——统合实体法政策下之裁判规范与诉讼法观点下之行为规范》,载黄国昌:《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134页。
[98]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56页。
[99]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57页以下。
[100]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63-264页。
[101]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59页。
[102]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04页;前引[14],gottfried baumgärtel等书,第223页。
善意取得制度范文第15篇
内容提要: 《物权法》第106条确立的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规则,只能解释为主张善意取得的第三人负担证明责任。尽管善意要件的证明有一定难度,但通过间接证据的运用、经验则的援引以及对方当事人事实主张责任的加重,证明该要件是完全可能的。立法论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需要结合诸如进攻者角色、盖然性衡量、证明接近之类的实质性因素,以及公示方式与交易习惯、诉讼程序的实际运作、法律政治考量之类的外部因素进行。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善意取得的成立需要符合三个要件:受让人善意,交易价格合理,不动产登记或者动产交付。三要件中,后两个要件具体而明确,其法律适用相对简单。唯第一个要件,因涉及受让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其证明究竟遵循何种原则和标准,不仅在司法实务中乱象丛生,学说上亦不乏纷争。
(一)实务中的乱象
实务中的混乱状态,从以下几个案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1]
案例1:a将其所有的房子交给侄子d长期居住,而d将该房转卖给了h。a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与h二人之间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无效;h主张其对房产构成了善意取得。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判决书中写道:“被告h辩称自己作为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该房屋归被告d所有,因双方签订协议时,没有向其交付任何有关该房屋的手续,而h又无证据证实该房屋系d所有,因此,h以善意购买该房屋的辩解,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2]
案例2:y与t原为夫妻。离婚后,y向h借款,并以t名下的轿车与h签订了质押担保。后y逾期未返还借款,h请求法院确认其对小轿车的占有构成善意取得动产质权。一审驳回了h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生效后,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抗诉理由之一是原审判决由原告h负担其为善意的举证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再审法院接受了这条意见,却仍维持了原判。再审判决中写到:“本案车辆质押合同的效力仍需衡量h占有该车辆时是否出于善意,即h不知道y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则构成善意取得。在判断h是否为善意,理论上虽应采取推定的方法,应由t对h占有该车辆时的恶意进行举证,但是,本案中的有效证据显示,y向h交付轿车时,机动车登记证书明确载明车辆所有权人是t,即使h不知道y与t离婚之事实,h也仅能推断该车辆系y与t的共同共有财产,在未经t同意的情形下,y不得单独对该车辆作出处分。根据在案证据已可证实h未尽一定程度的注意义务……” [3]
案例3:j与z原系夫妻关系。z在其与j的离婚诉讼期间,将其本人名下的一套房产卖给了w。j诉至法院,称该房产系其与z的夫妻共同财产,要求法院判令z与w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被告则主张其对该房产的占有构成善意取得。在一审过程中,原告j提交了其所属单位的电话本3份,以证明被告w知道原告和被告z是夫妻关系,并可能知道原告和被告正处于离婚诉讼期间。一审法院认为j的证据不足以证明w买房时系恶意,驳回了j的诉讼请求。j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判决书中写道:“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j上诉称被上诉人w购买房屋时并非属于善意取得,对该主张,因其未能举出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4]
反映在上述判决中的有关善意要件之证明的混沌不明之处,大致可以归入两个问题:一是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二是善意要件在具体案件中如何证明。就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第一份判决看上去认为第三人应当就其善意负证明责任;第二份判决明确指出,就第三人的善意,理论上应采推定的方法,由原权利人证明其恶意;第三个案件相对复杂,但从判决书的论述逻辑来看,法官似乎认为共同财产所有人应当就第三人接受财产转让时的非善意负证明责任。[5]就善意要件的具体证明,三份判决也都作出了详略不等的说明。
(二)学说上的分歧
就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者间存在明显分歧。尽管多数民法学者认为,就善意要件的认定应当采取推定的方法,即推定受让人为善意,而由主张其为非善意的原权利人就受让人的恶意或者重大过失负举证责任; [6]晚近发表的两篇专论却持不同观点。[7]在对现行法进行法解释学阐释时,两篇专论一致认为,善意要件应由主张善意取得的受让人(第三人)负担证明责任。不过,就导致这种证明责任分配方法的条文设计是否合理,二文之一却提出了激烈的批评。[8]在该文看来,我国目前的制度设计使得第三人不得不证明实际上很难证明的“消极事实”,这将严重限制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甚至让这一制度的规范目的落空。在逻辑上,这种批评以善意证明的难度否定第三人负担善意证明责任的制度安排,我们看到,这种逻辑在其他民法学者那里也有体现。[9]这提醒我们:在讨论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时,实际上无法回避该要件究竟如何证明的问题。
本文拟就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澄清呈现于上述判决、学说上的混乱和纷争。引言之后,第二部分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分析《物权法》第106条中蕴含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第三部分讨论善意要件的证明可能性及其实现策略;在结束司法论的考察之后,第四部分从立法论的角度分析未来该问题立法需要考量的内外因素;结论部分归纳本文主要论点,并就本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稍作阐发。
二、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法解释学的分析
所谓证明责任,即争议事实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的败诉责任。通说认为,证明责任规范在性质上属于实体法,应当主要从实体法规范中寻求和发现。[10]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与善意要件直接相关的则是该条第一款后句。这样,我国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主要就转化为该条规范的解释问题。
(一)语义解释
立法者一般不会在实体法中直接规定证明责任分配,但通过分析实体法规范的文义和结构,从中发现证明责任规范却是可能的。依其表述方式和规范结构,罗森贝克将实体法规范分为权利形成规范、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妨碍规范和权利受制规范,其中,权利形成规范是从正面规定权利成立的规范,后三种规范则是从反面规定权利消灭或者受阻的规范。由于每方当事人都要主张和证明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规范,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就对权利形成规范负担主张和证明责任,否认权利存在或主张权利消灭、受阻的当事人则对后三种法律规范负担主张和证明责任。[11]这就是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规范说。[12]考虑到规范说直接诉诸实体法规范表达方式的特点,人们有理由把这种学说看作实体法语义解释的一种。[13]尽管规范说已经遭到不少批评,但主流观点大多认可其基本框架,所谓修正只反映在一些细节; [14]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德国、日本,还是我国台湾,规范说都仍是法官司法实务中通行的学说。[15]究其原因,是因为由这种学说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清晰、稳定而统一,易受职业法律人的青睐。[16]因此,这里仍从规范说开始我们对《物权法》第106条的证明责任意义上的法律解释。
考虑到在诉讼中,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一般需要援引权利形成规范作为攻击手段,主张该权利不存在的当事人则要援引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妨碍规范和权利受制规范作为防御手段,这两类规范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基本规范”与“相对规范”来界定。[17]由此出发,关于《物权法》第106条第一句的解读方式就有两种:一种是,将前半句关于追回权的规定看作基本规范,而将后半句看作其相对规范;另一种是将后半句本身看作基本规范。在前一种解读方式中,《物权法》第106条后半句关于善意取得三要件的规定属于(追回权的)权利妨碍规范;在后一种解读方式中,该规定则属于(善意取得的)权利形成规范。但无论采用哪一种解读方式,关于该条证明责任分配方法的结论都是相同的,[18]即主张善意占有的当事人应当就该条列举的所有三个法律要件负证明责任——其中自然也包括善意要件的证明。我们看到,其他学者对《物权法》第106条的解释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9]
(二)体系解释
针对规范说的一个批评是,仅从法律条文的文义和构造中寻求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不合理的。[20]一方面,立法者在设计实体法规范时可能并没有考虑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另一方面,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常常也不是通过单个条文来表达的。仅仅从一个法律条文出发,机械地运用规范说,可能会得出与立法者意图相悖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法。现代法律解释理论认为,法条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一定的“意义脉络”当中。[21]这要求法律适用者在对一个法条进行解释时,除了关注这个法条本身的文法和语义,还要考虑它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与其他法条的关系。[22]在法律的意义脉络和逻辑关系中理解一个法条,这就是所谓体系解释。具体到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规则,上一小节的语义解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的起点,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考察:体系解释是否会带给我们不同的解释结果?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在《物权法》第106条的意义脉络中,善意取得是作为无权处分法律效果的例外情形规定的。[23]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这种体系安排背后的逻辑是:如果我们认为主张无权处分者应当证明其所有权及无权处分,那么作为与这种法律效果对抗的砝码,善意取得的主张人自然应当就其是否符合善意取得的三个要件进行证明。
其次,根据相同概念相同解释的法律解释规则,[24]关于《物权法》第106条中的“善意”概念的解释,应当尽量与民法中的其他法律制度保持一致。我们看到,在《合同法》的表见制度中,同样存在“善意”的概念。[25]就概念内涵,两种情形下的“善意”并没有太大区别;[26]就规范目的,物权法对于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与合同法对于善意相对人的保护亦无本质不同。[27]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权。” [28]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效力,如果没有相反理由,就《物权法》第106条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也应作相同的理解。
(三)目的论解释
法律规范的语义确立了法律解释的起点和边界;在此边界内,体系解释让法律规范的语义更加清晰和丰满,因此不妨看作是一种延伸了的语义解释。而无论语义解释还是体系解释,目的都在于探寻立法者的规范意图。在对规范说进行反思、批判的过程中,已有学者提出应在证明责任的分配基准中引入利益衡量或者实体法旨趣之类实质性考量的观点。[29]姑且不论这类观点是否成立,仅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如果基于规范说得到的证明责任分配结论与《物权法》第106条的规范意图明显冲突,那么这种结论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就《物权法》第106条的立法意图,学者的观点存在分歧。一位学者认为,《物权法》第106条通过将善意要件作为法律成立要件规定的方式将该要件的证明责任加诸第三人,体现了一种优先保护所有权的立法意图。[30]在另两位学者看来,如此规定只会限制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导致《物权法》第106条规范目的——即保护交易安全——落空的严重后果。二位学者更明确指出,不能想当然的以为,物权法作此规定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所有权;这只不过是法条设计不当的结果而已。[31]
在笔者看来,第一种观点更有说服力。首先,将保护交易安全界定为善意取得制度的目的虽然没有错,却不能把保护交易安全看作这一制度的唯一目的。正如拉伦茨所言,“一项法律规则常不只要实现一个目的,毋宁常以不同的程度追求多数的目的。”[32]尽管善意取得制度的确立表明法律在总体上采取了牺牲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而保护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的立场,但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无论何时、何地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因为这一点,多数国家选择了兼顾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与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的“中间法立场”,而非原则上不承认善意取得或者对善意取得的范围基本不加限制的“极端法立场”。我国《物权法》亦不例外。[33]从这个角度,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规范目的并非单纯保护交易安全这一种利益,而毋宁是在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保护这两种利益当中寻求平衡。[34]
其次,在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相比的意义上,说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偏重保护所有权并不牵强。如前所述,在我国《物权法》中,善意取得是被放在无权处分的法律效果——原所有权人的追回权——之后,作为其例外而规定的。这种立法体例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并不多见,与德国法相关规定更形成了鲜明对比。[35]《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1款规定:“即使物不属于让与人,取得人也因依照第条所为的让与而成为所有人,但取得人在依照该条的规定将会取得所有权时非为善意的除外。”而根据《德国民法典》第929条第1句,“为转让动产的所有权,所有人必须将该物交付给取得人,并且所有人和取得人必须达成关于所有权应移转的合意”。[36]学者指出,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彰显了物权行为有因性的立法原则,《德国民法典》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则以第929条确立的独立的、无因的物权行为逻辑起点。[37]也就是说,第929条确立了“满足交付与合意两个要件即带来所有权转移之法律后果”的规范,第932条第1款则将这一规范的适用范围从有权处分拓展到了无权处分。与这种明显旨在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例相比,我国《物权法》第106条无疑更倾向于保护所有权。
其实,这种倾向在我国《物权法》中多有体现。比如,我国《物权法》没有规定取得时效制度,对占有制度的规定也相当粗陋。考虑到取得时效以及占有保护均构成对原所有权的限制,现行法对这两类制度的消极态度,可以说进一步反映了立法者对于所有权保护的偏爱。
以上分析表明,《物权法》第106条在规范意图上的确偏重保护所有权,而将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施加给主张善意的第三人,正是这种规范意图的体现。退一步讲,即便我们承认“保护交易安全”是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主要规范目的,第三人负担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的立法例也并不会使这一规范目的落空。从原则上不承认善意取得,[38]到承认善意取得并且将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施加给原所有权人,我国《物权法》第106条的设计位于中间。这种立法例与那种将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施加给原所有权人的立法例相比,差别仅仅在于第三人善意与否真伪不明的那一部分案件;对于那些能够证明其善意的第三人而言,交易安全利益仍然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四)比较法解释
比较法不能作为解释现行法的直接依据,但可以为我们理解现行法提供间接参考。实际上,在对一种法律制度尚未形成稳定的法解释学共识之前,引入比较法资源经常是法律解释者不得不为的选择。我们看到,民法学者以推定解释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无疑受到了日本和我国台湾民法学著作的影响; [39]而徐涤宇、胡东海对现行法的批评,则是因为德国法提供了不同的立法例。[40]比较法上的这些反例,是否可以成为推翻本文解释结论——特别是基于规范说的语义解释结论——的依据?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完全否定的。
首先,日本法、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不构成对上文分析的反驳。一个不言自明的逻辑是:作为一种确定证明责任分配基本原则的理论学说,规范说仅适用于法律没有就证明责任分配作出规定的场合。[41]《日本民法典》第192条规定,“通过交易行为平稳且公然开始占有动产的人,在善意且无过失时,即时取得可在该动产上行使的权利。” [42]表面上看,善意在这里似乎是权利成立规范的要件事实。但问题是,就善意的成立,《日本民法典》第186条第1款已经规定:“占有人,可推定为以所有的意思、善意、平稳且公然地占有之人。” [43]《日本民法典》第186条实际是一条假推定之名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44]立法者通过这个规范,将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直接分配给了就占有人的善意提出异议的人。由于第186条的存在,规范说被排除在了第192条的解释之外。差不多相同的规定也出现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条。[45]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台湾民法学者的论述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总是被从反面、以恶意证明的方式赋予原权利人。[46]
其次,德国法同样不构成对上文分析的反驳。就《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1款,拉伦茨认为,“在有人对取得人的所有权提出疑问时,取得人只需要证明根据第929条所有的让与行为,而毋需也证明他在取得所有权之时是善意的。对取得人的所有权提出疑问的人,才必须对取得人的非善意提出证明。” [47]按照罗森贝克的理论,通过“……除外”这样的表达方式,立法者赋予第932条第1款以权利妨碍规范的性质。[48]主张该规范以妨碍基于第932条前半句主张善意取得者,需要就该规范负担证明责任,即证明取得人为非善意。[49]与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将善意要件作为取得人的权利成立要件规定相比,德国法第932条代表了另一种立法例。但这两种立法例都可以被纳入同一种解释工具,即规范说。
最后,上述立法例都可以在其本国善意取得制度的规范目的中得到解释。关于善意取得的规范目的,上一节已有简单涉及。这里以德国法为例,提供进一步的论据。在德国民法典第一立法委员会拟定的草案当中,善意的证明责任其实是被交给取得人的,因为当时的起草者认为,占有的公信力无法与不动产登记相提并论。但在第二次立法委员会那里,交易安全利益压倒了所有权保护利益。[50]结果,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意图在证明责任环节也获得了优先考虑,立法者将善意要件的规范形式由之前的权利形成规范改成了现在的法律妨碍规范。[51]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在立法上,将善意要件作为善意取得的权利成立要件和将其作为权利妨碍要件来规定都是可能的;第二,选择哪一种立法模式,起决定作用的是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就立法技术的运用而言,两种立法模式并无不同,即都是通过规范表述方式的选择,达到在当事人之间妥当配置证明责任的目的。
综上所述,尽管日本法、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和德国法关于善意要件证明责任分配的立法与我国《物权法》不同,但这只是各国(地区)善意取得制度不同立法意图的反映。一旦引入立法意图的因素,比较法上的不同立法例就变得可以理解,也不再有优劣之分。上述立法例不仅没有证伪,反而从方法上进一步证成了前文关于《物权法》第106条的解释结论。
(五)普适的德国法
徐涤宇、胡东海二位先生的《证明责任视野下善意取得之善意要件的制度设计——〈物权法〉第条之批评》一文(以下简称徐文),从证明责任角度对《物权法》第106条提出了激烈批评。徐文从《德国民法典》第932条出发,认为该条确立的善意要件证明责任分配规范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在比较法上具有普适性;反观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则由于立法者缺乏通过实体法分配证明责任的意识,有规范目的落空之虞;这一缺陷已经无法通过解释论弥补,而必须借助“超越法律的续造”来补救。[52]就该文部分观点及论据,前文已有零星反驳,此处不赘。唯“德国法的普适性”一点,因在徐文中具有方法论的基石意义,仍需进一步澄清。
首先可以指出的是:即便最粗糙的比较法考察,也不能得出《德国民法典》第932条具有“普适性”的结论。在大陆法系,日本法、我国台湾地区法、瑞士法的法条结构与德国法均不相同;在英美法系,美国法更是提供了完全相反的判例。[53]不需要更多的考察,对于“德国法具有普适性”的判断,有限的几个反例就已经足够了。更重要的是,即便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采用了德国法的立法例,因此在概率的意义上姑且承认德国法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性”,但这一判断对我们评估中国法也不具有直接的意义。立法者面对的社会情景不同,需要达到的立法目的不同,为此可以选择的立法技术也不同。评价一个国家的某个立法妥当与否,只能看这一立法在立法目的的设置上是否顺应了这个国家社会、经济的需要,以及立法者是否通过立法技术的运用,妥帖地实现了这一立法目的。从这个角度,仅仅因为德国法的“普适性”而批评中国《物权法》第106条设计不当,这本身就是武断的和不公正的。
在笔者看来,徐文的关键问题在于:发现了德国法与中国法的区别,却没有深入分析导致这种区别的原因,而是将其简单归咎于立法者的疏忽;接受了德国法学者关于《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的分析,却没有看到,这种分析只是对德国法的法解释学阐释——而这种阐释恰恰不具有“普适性”。[54]法解释学的终极目的是探寻本国现行法的真义,为做到这一点,只能从本国法规范的语义出发,参考本国法的体系和逻辑,探寻本国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德国学者如此,中国学者也应当如此。从这个意义上,德国法的规定,以及对这些规定的评注都不能成为解释、批评中国的直接依据。而本文迄今为止的分析表明在忠实反映立法者规范意图这一点上,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做得并不比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差;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未发现启动“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的充分理由。[55]
三、善意要件的证明之道
依前所述,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物权法》第106条第一款只能解释为第三人负担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不无争议的是,善意要件是否能够证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又应通过哪些方法来证明?这类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圆满回答,第一节的分析也许难免遭遇“概念法学”的非议。
(一)无法证明的善意
一个经常看到、但却很少得到充分论证的观点是,作为一种否定性事实,[56]善意要件很难从正面被证明。比如,叶金强认为:“由于第三人不知真实物权状况为一消极事实,要求第三人证明其不知,在逻辑上难于成立,而且占有具有推定力,第三人可以将占有人视为真正权利人,所以,在无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真实物权信息的情况下,即应推定第三人为善意。可见,原权利人如果要否定善意取得的构成,需要举证证明第三人知道事实真相。” [57]陈华彬认为:“因无过失为常态,有过失为变态,且无过失为消极事实,依民事诉讼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占有人应无须就此常态与消极事实负举证的责任。” [58]徐涤宇、胡东海认为:“受让人若要成功证明自己的善意,却并非易事。此所谓善意是指不知让与人无处分权而言。因而,‘善意’是一种否定性事实或消极性事实。此类事实,虽非证明责任理论中的消极事实说认为的‘消极事实不能证明’,却也是很难证明的,加之‘善意’是一种主观内在状态,其证明难度更大。” [59]甚至郑金玉也认为,由第三人自证其善意,将会给司法实践带来难题。[60]在笔者看来,这类观点的价值主要不在法解释学,而在法政策学。在法解释学层面,如果上文的分析成立,那么,即使真如论者所言——善意要件很难被证明,解释者也只能认为,立法者本来就是要通过证明难度的增加而将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限制在很小的范围。[61]但在法政策学层面,如果这种论点成立,立法者在设计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规则时就不应对其视而不见。但是,善意要件真的无法证明吗?或者至少,善意的证明难度要远远大于恶意的证明吗?无论从理论还是实务的角度考察,对这些设问的回答看上去都是否定的。
首先,作为这一论点理论基础的否定事实说,早已被证明为是不妥当的。否定事实说认为,只有肯定的事实能够证明,否定的事实是不可能证明的。这一学说早已被德国法学家抛弃。德国研究证明责任的所有权威学者——从最早的罗森贝克[62],到晚近的莱波尔德[63]、穆泽拉克[64]、普维庭[65],都一再指出,否定事实说原则上是错误的。肯定事实与否定事实的区分,从来不是决定证明责任分配的关键因素,甚至不是重要因素。即使是立法者经常会在立法上避免否定事实的证明,也不能改变这一结论。[66]在英美法系,该理论自十九世纪末就被学者抛弃。[67]尽管有判例从“否定性事实不易证明”的角度分析证明责任的分配,但正如学者指出的,在这些案件中,决定证明责任分配的关键因素其实是公共政策考量。在普通法中,同时大量存在要求当事人证明否定性事实的例子;就这类事实的证明,并不存在一个原则性的标准。[68]在我国,学者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69]在笔者看来,否定事实说之所以会被抛弃,主要是因为否定事实与肯定事实的划分非常模糊。[70]部分地因为这一点,否定事实是否难以证明,就成为一个不能一概而论的问题。一个事实要件究竟是从否定的方面更容易证明,还是从肯定的方面更容易证明,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71]
其次,具体到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正面证明善意未必比从反面证明恶意更难。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是指第三人的“不知情”,即不知道并且不应该知道处分人对于财产没有处分权;所谓“恶意”,则是指第三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处分人对于财产没有处分权。陈华彬先生认为:“占有人是否以善意加以占有,因属其个人内心之事,难以举证证明,故在善意占有抑或恶意占有的事实不明时,推定为善意占有。” [72]这一论断的前半句并无不妥;但问题在于,“恶意”同样是“个人内心之事”,没什么证据表明证明“恶意”比证明“善意”容易。实际上,无论善意证明还是恶意证明,都必须运用一些特殊的证明策略才能完成。[73]既然如此,善意证明的难度如何就能成为善意要件证明责任分配的依据呢? [74]
最后,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告诉我们,证明“善意”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说以上分析只是理论上的“假说”,那么中国法官的实践则为这种“假说”提供了大量证据。在《物权法》颁行后的审判活动中,中国法院频繁作出认定善意要件成立的判决。只需稍举数例: [75]
1、“白存忠持有宅基地使用证书,该使用证书上非原告名字,马正省征询了村委意见,签订协议时包括小队长在内的多名中间人参加,故马正省购买白存忠的房屋时没有恶意,是善意的。” [76]
2、“第三人李某运作为房屋的卖方持有原告韩某的房产证、身份证复印件、房屋钥匙,与被告王某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该房屋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被告王某购买了该房屋,并支付了合理对价。房屋买卖协议签订后,被告王某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已数年,原告韩某一直未提出异议。第三人李某运虽无权处分该房屋,但被告王某有理由相信第三人李某运有权处分。被告王某购买该房屋是善意取得。” [77]
3、“被告候某、万某间系夫妻关系,被告候某十多年来对其房产不闻不问,其漠视自己所有权的行为,显然有悖生活常理。被告朱某有理由相信被告候某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房已出售他人,被告万某也具有出售房屋的权,被告万某实施的出售房屋的行为,系被告候某、万某的共同意思表示。因此,被告朱某善意有偿取得房产,其合法权益应予保护。” [78]
4、“因涉案财产原所有权人群翊公司在设定所有权保留时未依法进行登记,亦未通过其他方式向合同外第三人进行公示,合同外第三人雅新线路板公司不可能知晓设备出让人系无权处分,其受让财产应属善意。” [79]
5、“在本案中,藏东菊将五间房作价8000元抵偿给了王国忠,是藏东菊的真实意思表示,王国忠接受该五间房屋予以折抵藏东菊的欠款是善意的,且藏东菊已经将该五间房屋交付给了王国忠,王国忠即取得了该五间房屋的所有权。” [80]
6、“本案中,被告袁铁旦取得争议房屋的权利前,出卖人在此长期居住,原告却没有在此居住,被告袁铁旦和出卖人经协商达成协议,袁铁旦支付了合理对价,出卖方交付了房屋的相关手续,在被告袁铁旦居住后,又自建了房屋,厂方没有提出异议,原告徐其岭事前事后经过该房,明知后也未提出异议,被告袁铁旦有理由相信出卖人对该房屋有处分权。” [81]
7、 “本案被上诉人张开欣于2005年12月4日经中介公司居间介绍,凭当时的房产现有资料(经济实用房的申购人、购房合同签订人均为薛兴国)直接与薛兴国本人签订‘房产买卖协议书’及‘补充条款’。交易时购房合同及购房发票原件交付张开欣保管,房产也交付张开欣入住,张开欣主观上显然是善意的。” [82]
8、“原告张晓娜购买该房屋时,是经中介公司中介购买,购买时诉争房屋登记的原产权人为袁铁路且登记上未显示有异议登记,故作为受让人的原告在购买该房屋时是善意的。” [83]
尽管上述判决就善意证明的阐述详略不等,将它们放在一起,却足以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善意要件的证明难度并没有给中国法官带来太多困惑。尽管笔者没有就善意取得的司法判决做一个系统的统计分析,尽管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大量认定“善意”不成立的案件,但笔者相信,上述判决对于打消那种“因为善意要件证明责任设置不当而导致《物权法》第106条规范意图落空”的担忧,已经足够了。
(二)善意要件的证明策略
作为一种涉及人的主观认知状态和心理状态的事实要件,善意的证明与一般客观事实的证明的确有所不同。这本是不言自明的。笔者相信,不会有哪个法官会用认定一般客观事实的策略和方法来对善意要件进行调查和认定。但这里仍打算对善意要件的证明策略稍作探讨。因为,这种讨论不仅可以为上述结论提供进一步的支持,而且对类似证明难题的解决也具有方法上的参考意义。
1、间接证据的运用。如前所述,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是指“第三人不知道并且不应当知道处分人对财产无处分权”。也就是说,主张善意取得的第三人不仅需要证明其“不知情”,而且需要证明其“不应当知情”——即“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情”。[84]其中,前者涉及第三人在交易时的主观认知状态;后者则是法律对第三人不知情的原因的评价,在实践中经常可以转化为第三人是尽到必要注意义务的问题。[85]
在证据法理论上,知识、意图、意愿这类存在于人类精神领域的事实被界定为“内在事实”,而与存在于外部世界、能够被人类通过五官感知的“外在事实”区别开来。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对于后者,直接证明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对于前者,多数时候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来证明。[86]与善意要件相关的“知情与否”就属于内在事实。对该事实,严格意义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一种,即第三人本人的声明。而考虑到第三人在诉讼中所处的地位,这种声明对法官事实认定的意义非常有限。第三人为证明其“不知情”,还要就此声明进行更具体的事实主张和证据提出。比如,第三人可以提供证人证言,证明他曾经在特定场合谈到过他要与出卖人进行交易,并且从言辞中可以得知他并不知道该出卖人对财产没有处分权。更常见的情形是,第三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出卖人在交易中展示的权利表征让他有理由相信其对财产有处分权。比如,对于不动产,出卖人提供的不动产登记中确实显示了其本人姓名;对于动产,出卖人对财产的占有在具体情景中看上去是持续、稳定的。第三人为证明这些事实提供的证据,在性质上都属于间接证据。对这类证据,法院首先应当审查其关联性,即审查间接证据与证明对象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对那些经过审查,被认为对证明主题的确有效力的间接证据,法院应当从整体上进行综合判断。也就是说,要将这些证据作为一个整体,看它们是否足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即第三人的不知情。[87]
为了证明“无重大过失”,第三人应当就交易的主体、时间、地点、内容和过程提供信息,以证明他在当时的情景中,已尽到了一般人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88]在逻辑上,“无重大过失”的证明发生在“不知情”的证明之后,并以前者为基础。但在实践中,对这两个证明对象的证明经常是不分彼此、交织进行的。比如,当第三人就交易场景以及他在交易中的表现提供证据时,这些证据一方面是证明其“无重大过失”的直接证据,另一方面,又不妨看作证明其“不知情”的间接证据。
上述思路对中国的法官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 [89]其中体现的证明逻辑,与上文的阐述并无实质区别。
2、经验则的援引[90]。所谓经验则,简单的说,就是“从经验中归纳得到的关于事物的知识或法则”。[91] “在经验则这个概念下,人们可以想到的除了通过观察具体事件得到的一般生活经验,还有交易生活、商业、贸易,甚至艺术、科学和技术中的一般性规则、原则和知识。” [92]在善意要件的认定过程中,经验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对于善意的证明经常只能通过各种间接证据来完成。比如,在关于二手车的争议中,第三人提供证据证明:他是在法定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上与出卖人完成交易的;他之前并不认识出卖人;他就该二手车支付了合理的对价。这些证据本身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直接证明第三人是善意的,但将它们放在一起,却可以初步证明这一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官在这里运用了一个经验则——即:在上述情形下,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出卖人对财产有处分权。在上文引用的第4个判决书中,法官也援引了一个经验则:对于没有登记并且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向社会公示的所有权保留,合同外的第三人不可能知道。可见,在间接证据与证明结论——第三人的善意——之间,经验则实际充当了一种桥梁或者纽带的角色。
应该注意,不同类型的经验则,其盖然性并不相同。有些经验则只具有较弱的盖然性,只能作为法官对案件事实进行综合判断时的参考;而另一些经验则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构成了“典型生活过程”,以至于可以直接发生表见证明的效果。[93]另外还要看到,经验则是对证据与争议事实之间关系的一种盖然性说明,就这种说明,对方当事人总是可以通过反例来推翻。比如在上述第四个案件中,原权利人就可以提出第三人实际上知道处分人没有处分权的事实,来反驳“对于没有登记并且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向社会公示的所有权保留,合同外的第三人不可能知道”的经验则。
3、对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义务的加重。[94]在善意要件的证明过程中,第三人并不需要就其主张的所有间接事实进行举证;对于对方没有反驳的间接事实,法官毋宁是直接确认为真。[95]而权利人对第三人主张的间接事实,也不能是简单地否认了事。考虑到善意要件本身的特征,如果简单地否认声明就足以推翻第三人的事实主张,那么法官几乎很少能对争议事实形成心证。善意要件证明的特征要求权利人在否认第三人主张的间接事实时,必须提出足以推翻该间接事实的相反事实。举例言之,如果第三人主张其不认识处分人,这时权利人就不能简单地反驳说,“第三人其实认识处分人”。他必须就第三人与处分人之间的关系提出更加具体的事实。比如他可以指出,第三人与处分人曾在某一特定时期同学。又例如,在对上文判决4中提到的经验则进行反驳时,权利人就不能仅仅说,“即使没有公示,第三人也有可能知道其所有权保留的事实”。这一陈述尽管在理论上完全成立,但作为对本案证明的反驳却是不够的。为了动摇法官的内心确信,他必须提出能够表明第三人知道处分人无处分权的具体事实。一旦权利人提出了足以反驳第三人事实主张的具体事实,接下来就应由第三人就这些事实的不存在进行举证了。第三人的证据只要能够达到推翻上述反驳事实的程度,就算完成了证明。[96]
就证明难题的解决,还能想到一些别的策略,比如法官的事实推定、证明标准的降低,等等。一来为篇幅所限,二来考虑到这些策略的适用范围与前述三种策略多有重合,其概念内涵亦不乏争议,这里不拟展开讨论。之前的阐述已经表明,尽管善意的证明有一定难度,但现代民事诉讼早已发展出一系列解决这类证明难题的策略。只要法官妥善运用了这些策略,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就第三人善意与否获得心证的。需要特别警惕这样一种简单化的思维:一旦将证明责任施加给了一方当事人,这一方当事人就将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出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对方当事人则可以高枕无忧。不仅法官不会认同这种思维,从学理的角度,以这种方式理解证明责任显然也是浅薄的和片面的。实际上,对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法官而言,[97]证明责任规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环节:一是在事实调查开始时,由哪一方当事人首先针对争议事实提出证据;二是在事实调查程序终结而法官无法对争议事实形成心证时,判决哪一方当事人败诉。而在这两点之间的漫长诉讼过程中,法官不仅可以,而且应当运用多种手段,从双方当事人那里尽可能多地获取相关信息,以便对争议事实形成心证。对于法官的审理活动而言,作为真伪不明之时的裁判规则的证明责任规范固然重要,但为了避免适用证明责任规范而发展出来的诸种证明策略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四、立法论上需要考量的若干因素
此前的论述已表明了笔者对《物权法》第106条的基本评价,那就是:从司法证明的角度,这一条文是可以解释的,也是可以适用的。但这只是一个解释论上的中立判断,它并不意味着笔者“喜欢”这个条文,更不意味着笔者否认这一条文有被修改的可能。这种可能性是否,以及何时出现,取决于立法者的法律政策考量。当然,立法者的法律政策考量也应当有章可循。就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立法,以下两类因素是立法者必须关注的。
(一)影响证明责任立法的实质性因素
按照德国学者的观点,法官对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运用只能从实体法出发,而不能在此过程中掺入实质性考量。因为那样的话,法官实际上篡夺了立法者的权力,法律的安定性将荡然无存。[98]但是,对于立法者而言,进行这类实质性考量却是可能的,有时候甚至是必要的。按照普维庭的归纳,这类实质性原则主要有:抽象的盖然性衡量、证明接近、社会保护思想、宪法上地位、进攻者角色、危险增加、消极性证明,等等。[99]不过,对于善意要件的证明,真正需要思考的只有进攻者角色、盖然性衡量和证明接近。
1、进攻者角色。进攻者角色原理的基本要求是,要求改变现状的当事人应当就其主张的事实负担证明责任。在普维庭看来,这一原理在各实质性依据中具有中心地位,因为它与保护占有、权利安定性、社会秩序保护、对现存事实状况的保护和禁止私力救济等基本法律价值密切相关。[100]实际上,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理论通说的规范说与进攻者角色原理基本上契合;或者换句话说,进攻者角色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规范说的实质性依据。[101]表面上看,在善意取得制度中,进攻者角色理论有利于支持让原权利人负担证明责任的观点。不过,这一论辩的价值非常有限。就善意取得所涉及的财产,在不同时期实际存在两个不同的占有:一个是原权利人基于所有权的占有,一个是第三人基于无权处分的占有。固然,基于第三人的视角,我们可以说原所有权人处于进攻者角色;但基于所有权人的视角,又不妨说第三人处于进攻者角色。进攻者角色原理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视角。起决定性意义的只能是立法者的价值判断,或者说,是立法者对所有权保护和占有保护这两种利益进行衡量的结果。
2、盖然性衡量。盖然性衡量理论要求立法者在配置证明责任时,衡量真伪不明时事实“为真”与“为伪”的概率,并据此制定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比如,就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立法者就应当衡量,在现实生活中,究竟第三人为善意的概率更大,还是其为恶意的概率更大。如果第三人为善意的概率更大,那么在真伪不明时判原权利人败诉看上去更具合理性;相应地,在立法上,将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原权利人就是较为妥当的选择。由于引入了概率概念,这一理论比较具有科学性的外观,因此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但是,这一理论对于立法者的参考价值却很有限。主要问题在于对于一个要件事实真伪不明之时“为真”或者“为伪”的概率,实际上很难衡量。以善意要件的证明为例,这一衡量首先涉及人们对于当前社会诚信状况的判断。如果一个社会的诚信状况较好,人们也许可以说,由原权利人证明第三人恶意是较好的选择;反之,则由第三人证明其善意更优。但是,这种判断很大程度上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究竟哪些案件会被认定为“真伪不明”,最终取决于法官的判断;而法官的判断又受到其证据调查能力、裁判习惯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将所有这些因素纳入盖然性衡量的范畴,看上去已经超出了这一理论所能容纳的范围。因此我们看到,就德国民法典第932条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德国学者通常认为,其实质性依据并非盖然性衡量,而是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即对占有人信赖利益的保护。[102]
3、证明接近。按照证明接近原理,立法者在设计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时,应当尽量让距离证据较近的一方当事人提出该证据。基于有利于查清案件真实和节省司法资源的考量,证明接近原理有其合理性,并且在现代产品责任法、医疗责任法等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体现。不过,作为一种主要着眼于克服证明困难的实质性依据,证明接近理论的意义不宜夸大。为了克服证明困难,现代证据法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和理论,比如间接证明、表见证明、对方当事人的事实提出责任,等等。由于这些策略的存在,许多时候,即便某些证据不在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一方,也不影响其对相关要件的有效证明。在证明困难的情况下选择这类策略,而不是根据证明接近原理重新设计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因为这些策略大体都可以归入“证据评价”的范畴,其运用并不会改变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人们实在有太多理由坚持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比如,前文刚刚提到的进攻者角色原理。进攻者原则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即使证据不在我这一方,但如果我希望改变一种法律关系的现状,通常情况下我就要负担证明责任,因为我不能让他人无端地忍受讼累。因此,尽管证明接近原理表面上有利于支持现行法——即有利于支持让第三人负担证明责任的立法例,但我却不愿强调这一论据。
(二)影响立法者利益衡量的外部因素
以上分析几乎都指向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最终决定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证明责任配置方式的只能是立法者的利益衡量。换句话说,就是在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保护这两种利益里面,立法者更偏重于保护哪一种利益。事实上,这也是笔者在之前的法解释学分析中反复强调的观点。但立法者生活在一定时空之中,其价值判断从来不能超脱于其所处的历史与社会之外。与上一节阐述的实质性因素相对,这种来自历史和社会的变量构成了影响善意要件证明责任配置的外部因素。这里不可能全面考察这些因素,只挑出三个方面略加阐述。
1、公示方式与交易习惯。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根基在于物权变动公示的公信力,一般而言,物权的公示方法即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有学者指出,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的公信力存在重大差别:对于不动产,只要受让人信赖了登记,就是善意的,除非其明知登记错误,否则无需考虑交易环境等因素而对于动产,由于占有的公信力较低,受让人就不能仅仅凭借占有的事实当然地相信处分人具有处分权,因而在判断受让人是否具有信赖利益时,还必须考虑其他一系列因素,比如价格的高低、交易的具体环境、交易的场所等。[103]也就是说,基于不同的物权公示方法,关于受让人善意的证明要求也会有所不同。为了弥合这种差别,立法论上似乎可以考虑:对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要件,由原权利人从反面证明受让人为恶意;对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要件,则由受让人从正面证明其善意。[104]
但上述建议很大程度只是理论演绎的结果,它在实践中的合理性,还要结合当前中国民间的交易习惯进行具体分析。比如,我们看到,在我国农村地区,不进行不动产登记的房屋买卖大量存在。基于这样一种现状,立法者如果只是简单强调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结果就有可能导致(在具体情境下)有失公平的案件处理结果。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在考量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方式时,对民间交易习惯的调查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诉讼程序的实际运作。如前所述,实体法关于一个事实要件证明责任分配方式的不同选择,反映了立法者对对立利益进行衡量的不同结果。但是,即便是同一种证明责任的立法例,其在各个国家的实际效果也未必相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证明责任分配方式只决定了真伪不明之时败诉风险负担的大致框架,而在这个框架之内,这种风险究竟以多高的频率出现,很大程度却取决于一个国家诉讼制度的运作情况。比如说,在一个当事人提出证据的手段匮乏,法官化解各种证明难题的能力不足的诉讼环境中,证明责任负担对当事人而言就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而在这两个因素都相对乐观的情况下,证明责任负担带来的压力则会小很多。另外,影响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际效果的还有法官的裁判习惯。比如,法官究竟是倾向于作出证明责任判决,还是倾向于回避作出证明责任判决?在后一种情况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实际意义相对较小,因为它被适用的频率本来就很小;而在前一种情况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影响则较大。考虑到善意本身就是一个主观性较强、证明起来有一定难度的事实要件,立法者在考量其证明责任分配方式时,对上述因素不能不察。
3、法律政治的考量。法律不止是对既有社会生活状态的确认和保障,在许多时候,它还承担着引导公众的行为方式,塑造某种立法者期望的社会生活状态的功能。因此,在一定时期,法律有可能成为立法者推进社会变革的手段和工具。如前所述,现行法对所有权给予更多保护,而对交易变动施加了较多限制。就此制度安排,不妨认为,其背后隐藏着一种“目前社会上的交易行为不尽谨慎”的预设。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前提性预设被修正甚至抛弃都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目前这种制度安排对于经济生活的实际影响是:财产所有人可以以较为随意的方式行使所有权的权能,而受让人则需要在交易中多加谨慎。假如将此看作一种法律政治的考量,这种考量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同样有可能朝着有利于受让人、有利于交易便利的方向变迁。立法者在对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进行配置时,应当对此有着清醒的自觉。
五、结论
经由第二到第四部分的论述,就引言提出的问题,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1、《物权法》第106条确立的善意要件的证明责任规则,只能解释为主张善意取得的第三人负担证明责任。
2、通过间接证据的运用、经验则的援引以及对方当事人事实主张责任的加重,善意要件是可以被证明的。
3、立法论上关于善意要件证明责任分配的讨论,需要结合诸如进攻者角色、盖然性衡量、证明接近之类的实质性因素,以及公示方式与交易习惯、诉讼程序的实际运作、法律政治考量之类的外部因素进行。
此外,本文附带批评了徐涤宇、胡东海二位先生关于善意要件证明责任分配的分析。在笔者看来,尽管徐文的材料、观点均不无偏颇,其最致命的缺陷却在方法。将一个外国法上的命题“普适化”,拿来解释和批评中国法,这种研究方法在中国法学界相当流行。关于这种方法的谬误,前文已有揭示;至于此种谬误的避免,则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在分析中国法时,坚守作为解释者的中立立场。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行法在周密与精致程度上与德国、日本,甚至我国台湾地区法制相比,仍有明显差距;这种差距,又因为上述国家和地区相对丰富的法解释学研究成果而被进一步放大。但是,一种外国法律制度在逻辑周延性、体系自洽性上的优势,并不能成为我们放弃现行法的理由。正因为我们的现行法相对粗糙,才更需要法律人去悉心呵护。只有法律人怀着一种“护法者”的敬畏之情,以最大的耐心去为现行法探寻可能的解释和适用空间,这法律才能在我们的手中获得生机。
其次,在批评中国法时,更多关注中国法的运作实践,而不是仅仅关注中国法与外国法的文本差异。文本比较只能说明有限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法律文本相对简单、粗陋的背景下,拿其他国家成熟的法律制度和理论来衡量它,很容易就得出关于我国法的负面评价。但这种评价并不公正,也没有太大意义。一方面,文本比较揭示的“问题”在实践中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另一方面,法律文本的粗陋可以通过解释者的努力弥补,而这正是法学家的职责所在。
注释:
[1] 为节省篇幅,案情介绍以反映案件主要争议为限,判决书引用则限于与善意要件的证明直接相关的部分。三份判决均来自“北大法宝”,有兴趣的读者自可下载阅读全文。
[2] 判决书全文,见《(2009)郑民初字第963号判决书》。
[3] 判决书全文,见《(2010)浙杭商提字第1号判决书》。
[4] 判决书全文,见《(2010)郑民二终字第537号判决书》。
[5] 在实务中,法官很少使用“真伪不明”的字眼,对于肯定之外的事实判断,一般只是笼统表述为“证据不足,予以驳回”。从理论上,这意味着法官可能就该事实形成了为“否”的内心确信,也可能是该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另一方面,中国现行法上的“举证责任”,与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上的“证明责任”或者“举证责任”概念并不完全相同。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就上述判决究竟采纳了哪一种证明责任分配方案,实际上很难准确判断。这里的归纳是笔者细读三份判决文本之后得出的结论,其中,法官的表达方式和论理逻辑尤其受到了重点关注。笔者深知,这种归纳不完全精确,但为了研究的开展,眼下也只能满足于这种只具有大致可靠性的判断了。
[6] 比如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267页;叶金强:《论善意取得构成中的善意且无重大过失》,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5期;陈华彬:《民法物权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页;程啸:《论不动产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释义》,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尽管上述论著中的某些发表在《物权法》颁布之前,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论著的作者在《物权法》颁行后改变了观点。
[7] 参见徐涤宇、胡东海:《证明责任视野下善意取得之善意要件的制度设计——〈物权法〉第106条之批评》,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4期;郑金玉:《善意取得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研究》,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6期。
[8] 参见上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
[9] 参见前引[6],叶金强文;前引[6],陈华彬书,第550页。
[10] leo rosenberg,die beweislast auf der grundlage des bürgerlichen gesztzbuchs und der zivilprozessordnung,5.aufl.münchen:c.h.beck, 1965,s 82;hans prütting,gegenwartsprobleme der beweislast,münchen:c.h.beck 1983,s 20.;adrian keane,the modern law of evidence,butterworths,1996,p 69;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页(该章为李浩教授撰写)。
[11] 上引[10],leo rosenberg书,第100页以下;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理论与制度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0页。
[12] 通说有时又被称为法律要件分类说,比如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笔者认为,尽管法律要件说与规范说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但代表性论述的内容基本一致。因此,这里不对这两个概念作刻意的区分。
[13] 关于规范说直接诉诸法律文义和规范构造的特点,参见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83-284页。
[14] 比如,在德国,学者基本上都已放弃罗森贝克理论中的“权利受制规范”这一规范类别,vgl gottfried baumgärtel/lhans-willi laumen/hanns prütting,handbuch der beweislast:grundlagen,aufl 2.carl hezmanns verlag,2009,s 146 f.在日本,有学者主张在证
明责任分配标准中引入“实体法旨趣”之类的实质性考量,比如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98-399页。关于日本学者批评观点的更多介绍,参见前引[11],高桥宏志书,第441-448页;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295页;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174页。
[15] 关于规范说(或者法律要件说)的通说地位,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页;前引[14],张卫平书,第305页;前引[12],李浩书,第128-129页;毕玉谦:《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185页。另外,上述中国学者都赞成在中国以规范说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
[16] 参见前引[12],李浩书,第128页;前引瑏瑤,王亚新书,第174页;前引瑏瑥,毕玉谦书,第244-245页。
[17] 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100页。
[18] 一个规范究竟是基本规范还是相对规范,主要取决于当事人在具体诉讼中援引该规范的时间和场合,而对证明责任分配并无影响。关于基本规范与相对规范之间关系的相对性,又见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102页。
[19] 参见前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前引[7],郑金玉文。
[20]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83-284页;前引[14],新堂幸司书,第398-399页。
[21] 参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4-207页。
[22] 卡尔•恩吉斯:《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23] 梁慧星指出,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与《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制度构成了特别法与一般法的逻辑关系。参见梁慧星:《中国民事立法评说》,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
[24] 关于这一解释规则,见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5-76页。
[25] 《合同法》第49条并没有出现“善意相对人”的字眼,这一条只是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该行为有效。”但无论在学理还是在实务中,这里的相对人通常都被称为“善意相对人”。
[26] 即都以第三人不知道并且不应当知道特定事实为内容。
[27] 即都在于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
[28] 《最高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
[29] 参见前引[11],高桥宏志书,第244-248页。
[30] 参见前引[7],郑金玉文。
[31] 参加前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
[32] 前引[21],卡尔•拉伦茨书,第209页。
[33] 参见前引[6],陈华彬书,第282-283页。
[34]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平衡这两种利益的功能,又见谢在全:《民法物权》(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
[35] 《德国民法典》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932-934条,以第932条最为基础,第932条又援引了第929条。相关法条的逻辑关系,见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页。
[36] 《德国民法典》(第三版),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34、335页。
[37] 参见前引[7],郑金玉文。
[38] 比如挪威、丹麦等国。参见前引[6],陈华彬书,第281-282页。
[39] 从论者的知识背景和参引文献中不难发现这一点。
[40] 参见前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
[41] 参见前引[12],李浩书,第138页;前引[15],陈刚书,第256页。
[42] 渠涛编译:《最新日本民法:日本民法典》(2006年新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43] 同上书,第44页。
[44] 推定之名的证明责任规范,见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204页以下。
[45] 见《“中华民国”民法典》第944条。这一条排除了规范说对于该法第948条的适用。类似的规定还出现在《瑞士民法典》引言部分的第3条。按照该条规定,“当本法认为法律效果系属于当事人的善意时,应推定该善意存在。”这条规定同样排除了规范说对于《瑞士民法典》第933条的适用。
[46] 参见前引[34],谢在全书,第221页;王泽鉴书,第486页。
[47] 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又见vgl.jürgen oechsler,in:münchenerkommentar zum bgb,5.aufl.c.h.beck,münchen 2009,s 1069;othmar jauernig(hrsg.),bgb-kommentar,5.aufl.c.h. beck,münchen 2009,s 1293;前引[14],gottfried baumgärtel等书,第223页;palandt/bassenge,bgb,69 aufl.,c.h.beck,münchen2010,s 1504.
[48] 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126-127页,脚注5。
[49] 德国有民法学者认为,善意是善意取得的权利形成事实,只因其认定采推定的方法,因此须由反对方负担证明非善意的证明责任。比如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下册),申卫星、王洪亮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页;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吴
越、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推定。因为,就善意的成立,法律并未规定基础事实;关于恶意的证明是主证,而不是反证,见前引[47],othmar jauernig书,第1293页。
[50] 前引[47],jürgen oechsler书,第1069页。
[51] hans-joachim musielak,die grundlage der beweislast im zivilprozess,walter de gruyter,1975,s 379;前引[48],othmar jauernig书,第1293页。
[52] 参见前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
[53] see,e.g.,oscar gruss&son v.first state bank,582 f.2d 424,432(7th cir.1978);natural resources,inc.v.wineberg,349 f.2d685,688 n.8(9th cir.1965);albee tomato,inc.v.a.b.shalom produce corp.,155 f.3d 612(2d cir.1998).早期的一个述评, see evidence-burden of proving bona fide purchas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4,no.1(dec.,1936),pp.146-148.所有这些判决和述评都一再指出,在美国法上,多数判例认为主张善意取得的受让人应就其善意负证明责任。
[54] 在笔者看来,徐文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作者预先接受了《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法以及德国学者关于该条文立法技术的论述;因为对这种“前见”缺乏必要的自觉,当二位作者开始观察我国《物权法》第106条时,实际上已经无法做到作为一名解释者所应有的客观、中立。
[55] 关于“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参见前引[21],卡尔•拉伦茨书,第286页以下。
[56] 有时又被表述为消极事实。考虑到这主要是译名选择的不同所致,本文对这两个概念不作区分。
[57] 参见前引[6],叶金强文。
[58] 参见前引[6],陈华彬书,第550页。
[59] 参见前引[7],徐涤宇、胡东海文。
[60] 参见前引[7],郑金玉文。
[61] 罗森贝克指出:“证明困难并非证明不可能……如果认为对否定加以证明是没有必要的,那就意味着必须修改实体法。”否定事实是否需要证明,“仅仅取决于法律是否将该否定规定为法律效力的前提。如果法律将它规定为法律效力的前提条件,那么,主张此等法律效力的人,同样必须就该否定承担证明责任。”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332、333页。
[62] 同上书,第330页以下。
[63] dieter leipold,beweislastregeln und gesetzliche vermutung,berlin:dunker&humblot 1966,s 47.
[64] 前引[51],hans-joachim musielak书,第371、376页。
[65]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59页。
[66] 前引[10],leo rosenberg书,第333页;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59页。
[67] 黄国昌:《阶段的举证责任论——统合实体法政策下之裁判规范与诉讼法观点下之行为规范》,载氏著:《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68] see rupert cross/colin tapper,cross on evidence,buttersorths,1990,p124.
[69] 参见前引[12],李浩书,第128页;前引[14],张卫平书,第281-282页;折衷的观点,见前引[15],毕玉谦书,第41-50页。
[70] 前引[14],张卫平书,第281-282页。
[71] 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见姜世明:《举证责任与证明度》,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56页。
[72] 前引[6],陈华彬书,第550页。
[73] 下一节集中讨论这些证明策略。
[74] 笔者认为,日本法和台湾法中有关占有的善意推定在性质上属于占有推定的内容,导致这种立法的是法律政策的考量(即对占有公信力的确认和保护),与善意的证明难度并无直接关系。
[75] 出于篇幅考虑,仅引用判决书中认定善意要件成立的部分。完整的案情和判决,请参考判决书原文。所有判决均来自“北大法宝”。
[76] 《(2010)焦民二终字第196号判决书》。
[77] 该判决在二审中被改判,但改判的理由是不动产没有登记,而不是第三人非善意。参见《(2009)商民终字第120号判决书》。
[78] 《(2008)崇民一(民)初字第3149号判决书》。
[79] 《(2007)苏中民三初字第0094号判决书》。
[80] 《(2009)新中民四终字第504号判决书》
[81] 《(2009)川民初字第0972号判决书》。
[82] 《(2007)厦民终字第2115号判决书》。
[83] 《(2009)驿民初字第2324号判决书》。
[84] 关于善意的内容,民法学界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从现行法出发,将善意解释为包含不知情和非因重大过失不知情较为妥当
[85] 前引[34],王泽鉴书,第486-487页。
[86] 前引[14],gottfried baumgärtel等书,第309页.
[87] 关于间接证据的整体性审查,参见前引[14],gottfried baumgrtel等书,第320页
[88] vgl gottfried baumgärtel/lhans-willi laumen/hanns prütting,handbuch der beweislast:bgb sachenrecht(§§854-1296).aufl 3. carl hezmanns verlag,2010,s 224.
[8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
[90] 这里之所以使用“经验则”,而不是更流行的“经验法则”一词,是因为,这一概念显然来自德语的erfahrungssätze一词,而这个由erfahrung(经验)和sätze(句子)构成的德文单词,并不包含“法则”一词的含义。另外,如果我们把erfahrungssätze译为“经验法则”,在翻译与denkgesetz(思维法则)、naturgesetz(自然法则)并列的erfahrungsgesetz一词时就会遇到困难,因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验法则”。
[91] 前引[11],高桥宏志书,第29页。
[92] stein/jonas/leipold,kommentar zur zpo,22.aufl.tübingen 2008,s 640.
[93] 不同类型的经验则,见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106页以下。
[94] 德国学者将此称为“证明相对方事实主张具体化义务的加重(gesteigertel substantiierungspflicht des beweisgegners)”,见前引瑏瑤,gottfried baumgärtel等书,第358页以下。
[95] 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下),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30页。
[96] 参见前引[14],gottfried baumgärtel等书,第360页。
[97] 这里之所以限定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是因为英美法系的证明责任概念在构成上与大陆法系存在明显差别,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大陆
法系的相关理论。关于这一点,可参见黄国昌:《阶段的举证责任论——统合实体法政策下之裁判规范与诉讼法观点下之行为规范》,载黄国昌:《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134页。
[98]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56页。
[99]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57页以下。
[100]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63-264页。
[101]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59页。
[102] 前引[10],hans prütting书,第204页;前引[14],gottfried baumgärtel等书,第223页。
- 上一篇:会计电算化实训报告范文
- 下一篇:案情汇报材料范文